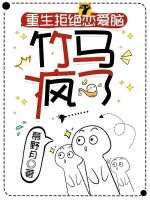尼采不在家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瞎子恍然,“眼中”出現了一些片段,他分心二用,邊熟稔彈奏著琵琶,邊看著那連續的片段,像是看著上了年代的老港片。
···
破落的街巷老舊潮溼,圍著街巷買賣的人群踩著汙水,逆流而行的男人叩響了玫夫人家外的木門。
玫夫人身著碎花無領襖裙,半白的頭髮挽成了髻,臉上總是掛著恬靜的淡淡笑意,哪怕歲月在她的臉上蝕刻出了細微紋路,這笑意也不曾更改。
供香的氣息從玫夫人的家中飄出,竊竊私語聲像是在男人的耳畔低語呢喃,也似呼喚哭喊。
玫夫人抬眼,盤旋在空中的湛青煙雲中浮現幾個奔逃的輪廓,隨後完全消散。
“家裡小的不懂事,見諒。”玫夫人靜靜的看著男人,有些歉疚的笑著。
男人喉結聳動,他小的時候,玫夫人便是如此,總會對人道歉,說家裡的孩子不懂事,只是那時玫夫人還很年輕,也是最靈驗的。
玫夫人瞧事從不大張旗鼓,沒有什麼法壇,也不跳什麼大神。
家裡遇了邪的,玫夫人說著吳儂軟語,邪祟便離開了。
小孩撞了煞的,玫夫人袖手一抹,不退的高燒便消了。
後來玫夫人的丈夫因病離世,她便也不怎麼替人瞧事兒了。
她說:“報應,不就來了麼?”
——
玫夫人出身水鄉,也是書香門第之家,有才有德,性子恬靜,後來嫁人了也與丈夫桂先生琴瑟和諧,夫婦二人相敬如賓,哪怕玫夫人無法生育,桂先生也不曾有過埋怨。
只是有時候桂先生會問要不要收養一個孩子。
玫夫人總是說:“家裡孩子多,再添一個,它們會害怕。”
桂先生總是問:“為什麼要害怕?”
每當這時,玫夫人都會笑一下:“害怕母親的愛會被搶走唄。”
···
街道上聚攏了不少人,頑皮的孩童們手裡捏著糖人瞧著大人們把丹砂,白堊,黑炭,青雘朝著臉上塗抹,老人檢查著高蹺是否完好,
斧子、鍘刀、剪刀、鏈刀錐子等的尖銳利器散落在木箱裡,頑皮的小孩摸上去,笑著說:“軟的。”
玫夫人跟著男人朝前走著,而後停了下來,她嫻靜的看著玩耍的孩子,嘴角噙著笑意。
“回來吧。”
不知道對誰說的,語畢,玫夫人便離開了。
孩童們問著。
“你們要走了嗎?”“好吧,等會一起看社火吧?”“哦,好吧···”
社火娛神,香火娛人,移居的人們將這重大的典禮也一併帶到了香江哩。
化著妝的老人瞧見了,忙把小孩們喊了過去,把丹砂抹在了小孩的額心。
“丹砂辟邪,丹砂辟邪。”老人一邊抹著,一邊唸叨著。
畢竟小孩能看見大人看不見的東西,若是個壞的,便會遭了祟。
丹砂可辟邪,點在額心那就不會遭惡祟了。
——
玫夫人喜歡花,因此桂先生總會在清晨將院子裡的花摘出,花瓣還沾著露水,便放在了玫夫人的床頭。
玫夫人醒來後,又會將花插進花瓶裡,換掉謝了的花,再將枯萎的花葬入土中。
桂先生總說他是家裡最會養花的人。
玫夫人聽罷都會笑:“這家攏共就咱倆人啊。”
後來,玫夫人成了這個家最會養花的人。
···
玫夫人打量著莊園門口的月季,花小瓣少,色暗淡而無光澤,暗暗搖頭。
那個逆流而行扣響玫夫人屋門的男人是個大宅宅院裡的僕人,姓就不提了,名兒叫做豐良,早年間被買來,彼時主人問豐良,為什麼要叫豐良。
豐良答:“希望家裡收成好唄,教書的先生寫了兩個字,說“良”和“糧”讀起來一樣,但爹覺得“良”比“糧”好寫,所以就叫豐良了。”
可是,豐良出生以後餓死了兩個姐姐,剛出生的小妹也快要被送到嬰兒塔裡了,他倒是有個哥哥還活著,可惜是個痴傻的,痴傻的哥哥每逢年關看到了點肉絲,都會喊“招娣”“盼娣”。
那是他兩個姐姐的名字。
主人一聽:“那你以後就叫阿良吧。”
阿良奇怪的問:“為什麼不叫豐良?”
主人嘆了口氣:“叫豐糧,不也沒保住你家女孩麼?”
此後,阿良便不再叫豐良了。
···
阿良家主人姓陳,留過洋,但沒什麼洋墨水,實際上,他肚子裡也沒什麼墨水,回來以後繼承家業,做了個富紳,一房四個姨太太,正妻學著洋人和他離了婚,他倒也不怎麼介意。
陳老爺領著四個花枝招展的姨太太出了門,其中一個挺著肚子。
“玫夫人,有失遠迎,有失遠迎,您令寒舍蓬蓽生輝啊。”陳老爺笑呵呵的。
玫夫人沒應,只是瞧著躲在人群當中的小姑娘,小姑娘也定定的瞧著她。
陳老爺見了,便招呼著小姑娘過來。
“笙萍,快叫玫阿姨。”陳老爺牽著笙萍的手,教著笙萍,順便也為玫夫人介紹著,“她是阿良的女兒。”
玫夫人看了看阿良,也看了看笙萍,俯身摸了摸笙萍細軟的頭髮,後將笙萍脖子上掛著的長命鎖挑了出來。
“這鎖,誰給她掛的?”玫夫人問著。
“是個老太太,老太太討水喝的時候說笙萍年紀小身子弱,容易夭了,她說可以送一副長命鎖,這樣笙萍就能平平安安的長大了。”
玫夫人聽了,愛憐的撫著笙萍的前額,扯下了長命鎖。
“償命鎖保不住,只會償命,還是家裡供奉床頭婆婆吧,婆婆很慈祥呢。”
床頭婆婆,是孩童們的保護神之一。
玫夫人眼神微眯,若有若無的怒意和殺機閃過,又被藏起,她握著長命鎖,用手帕包著收了起來,
她抬眼看著陳老爺。
“你讓阿良請我來,是出了什麼事麼?”玫夫人問著陳老爺。
陳老爺面色稍沉,低聲道。
“是···佳佳說她見著不乾淨的東西了。”
——
阿良小的時候也經常跟著陳家老爺去玫夫人家裡聽桂先生彈鋼琴,陳老爺不懂西洋樂器,但並不妨礙他附庸風雅,聽桂先生說鋼琴是個洋玩意,有時鋼琴裡總能彈出很多他覺得好聽的樂曲。
阿良問桂先生:“桂先生,這洋玩意能比得上咱老祖宗留下來的樂器麼?”
桂先生答:“每種樂器都是平等的,只是性格不一樣,音色不一樣,是哪裡的樂器其實不重要,能表達音樂的美感就好。”
阿良似懂非懂:“那玫姨喜歡你,是因為這個洋玩意麼?”
桂先生笑而不答。
玫夫人喜歡小孩,是街坊四鄰都知道的事情,每次阿良來,玫夫人都會悄悄的塞幾塊裹著花花綠綠紙張的糖給他。
只是長大以後的阿良,不太敢接近玫夫人家了。
桂先生離世以後,玫夫人就好像有點···變了。
如果不是陳老爺說“你是玫夫人看著長大的,伱去請,總好過我去請。”的話,他也不敢去。
於是他就去了。
畢竟,主僕情深嘛。
···
玫夫人摸著陳老爺家中客廳擺放著的鋼琴,手指在琴鍵上掠過,未曾摁下。
她不是不會彈奏,只是沒有那個人在身邊。
佳佳原來是舞廳頭牌歌女,看中了陳老爺的錢,就成了陳老爺新納的妾,也即是第四房姨太太。
因希望家中和諧,便希望妻妾能情同姊妹,所以妾便被稱為了姨太太,
玫夫人看著四姨太高高隆起的肚子,將手輕輕撫在了衣服上。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收回了手,玫夫人對著陳老爺說道。
四姨太的臉色變了。
陳老爺不明白玫夫人這話什麼意思。
玫夫人只是笑笑,打量了一眼四姨太。
不說話。
——
沒人知道玫夫人這一身本事是哪裡來的,桂先生問,玫夫人也只是笑笑。
玫夫人說:“小時候碰見了一個男的,他輕輕拍了拍我的頭三下,然後,我就有了這一身本事。”
桂先生以為玫夫人在說笑:“拍三下就這麼厲害了?你沒讓他多拍幾下?”
玫夫人認真思索了一下:“對啊,我怎麼沒想到呢。”
夫婦二人對視一眼,哈哈笑了起來。
···
玫夫人倒是見到了一屋子的人,那不乾淨的東西卻是沒見到。
陳老爺說四姨太平日裡經常去佛堂吃齋唸佛,怎的會招惹到不乾淨的東西呢?
玫夫人說佛堂裡供的佛也得信的人多才能靈。
四姨太有些不悅,想說點什麼話,但是耳邊卻傳來了竊竊私語聲。
她知道玫夫人有本事,便張了張嘴,不說話了。
玫夫人側耳傾聽著,但好像沒在聽他們說話。
聽完後,玫夫人笑笑。
陳老爺忙問玫夫人:“玫夫人···您有頭緒了麼?”
玫夫人將手指豎在了唇前,陳老爺不禁噤聲。
卻聽得玫夫人不緊不慢說道。
“到飯點了吧?多備五副碗筷。”
——
玫夫人做菜煮飯時都會做許多,桌子上也都會放五副碗筷。
桂先生初時雖然不理解,但也表示了包容。
玫夫人說:“它們五個小赤佬都是保護我的哩。”
桂先生忍俊不禁:“那個是髒話,不可以說的哦。”
玫夫人夾菜到五個空碗裡笑道:“但是它們確實都是小赤佬啊。”
因為“赤佬”在玫夫人家鄉那裡也有“鬼”的意思。
···
“呀,少備了一副啊。”玫夫人看著桌子上的碗筷道,她又看了看吃起來了的四姨太,搖了搖頭,“算了,別備了,備不過來了。”
陳老爺問著玫夫人:“玫夫人,您這是什麼意思?”
“你們要我驅的,就在她肚裡。”
陳老爺手裡的筷子掉在了地上。
四姨太沒答話,只是自顧自的吃著,她抬起了頭,嘴裡的東西還沒嚥下去,腮幫子高高鼓起,對著玫夫人笑了起來。
像個小孩。
陳老爺有些顫抖,關切的接近四姨太。
但是四姨太卻惱怒的推開了陳老爺,繼續刨著碗裡的吃食。
玫夫人只道可憐,末了又說。
“生下來就沒吃過東西,活活餓死了,難怪像條護食的小狗兒,當媽的人,也能如此狠心啊,這不,報應不就來了麼?”
四姨太的臉上,青白輪轉,連同輪轉的,還有面容。
時而女人,時而小孩。
那小孩的臉,還不重樣。
“還不止一個呢,可憐啊,狠心啊。”
玫夫人搖著頭,將筷子倒插在了最大的燒雞上。
她唸叨著。
“吃吧,吃吧,吃飽了,好上路。”
——
秦西涯回過了神,畫面離消,真的是一部很引人入勝的“電影”,雖然不甚明晰,但那種“破碎感”的罅隙間充斥著對於‘劇情’猜測的遐想。
他個瞎子也看的津津有味,只是斷了,斷在了不上不下,不高不低的地兒。
像是小說裡的“斷章”,讓人恨得牙癢癢。
他牙也癢癢,卻還在回味,
戲臺上的《霸王別姬》也唱到了最後一折,直至謝幕。
瞎子抱著琵琶,身邊樂班子的成員們各自咧嘴,那後臺討論的兩個“人”也不見了。
戲曲謝幕,瘋狂的戲迷們扔著花束,少女喊著。
“陳老闆!陳老闆!再來一折呀!”“段老闆啊我們愛你呀!”···
兩個角兒一個扮虞姬,一個演霸王,假霸王假虞姬一一還禮。
樂班子們已經下了臺。
沒太多人會注意到顯眼卻又不惹眼的樂班子們,就算注意到,也只會看到那個閉著眼彈琵琶的瞎子,原因無他,因為瞎眼。
某個啞口的少女捧著花,想要送出,卻害羞不敢。
瞎子注意到了那遲疑的女孩,卻沒太過注意,畢竟,她只是沒說話···哦,她也不會說話。
秦西涯下了臺,將琵琶包好,背在身後,向著戲院外走去。
身著碎花無領襖裙的老年婦女等候在外,半白的頭髮挽成了髻,年約六七十,臉上也生出了老年斑,可卻讓人覺得她僅有四十幾許。
“伢兒,該回家了。”女人慈祥的說道。
“我知,玫姨。”秦西涯不自覺脫口而出,“夜晚飯食乜嘢?(晚上吃什麼)”
他是‘觀眾’,也是‘角色’,方才有翻譯,所以是普通話,但現在的粵語,卻是明確知曉其含義的。
“食乜嘢?飲骨頭湯先啦(吃什麼?先喝骨頭湯啦)。”玫夫人輕笑,而後看向了瞎子身後,調侃了一句,“系(聲同“hei”嘿)靚女仔嘅(是漂亮小姑娘哎)。”
瞎子回過了頭。
那個啞口的姑娘抱著花,似乎下定決心後追了出來。
將花捧給了瞎子,拽過了秦西涯的手,一筆一劃寫了起來,有些生澀,就好像死記硬背下來學會寫的字一樣。
“你的琵琶彈得很好聽,我很喜歡。”
瞎子怔住,
旋即,
泣不成聲。
玫姨搖頭,無奈又哀傷,低聲吳儂軟語:“前世之因啊,唉。”
啞女不知所措,徒勞無功的為瞎子擦著眼淚,焦急的想要讓瞎子別哭,可說不出話。
鈴鐺走的時候,瞎子沒哭,可能是因為他知道鈴鐺魂魄仍在,他也堅信能夠和她再見的緣故,他有許多理由說服自己不去傷心。
但,鈴鐺的確是死了啊,忍受死亡的痛苦,又還要忍受孤寂,在等待的時間裡···她,要等待多長時間呢?
過去種種浮上心頭,淚水後知後覺,此刻,他將那時沒哭出來的傷心一併嚎啕了出來。
“讓他哭吧,哭出來會好受些。”玫姨微微笑著,又心疼的看著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