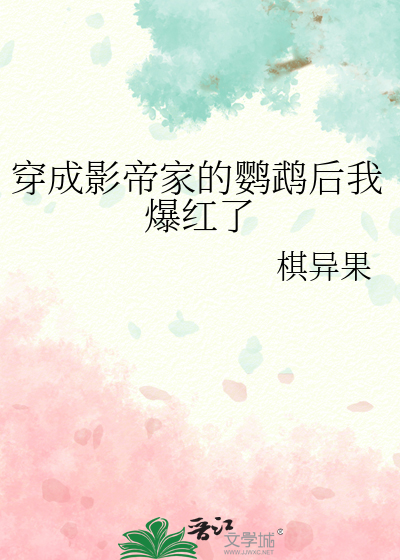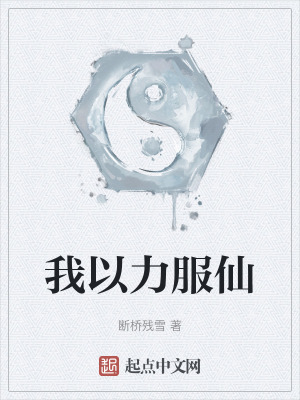安渝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絕症?
蕭惟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謝無猗還不到十八歲,她的身手那麼好,精神那麼足,怎麼可能會得了絕症呢?
花飛渡的聲音仍在繼續,蕭惟只覺得他已被一片冰雪覆蓋,寒意徹骨,茫然無依。
“這是種很罕見的病,患病者會漸漸失去感官。起初是對冷熱不敏感,進而蔓延到全身,四肢麻痺,使不上力。最後……”
花飛渡垂下眼睫,喉頭哽咽,蕭惟忍不住追問道:“最後會怎樣?”
“最後身體無法自主活動,意識雖然清醒但不能言語,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原本能掌控的一切抽離開來,”花飛渡頓了一下,緩慢道,“藥石無救,只有等死。”
日月西沉,凡人難逆。
蕭惟胸口劇震,猛然想到大婚第二日謝無猗的話。她說她眼中的日出日落和月出月落是一樣的,都不可擋,不可追。
她說得輕描淡寫,卻又那樣蕭索寂寥,原來是這個意思。
蕭惟雙手交握在一起,艱難地問道:“那她已經發病了嗎?”
花飛渡搖搖頭,“還沒有,她現在只是有輕微的症狀。不過這種病沒有病因,受到一些刺激就有可能迅速發展。”
“刺激?”蕭惟心中陡然升起疑懼。
“心緒不穩,或者……”花飛渡表情變了又變,“其實她原本應該遠離水的。”
蕭惟一下子記起萬春樓後院發生的那一幕,不免有些責怪謝無猗,她怎麼一點都不愛惜自己的身體?明知道要離水遠點,還敢在池中撲騰。
難道喬椿的清名比她的命更重要的嗎?
“那……如果發病,她能活多久?”
“三五個月都有可能,多數人能活一年,最長的也不超過五年。”花飛渡穩住心緒,看向蕭惟的目光中多了幾分憐憫,“殿下,您的大恩我們無以為報,可從古至今身患日月沉的人沒有活到三十歲的,我告訴您這些也是不想讓您陷得太深。”
蕭惟自嘲地彎了彎嘴角。
陷得太深嗎……晚了,他已經放不下了。
放不下人前假作恩愛時那隻與他緊緊相牽的手,放不下在絕境中那個為他破開生路的身影。說不清道不明地,蕭惟早已把她裝進心裡,融入骨髓。
“我相信殿下對我們丫頭是真心的,但……她本無永壽,殿下是天潢貴胄,不可能只守著她一個人。”花飛渡撤步跪下,“殿下,我知道這麼說很殘忍,但您得承認這是事實。等一切塵埃落定,請殿下放她走吧。”
讓她趁著清醒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多走走不一樣的路,直到無悔地,體面地和她熱愛的山河日月告別。
蕭惟定定地看著花飛渡,半晌彎腰將她扶起。他當然明白花飛渡是好意,可也只有蕭惟自己清楚,在這樁婚事裡,謝無猗賭的是喬椿的清白,他賭的卻是自己的心。
“讓小猗來決定吧。”
我……願賭服輸。
說罷,蕭惟便讓花飛渡先去休息,一個人坐在謝無猗的床前。
她睡熟的時候呼吸向來很輕,蕭惟一直以為是她內力深厚的緣故,現在看來恐怕和日月沉也有關係。
謝無猗蜷縮在被衾裡,除了時不時皺皺眉頭,整個人一動不動,像一隻被困在蛹中的蝴蝶。
她該是累極了,連蕭惟握住她的手都沒有察覺。
謝無猗的手指又細又長,指縫裡隱著許多深深淺淺的疤痕和薄繭,應該都是練習蒼煙時留下的。
蕭惟看著看著,忍不住俯下身,蜻蜓點水般吻了吻謝無猗的指尖,而後輕輕釦住。
在花飛渡告知謝無猗的病以前,蕭惟從沒想過要將她永遠留在身邊,因為他早就知道謝無猗不屬於皇宮,甚至不屬於澤陽。
她應該在千山萬水間留下足跡,做自由自在的蝴蝶,無拘無束的鸞鳳。
而他,只需要在她身後默默看著就好。
可現在……
蒼天判了她死罪,誰都攔不住。
如果是這樣,他還要放她離開嗎?
讓她無聲無息地從視線中消失,在一個不為人知的地方孤獨著沉默著死去,這樣的事蕭惟連想都不敢想。
天光大亮,蕭惟的腦子卻越來越迷糊,不一會也伏在一旁睡著了。
謝無猗不知道自己到底睡了多久,再次睜開眼時,只見蕭惟握著她的手,另一手撐著頭,眉目間寫滿了疲憊。金色的暖輝從窗外斜斜灑下,沿著他的鼻尖和指節輕盈躍動。
她不覺露出淡淡的微笑。
謝無猗稍側過頭,不想這輕微的動作立即傳導到蕭惟掌中。他悚然驚起,見謝無猗已經甦醒,忙向前挪了挪身子。
“怎麼樣,好點了嗎?”
“我沒事。”謝無猗收回手,支撐著坐起,“殿下,聞逸……”
“聞逸我已經看住了,你放心。”蕭惟凝視著謝無猗,輕聲埋怨道,“你也是,好歹合作一場,我們也算是朋友,怎麼病得這麼厲害都不告訴我?”
謝無猗不由愣住,她仔細看了看蕭惟那心痛不已的表情,就猜到花飛渡已經把她身患日月沉的事告訴蕭惟了。謝無猗嘆了口氣,不以為意地笑道:“女人嘛,總有身體虛弱的時候。花娘和殿下說那些做什麼,也太小題大做了。”
好像是為了讓蕭惟相信她的話,謝無猗將左臂上的蒼煙在手中快速翻轉幾圈,又勾住手指朝他的手背上敲了兩下。
“溫的。殿下看我這不是好好的?”
看著藍紫色的熒光在掌中輕閃,半透明的羽翼棲息在謝無猗的腕上,蕭惟心中愈發酸澀。他苦笑著揉了揉謝無猗的頭髮,“一切都快結束了,小猗不需要再拼命了。”
謝無猗眨著亮晶晶的眼睛,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
她已經查了兩年,如果真到了查無可查的地步,任何結果她都能接受。
眼看面前鋪開一條康莊大道,無論此前經歷過什麼都值得。
謝無猗垂下頭,無意間看到了蕭惟手上的傷痕。她心中莫名地一顫,忙搬過蕭惟的手,“殿下受傷了?是在江南莊傷到的?”
蕭惟頓了頓,隨口道:“沒有,路上不小心劃的。”
謝無猗靠得實在太近,蕭惟甚至能感覺到散逸在掌心的她的鼻息。陽光疊加起燭光,在謝無猗的鼻樑一側投出陰影,也照亮了兩叢濃密的金色絨毛。
蕭惟的耳根忽然熱熱的,他拼命搜尋著其他話題,以掩飾這不合時宜的窘迫,“江南莊已經炸燬了,你先吃點東西,一會……要不我們一起去看看?”
這一問果然奏效,謝無猗的注意力立時被轉移,“真的?可以去?”
其實自破解江南莊的機關後,謝無猗就想找機會再回去一次了。褚餘風雖已難逃罪責,但他們始終沒有抓到褚瀚的把柄,一個拎不清的範蘭姝也不能作為人證。
一想到褚瀚使了那麼多絆子,差點讓他們死在臥雪莊,謝無猗的牙根就直癢癢。
更何況,她當真對江南莊的設計者十分感興趣。
“當然。”
蕭惟亦挑眉,擺出慣常那般恣意慵懶的表情,不懷好意地笑道:“不給褚小哥點顏色看看,本王猶嫌不足。”
幾人墊了肚子,蕭惟便命春泥趕馬車,一行人結伴返回江南莊。快到時,謝無猗想出去疏鬆疏鬆筋骨,蕭惟拗不過她,只好下車陪她步行,讓春泥與花飛渡在後面慢慢跟著。
夕陽緩緩隱沒山後,二人並肩走在寂靜的小路上,周遭只有腳踩落葉的“沙沙”聲。
蕭惟抬頭看向那道金紅色的光芒,又想起謝無猗的病,不由得握緊雙手。
如果可以,他願意付出一切代價換她康復,讓她隨心所欲地周遊四海。
她的人生根本不該止步於此。
察覺到蕭惟此刻的失落,謝無猗坦然地笑了,“殿下不必憐憫我。我這個人呢,別的事上或許糊塗,可唯獨這點不會犯傻。”
她見過太多如蕭惟這樣的眼神。
謝無猗專注地在樹葉堆上印出自己的腳印,口中調侃道:“不就是一個日月沉嗎,說不說又如何呢?不過就是讓知情人感嘆一句,你看那個小姑娘多可憐,怎麼保養都活不到三十歲,然後該做什麼做什麼去。”
每個人都在走向死亡,可身患日月沉的人不一樣,他們清楚地,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壽數,也看得見生命的盡頭。
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比其他人更平和,更敏銳,也更能感知到世間的苦難。
蕭惟偏過臉,靜靜地凝望著謝無猗。
原來別人只會憐憫嗎?除了她的家人,再沒人心疼過她嗎?
謝無猗隨意翻動著蒼煙,任清冷的波光在指尖流動,“人哪有不苦的。與其不斷重複所謂的苦難,還不如多做些想做的事,總不枉來這世上走一遭。”
她話語平靜,彷彿是在談論一個陌生人。
可就是這樣明晰到令人心痛的理智,讓蕭惟忽然好想抱抱她,抱抱這個讓他魂牽夢繞的女孩。
他總是天不怕地不怕什麼都敢做,可唯獨面對謝無猗,蕭惟就像個茫然無依的孩童。
“那……此事了結之後,你怎麼打算?”
蕭惟落後半步,深深望著謝無猗的背影。即便再恐懼,再患得患失,他還是得問她的意願。謝無猗不是任何人的附庸,如果她執意要走,那他……就再試一試,看還有沒有別的辦法能讓她留在自己身邊。
多一天也好。
說話間,二人已經走到江南莊。由於謝無猗取靈機盒時觸發了機關,整個莊子早已炸成一片廢墟。謝無猗站在一堆碎瓦上,對著遮住夕陽的遠山輕聲呢喃。
“和離吧。”
蕭惟的心口一陣刺痛,謝無猗轉回身,風吹起她臉頰兩側的頭髮,絲絲入骨。
“殿下,我不是謝九娘,我是喬蔚。”她挑起唇角,笑容十分慘淡,“其實我是個很自私的人,本來也是在利用殿下的身份查案。是我說謊在先,難道還能一直頂著謝氏女的身份做你的王妃嗎?”
可我不介意。
蕭惟上前一步,謝無猗卻像知道他要說什麼一樣抬手攔住他的話。
“殿下,我已經欠你很多了。我可以用任何方式償還,唯獨不能玷汙燕王妃的名號。”謝無猗的目光寂如古井,“我們都知道那張婚書會作廢,所以,還是儘快放手的好。”
在她心裡,蕭惟是張揚的,也是純粹的。無論他披著什麼偽裝,謝無猗都相信他還是他們最初相遇時的模樣。
這樣一個蕭惟啊,她怎麼能用感情做交易呢?
蕭惟雙手冰涼,雖然早就預想過謝無猗會這樣回答,可當真真切切地聽到這些話時,他還是心痛到無以復加。
謝無猗心思剔透如冰,恩怨一向分明,她下定的決心無人可以更改。
本就是他一廂情願,他還能怎麼辦呢。
蕭惟別開頭,氣息有些不穩。他強自定了定神,指著江南莊的廢墟問道:“先說正事吧,這裡你能看出什麼嗎?”
天邊泛起濃濃的墨藍色,謝無猗掃視一圈,機關不是被炸燬就是沖毀,實在沒什麼研究價值。現在他們只能確定,是想讓謝無猗查知真相的人實力更勝一籌。
“有一點很奇怪。”謝無猗踢過腳邊的瓦片,皺眉道,“費盡心機造了這麼複雜的一間密室,難道就是為了關著聞逸嗎?”
“自然不是。”
蕭惟雖然平時不問政事,但這並不耽誤他對朝中瞭解頗深。蕭惟想了想道:“如果是兵部勾結外人做一些暗地裡的交易,這裡的鬼莊傳說和重重機關倒是可以很好地保護他們。”
謝無猗深以為然。蕭惟曾說江南莊像武庫,再加上褚餘風兵部尚書的職銜,他們不得不多想一層。
“小猗,”蕭惟走到謝無猗身邊,附耳低聲道,“我們得掌握主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