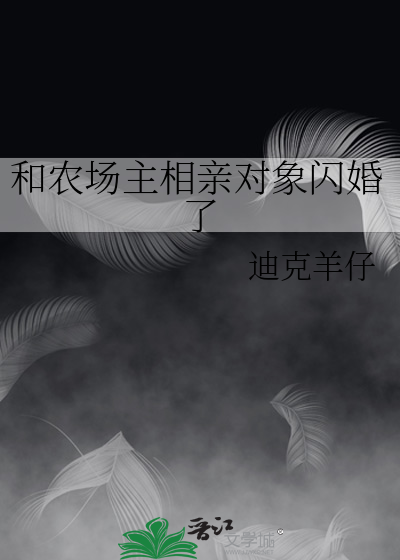森木666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北狄公主挑選夫婿一事乃昭元帝金口應允,凡被她相中者,無論尊卑貴賤,都需承下和親相公的身份。
聖意難違。
鴉雀無聲的寶津樓內立時有竊竊私語傳開,半晌又重歸寧靜。眾人眼觀鼻鼻觀心,見昭元帝神色複雜,皆不敢輕易開口。
——大鄴或許可以失去一個丞相,但昭元帝絕不允許北狄得到柳柒。
方才毛遂自薦的青年才俊們紛紛轉頭看向端坐在左前首的柳丞相,那張俊美如玉雕的臉上窺不見半分波瀾,彷彿公主相中的另有其人。
柳柒起身行至殿中的紅氈上,對述律蓉蓉泰然揖禮:“公主機敏聰慧、英姿颯爽,蒙芳心相贈,微臣感念於懷。然臣淺陋鄙薄、德行有虧,不敢妄攀公主,有損公主名節。”
眼角餘光裡,雲時卿正悠然自樂地撥弄玉碟裡的果脯,與四周膠著的氣氛格格不入。
柳柒還記得昨晚小廝彙報給他的訊息,彼時他誤以為雲時卿和北狄公主暗通款曲是想勸服公主擇二殿下為夫,為三殿下滌清儲君之爭的對手,沒想到此人真正的目的竟然是他。
揚湯止沸,莫若去薪。對付勢單力薄的二殿下的最佳方法,便是折其羽翼,順便也拔除了眼中釘、肉中刺,雲時卿這一招,倒稱得上是“一石二鳥”。
公主被拒,未免失落,卻還是佯裝鎮定地問道:“柳相何出此言?”
無數道視線齊刷刷地落在柳柒身上,就連雲時卿也忍不住放下銀匙,想聽聽這位丞相大人會如何解釋。
柳柒側首,見那人面含淺笑、幸災樂禍,遂溫溫和和地說道:“柳柒入仕十載未娶,實有難言之隱。只不過此事汙濁下流,不該示之以眾。”
男子的難言之隱,無外乎不能人道。
果然,眾人都被勾出了好奇心,昭元帝立馬出面打圓場:“既是難言之隱,柳相就不必細說了。”
但公主卻不想放過他:“蓉蓉好奇,還望柳相告知一二。”
柳柒看向雲時卿的眼神漸漸變得複雜,遲疑了幾息才開口:“昔年會試之前,微臣曾與雲相有過一段無法宣之於口的過往,後因種種原因而不得不分開……”
這段“無法宣之於口的過往”點到為止,柳柒輕嘆一聲,語氣稍顯落寞,“柳柒之欽慕,譬如時卿者。縱然如今與雲相再無糾纏,但我所喜所好之人,須與雲相有幾分相同。公主的良人絕非微臣,還請公主三思。”
雲時卿嘴角微僵,彷彿聽見了一個天大的笑話,而沉寂已久的寶津樓卻因為柳丞相的一番剖白開始沸騰。
“這這這這……怎怎怎怎……誒!陸尚書!你為何用頭砸桌?!”
“老夫吃醉酒了,想砸醒自己。”
“原來柳相喜歡雲相這類的。”
“他們……居然……那什麼……”
“說他二人有仇我信,可若說有情……簡直是無稽之談!”
“柳相清廉剛正,何時撒過謊?”
“難怪兩位丞相至今未娶,原來這當中竟有如此震撼的一段往事!他們現在之所以水火不容,想必和那段過往有關吧,正所謂愛之深則恨之切……”
有人借酒壯膽,摸到雲時卿身旁好奇問了一嘴,雲時卿眼風掠來,皮笑肉不笑,那人怯怯離去,再不敢多言。
事已至此,這段情緣真假與否已經不重要了,眾人先入為主,認定斯文儒雅的賢相不會說謊,更何況柳柒說得情真意切,不顧清譽也要吐露心跡,雲時卿若在此刻辯解什麼,毫無疑問會被推上風口浪尖,甚至坐實這段過往。
他淡淡地看著柳柒,臉上再無閒適,只餘一絲不達眼底的笑。
述律蓉蓉擰緊了眉,她還未來得及說話,便聽見席上有人開口,一把渾厚的嗓音足以壓下殿內的議論:“早就聽聞大鄴朝風氣開放,如今有幸一瞻,果真不同凡響。不過我們草原兒女成婚講究的是心意相通,既然柳相對女子並無興趣,公主,擇選駙馬之事還請從長計議罷。”
昭元帝輕嘆一聲:“朕也是剛剛才知曉柳相他……”
一旁的貴妃見狀,當即引開話鋒,說道:“今日乃上元佳節,內侍官早在金明池畔布好了煙花,公主若是得趣,不妨移步水心五殿,與眾人共賞。”
述律蓉蓉無心再議和親之事,便和昭元帝以及貴妃等人前往水心五殿賞燈。
翌日早朝,平靜祥和,百官尚沉浸在昨晚的風波里,難得沒有爭吵。
散朝後,柳柒與幾位大人來到宣德門外,正互相道別時,一道俊拔的身影自左掖門行出,紫色官袍在晨風中獵獵翻飛。
柳柒裝作沒看見,踩著積雪負手前行。
還未走出兩步遠,身後便傳來了一陣清緩的嗓音:“柳大人。”
寒風凜冽,冷意浸骨,各部官吏行色匆匆,忙不迭聽見這聲呼喚,紛紛駐足凝目,彷彿那人叫的正是他們的名字。
柳柒雖未停步,但速度卻減緩了不少,待雲時卿走近時他才客客氣氣一笑:“雲相。”
雲時卿說道:“時候尚早,柳大人還未用早膳,不如與在下前往雲生結海樓吃碗熱乎的羹湯暖暖身子。”
柳柒回絕道:“我與雲相不熟,就沒有必要吃羹湯了。”
雲時卿似笑非笑:“既不熟,為何還要捏造是非,把我說成你的舊情郎?”
雪地之中人來人往,柳柒回頭看了看,那些試圖往這邊靠近的官員們忽然間做鳥獸散,周圍頓時清靜了不少。
雲時卿嗤道:“怎麼——心虛了?昨晚你當著那麼多人的面慷慨陳詞時可不見你眨一下眼。”
柳柒頓足,淡淡地看著他。
宮門外的人影彷彿在這一刻陡然增多,無數道視線齊刷刷射了過來。
幾息後,柳柒默然轉身,抬步往自家輿轎走去。
雲時卿卻一把扯住他的袖口,質問道:“我的清白被毀,聲譽掃地,你就打算這麼走了?”
宣德門外頓時鴉雀無聲。
柳柒的目光掠向那隻指節修長、骨線明晰的手,不由失笑:“待我回去之後立馬修一封婚書,擇個吉日便迎你進門,如何?”
雲時卿也展顏一笑:“柳大人一言九鼎,可莫要失信。”
柳柒拉下嘴角,扯回衣袖後大步離去。
不出半日,兩位丞相大人的事蹟便在京中傳開了,又過了兩日,各大茶樓酒肆的說書人以此為噱頭,每一場評書都座無虛席,甚至連書坊也開始刊賣話本。
晌午,柳柒在書房內抄寫經文,貼身小廝柳逢叩門入內,從懷中取出一封拜帖呈遞過去:“公子,這是陸尚書差人送來的拜帖,邀您明日申時前往雲生結海樓一敘。”
柳柒接過拜帖壓在鎮紙下,見他沒有離開的意思,便問道:“還有何事?”
柳逢支支吾吾地說道:“今日京中各大書坊陸續刊印了不少話本,全是……全是公子和雲相的那些事。”
柳柒淡聲問道:“我和雲相的哪些事?”
香爐裡浸出幾絲白煙,嫋嫋娜娜,悠然浮蕩。
柳逢透過菸絲打量著自家公子,反覆斟酌良久,卻不知該從何說起。
柳柒很少見他這般不利落,又問:“都刊印了些什麼書?”
柳逢如實回答:“有《恨海情天錄》、《絕豔郎君孽緣傳》和《宿敵丞相惹風月》,其中《恨海情天錄》只印了第一話,售價十五錢;《絕豔郎君孽緣傳》已刊印至第三話,售價三十錢;《宿敵丞相惹風月》刊印至第二話,其內容略有些淫.穢,但卻是時下最受追捧的,有插圖的賣一百二十錢,無插圖則只需——”
“驛館那邊近來如何,可有動靜?”柳柒放下筆毫,沉聲截斷他滔滔不絕的回話。
柳逢識趣地不再提話本之事,應道:“述律公主從金明池御宴回來後就沒有離開過驛館,倒是那群膀大腰圓的使臣們每日都在京中走動,偶爾還會出入風月場所。公子放心,小人盯得緊,他們身邊並無可疑之人出沒。”
翌日申時,柳柒前往雲生結海樓赴約。
雲生結海樓是一座酒樓,此樓臨汴河而建,內裡結構仿照江南園林修砌,青磚白牆、山環水旋,在京中頗負盛名。
而酒樓裡面的佈置更是別具風格,按照四時節令不同,分出了“梅”、“蘭”、“竹”、“菊”四院,每院各設六間雅室,竹簾挑窗,翠屏錦繡,甚得雅趣。
當然,這樣富貴又不失風騷的酒樓在京城裡比比皆是,雲生結海樓之所以更勝一籌,便是勝在酒樓裡的侍者。
這些貌美俊秀的姑娘少年們個個都會品竹彈絲,人人都善詩書墨畫,正好迎合了達官顯貴們。
久而久之,雲生結海樓便只招待權貴,尋常客人絕無機會踏足此地。
“公子,雲生結海樓到了。”
翠幄青綢的車簾被人挑開,冷風裹挾微雨灌入馬車內,捎來幾分刺骨的寒意。
柳柒攏緊墨藍大氅,不露聲色地下了馬車,柳逢立刻撐開一柄漆花的油紙傘,緊步跟在他身後。
還未走出幾步,就聽柳逢說道:“那好像是雲相的馬車。”
柳柒回頭瞥了一眼,而後撩袍邁上石階:“你是第一次見他來這裡嗎?”
柳逢悻悻然收回視線,隨主子一道進了酒樓。
到正廳後,柳逢便不再前行,隨後由兩位美貌的侍女領著柳柒沿遊廊往東而去。
穿過幾道月牙門,又踏上幾座流水小橋後,終至梅院的第二間雅室。此處植有幾株碗口大的綠萼梅,暗香滿園,浸人心魄。
今日送拜貼之人是吏部尚書陸麟,同行的還有幾位大臣,見柳柒到來,紛紛起身揖禮。
幾人圍坐在黃梨木鏤花方桌前,紅泥爐煨著的花雕酒熱辣清香,與玉盤裡的果脯糕點的甘甜相融,引人垂涎。
一杯濁酒下肚,一陣寒暄後,陸尚書起了個話頭:“再過幾個月二殿下就要行冠禮了,陛下卻遲遲不立儲君,這可如何是好。”
另一人說道:“儲君關乎國祚,歷代君王都無比慎重。而咱們陛下重情義,心裡一直惦記著先帝的遺腹子,所以才會空著太子之位。”
“幾位殿下之中,唯二殿下仁厚親民,只可惜殿下母族式微沒落,難以在朝中立足。”
“對了,上元節那晚柳相為何要與雲時卿扯上關係?如今此事傳得沸沸揚揚,有損柳相的清譽啊!”
話鋒落在柳柒身上,他不得不給出解釋:“述律公主入京之前曾接觸過雲時卿的人。”
有人不解:“這與洗塵宴有何關係?”
陸尚書蹙了蹙眉,很快就反應過來了:“他定是想利用和親的名義把二殿下送出關外,然後扶持三殿下坐上儲君之位。不過此舉太過冒險,陛下不會輕易送皇子和親,所以雲時卿便與述律公主串通一氣,斷二殿下羽翼,擇柳相為夫。”
一旁那位大人扼腕道:“可是柳相也不必拿自身名節做賭,如今此事傳得沸沸揚揚,柳相以後如何成家立室?”
柳柒淡淡一笑:“事出從急,我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他們這種深陷黨派之爭的人,成了家反倒是累贅。
廊下風聲陣陣,吹得護花鈴叮噹作響。短暫的沉吟後,棟樑們又拋開話題談了些興致之事,末了陸尚書眉開眼笑地舉起酒杯:“諸位,請!”
幾人紛紛回敬。柳柒一口熱酒還未入喉,忽覺丹田內隱若有爐火在炙烤,他只當是花雕醉人,並未在意。
但很快,這股火愈燃愈烈,似被勁風勾動,遊竄至四肢百骸。
周身氣力彷彿在這一刻脫了骨,酒杯倏地從他手中滑落。
“柳相?”
“柳相這是怎麼了?”
柳柒耳畔一陣嗡鳴,已分不清是誰在關切擔憂。
他知自己中了陰招,可眼下這幾人均是信得過的知交同僚,斷無加害他的可能。
少頃,柳柒強忍不適起身請辭:“在下身體略感不適,恕狂駕之罪。”
眾人並未阻攔,叮囑幾句後目送他離開了雅室。
風雨漸盛,吹打著遊廊裡的護花鈴,叮鈴叮鈴,宛如鬼魅鳴嚎。
柳柒離開雅室後並未走出梅院,而是推開了遊廊盡頭的那扇門。
身體的異樣來勢洶洶,若是以這副模樣出去,定然比當著滿朝文武斷袖更加可恥。
沉浮官場多年,柳柒見過的腌臢手段數不勝數,卻沒想有人膽大如斯,竟敢對他下手。
梅院裡每間雅室的陳設不盡相同,柳柒體如爐火,炙熱難捱,他虛軟無力地繞過屏風行至暖閣,旋即解開大氅,掬一捧室內蓮池裡的清水澆在臉上,而後靜坐,調理內息。
恍然間,屋內浮現出了一股濃烈的香氣,如花似蜜,邪媚至極。
柳柒調息良久卻不見半分成效,身體漸漸骨軟筋麻,他解開衣襟,整個人無力地伏在貴妃榻上。
那股邪香愈來愈烈,攪動著體內的慾念。柳柒呼吸疾熱,唇若施脂,眼似桃花,連指節都染上了一層荷色。
正這時,雅室的房門被人推開,繼而有腳步聲入內。
柳柒輕掀眼簾,見屏風外佇立著一道人影。
屋內光影稀疏,那人狐裘錦衣,玉冠束髮,一身氣度修竹也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