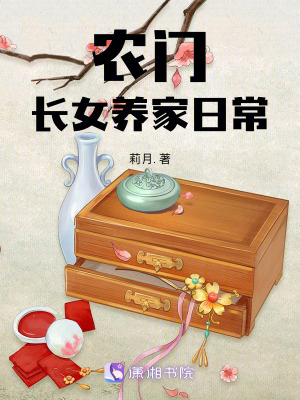第233章你是誰(一)
桑家靜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啪!
啪、啪、啪——
鄭曲尺這頭正專心致志地思索著事情,卻聽到旁邊兩人跟身上有跳蚤似的,東扭西扭,你一巴掌、我一巴掌地在身上拍打,製造噪音。
「安靜些。」
「不行啊,這什麼樹啊,夜蚊多得要死,我身上都癢死了。」小三小聲抱怨道。
小七也低悶地「嗯」了一聲。
小三忽然發現鄭曲尺好像一點事兒都沒有,他心態失衡了:「不是,怎麼它們只叮我們倆兄弟,難道這些蚊子還分人欺負不成?」
鄭曲尺也是服了他們,她從身上的斜挎包裡找了找,然後掏出兩塊削成了薄片的木頭扔給他們:「揣著它,蚊子自然就會遠離你們了。」
「這是啥?」小三將它攤在手上,翻來覆去地看。
小七更是湊到鼻子處嗅了嗅,感覺味道還挺好聞的。
鄭曲尺點開他的腦袋,別叫他的嘴巴碰到:「這是我做的燻蚊香樟木,浸泡了一種特殊的藥水曬乾的,你們別誤食了,它日常佩戴在身上,可以拿來驅蟲防蚊。」
他們一聽就明白這是個好東西,立馬揣進兜裡拍穩妥了,兩張臉如出一轍地咧開嘴角嘻嘻笑道:「謝謝了。」
見兩人終於消停了,鄭曲尺這才轉回頭繼續盯睄,但是就耽擱這麼一會兒功夫,下方就發生了巨大變故。
星月掩閉,黑比漆,嘯聚惡風灌入曲道,人馬漸近,或許也是感應到了什麼風雨欲至的危險氣息,他們夜露匆忙的腳步,漸漸遲緩下來。
但是任他千般謹慎小心,一旦沒有及時止步,便會陷入早就埋伏的惡狼圍獵場。
只見山坳的兩邊長坡上,猝不及防滾落下許多巨石,由於光線昏暗,底下的人聽到了動靜,卻一時沒法即刻分辨出逃離的方向,隆隆隆的砸落伴隨著石子與塵土,這一下嚇得馬驚嘶鳴,人聲雜亂。
「快,快朝前跑!」
後邊的路都被這些大石頭跟一半滾下來的灰土黃泥給擋住了,人能走,但馬車卻難以越過,只能選擇繼續朝前邊跑。
他們鞭打著馬匹,想趕緊逃離這一片災難區域,然而他們卻不知道,這卻是正中路匪的心意,他們正毫無知覺地疾速駛進了路匪的包圍圈中。
一條套繩倏地收緊,套住了馬腿,更多的人踩到了路匪們提前佈置下的陷阱,當即是人仰馬翻,同時轟隆的爆炸聲不斷響起,火光大作,濃煙滾滾,更是造成了一片亂糟糟的景象。
這山壁之下,最寬有十幾米、最窄僅有一條寬幾米左右的小道,緊貼山壁,十步三轉,蜿蜒直上峰巔,他們想要從這裡逃走,很難。
因為這一條道就是路匪們精挑細選之下,專程用來「吞食」的血盆大口,這條小道就是「喉管」,他們跑得越慌亂,就越是自投網羅。
夜裡無論是嵬嵬的林間還是巍巍的山谷,都是寂靜而漆黑,唯獨這一塊兒地界集中了所有光熱與喧囂。
如此驚險又駭人的動靜之下,馬受驚,人受傷,馬車自然就是一種累贅存在,直接震得馬車內的人,不得不從車內爬了出來,再由侍衛們攙扶著下車。
鄭曲尺就在斜上方看著,直到她看到馬車內逃出來的人時,不由得驚得瞪大了眼睛。
怎麼會是、是他?!
那有別於正常男人的陰柔作派,那胖墩墩又尖聲尖氣的男子,不正是她前不久才打過交道的大太監總管嗎?!
鄭曲尺人被驚麻了。
臥槽,他們這些路匪的膽子是真肥啊!他們究竟知不知道這些人是什麼來歷啊?!
一個鄴王的親信,一個是朝中重臣,要真是叫他們幹成了這一票,那還得了?!
只怕從此他們福縣將永無寧日了!
「你們知道他們是誰嗎?」鄭曲尺問小三跟小七。
小三轉過頭,對上鄭曲尺此刻異常嚴肅的神色,莫名有些心虛感:「興安哥說了,這些人是從有錢的地方來的,看穿衣用度就知道富得流油,但具體他們是誰,我們也不大清楚。」
鄭曲尺:「……」
她內心尖叫咆哮——啥都不知道,你們就敢去打劫?!
一個盛安公主在他們福縣遇上路匪失蹤了,這事就已經叫鄴王火急火燎的派了他家大總管過來問責了,這還是情況不明確、只是猜疑的情況之下。
而這一次,事情明明白白、毫不含糊地重臣倆都在福縣被劫得連條褲叉都不剩,那他們長馴坡的營寨的人豈不又成背鍋俠了?
不行,她得在事態發展到更嚴重之前,阻止他們。
「興安現在在哪裡?」
她徒然站了起來。
小三跟小七一驚:「你幹嘛?」
「不能叫他們打劫這夥人,不然會出大事的!」鄭曲尺緊聲道。
小三惶然問道:「大事?什麼大事?」
兩小隻很是茫然,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的嚴重性。
「現在沒時間解釋了,咱們還是趕緊去找人。」
——
這頭鄭曲尺正叫著小三小七帶著她一路找了過去,另一頭眼見一切進行得十分順利,對方人員折損得厲害,又被困於小道之中,路匪們這才從暗處大搖大擺地衝了過去。
他們是真的囂張,幹這種犯法劫匪的事,卻連臉都懶得遮一下。
大太監總管從馬車上被扶到地上,一直還驚魂未定,不知道是誰要害他們,直到這一群路匪們出現。
他眯了眯細小的眼睛,打量了一番這些人的窮酸裝束打扮:「你們是什麼人?!」
路匪眼神狠狠一瞪,舉起刀來:「識趣的話,就趕緊將你們身上值錢的東西都通通交出來,否則我們就殺了你們!」
李大人被人護在後方,他扶正了頭冠,霎時間明白過來:「你們就是路匪?!」
「哈哈哈哈,兄弟們,他們這才認出咱們是哪一路的人啊,看來還是見識不行啊。」路匪們嘲笑道。
大太監總管惱怒道:「你們知道我們是誰嗎?」
他想說出自己的身份來威攝震住對方,卻沒想到這群路匪根本油鹽不進,一切只往錢上看。
「你是誰?你就算是天王老子在這兒,咱們也敢動手,少他媽的廢話,趕緊掏東西出來,要不然一會兒咱們兄弟親自動手,就少不了你們的排頭吃!」路匪凶神惡煞道。
「放肆,大膽!」
都到這會兒了,大太監總管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處境,還當自己是在宮裡被人捧著臭腳的高高在上。
「你才放肆大膽呢!」
路匪沒慣著他,直接就是一嘴更大聲、更兇狠的怒懟過去。
劉大人趕緊上前拉了一下大太監總管,他畢竟是搞文字獄的女幹佞,腦子正常情況下都線上,他明白這個時候千萬別激怒這些亡命之徒,既然對方求財,那最好的解決方式就是舍財保命。
他以眼神示意大太監總管先不要衝動,正所謂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這事兒沒完,遲早有一天,他們會叫這些路匪死無葬身之地。
「看來,還是這一位大人識時務啊,早這樣多好,乖乖地將錢全部掏出來。」興安勾唇一笑,招了招手,他們兇相畢現,紛紛掏出武器。
如今他們這邊的侍衛大多數受了傷,硬拼突圍著實艱難,劉大人忍著滿腔怒意,叫人將車內的值錢的東西都扔在地
上。
然而,路匪們還並不滿意:「你們身上的呢?」
於是,劉大人他們咬著牙,將身上的配飾與掛件取下,一併扔前。
這時,興安好似還是不甚滿意,他一雙深沉的眸子,如無機質的蛇瞳,在他們周身晃悠轉動一圈,嘴角噙笑道:「你們身上的衣物看起來也值不少錢,一併脫了吧。」
什麼?!
要錢就算了,現在連他們身上敝體遮羞的衣服都不放過!
簡直欺人太甚了!
大太監總管咽不下這口氣,不過就是區區一鄉下匪徒,竟也敢吃了熊心豹子膽,欺負踩爬到咱家的頭上?
他當即怒罵道:「都是婦人當道為禍患,如此大一個軍營寨鎮定在此,卻叫你們這些路匪囂張至此!」
剛趕過來救場,卻聽到大太監總管的一頓辱女感言:「……」
她就知道!
她就知道,這些人一旦發生什麼事情,從來都不會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或者就事論事,冤有頭債有主。
他們會遷怒,會責怪,會怨恨,會認為一切都是別人的錯,是別人害的,甚至現在連性別都能是一種錯!
「不肯脫是吧,那就讓咱們兄弟來幫你們吧!」
路匪們摩拳擦掌,一臉陰陽怪氣地打算上前動手。
而劉大人他們臉色漲得肝紅,既氣又慪,連連後退,甚至都考慮著要不就乾脆殊死一拼吧,總好過被人扒衣***至此,丟人至極。
「等等!」
鄭曲尺趕緊上前阻止。
她還是來晚了,沒有攔下他們露面,如今這情況,水火不容之勢,分明就已經是將大太監總管與劉大人他們得罪狠了,此事也難以善了。
路匪忽聞這一聲喊停,與興安一併轉過頭去,卻見到了小三小七與那新來的「小鄭」一塊兒氣喘吁吁地跑了過來。
而「小鄭」臉上還撕了一塊布蒙上,她遮遮掩掩走到興安面前。
興安對她如今這鬼祟的模樣還挺好奇的,他道:「等什麼?」
路匪們也不明白她突然冒出來,喊「等等」是個什麼意思。
「我有幾句話,想與興安哥私下聊一聊。」鄭曲尺壓低嗓音道。
興安卻說:「沒瞧見我在辦正事?有什麼事,過後再說吧。」
鄭曲尺一把拉住他,隱忍道:「過後說,就遲了。」
興安好似聽明白了些什麼,他視線掃過大太監總管那邊:「你這麼著急趕過來,是為了他們?」
「不是……我……」她一時之間都不知道該怎麼解釋了。
路匪們皺眉看著鄭曲尺,而另外劉大人那邊的隊伍也一臉狐疑與驚訝地打量起鄭曲尺。
是一名女子……想不到路匪當中,竟還有女子的存在。
興安卻勸她死了這條心:「都進行到這一步了,我不可能會收手的。」
「現在收手,事情還有挽回的餘地。」她湊近他,想小聲地與他說一說對方的來歷與身份。
「哦,我看……你是覺得自己還有挽回的餘地?」他似笑非笑地看著她,下一秒,卻一把扯掉了她臉上的蒙面巾:「你遮著臉做甚?」
當面巾離臉那一刻,鄭曲尺腦袋一下就炸了,她本能地看了一眼太監總管的方向,然後反應過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轉過頭去,拿手一把遮住了臉。
「你摘我面巾做什麼?!」
她怒不可遏地質問興安。
她聲音咬得很小,生怕別人聽出她的原聲來。
然而,一切終究還是太遲了。
大太監總管先是神色古怪,眼帶沉思
,最後稍微回憶了一下,眼睛就瞪得像銅鈴似的,他指著鄭曲尺大喊道:「原來是你——」
「不是我——」
她用手擋著臉,立即反駁。
然而,大太監總管此時已經十分確認了:「就是你,想不到你竟然會跟路匪勾結到一塊兒,我知道了,就是你在背後搗鬼的吧,咱家絕對會將這件事情稟報——」
噗——
尖厲的聲音戛然而止,大量的鮮血不斷從大太監總管的喉管處飆射而出。
太監總管的話還沒有說完,人就捂著喉嚨,血染一身倒在地上,死不瞑目。qδ.net
而呆然看著他死相的那一刻,鄭曲尺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完了。
這事,麻煩大了!
劉大人見大太監總管就這樣輕易死在了他在面前,整個人目瞪口呆,抖得跟篩子似的,本來也想說的話,這會兒卻識相的徹底閉嘴了。
他驚恐地看了看殺完人之後卻還在笑的興安,又看向一臉呆滯的鄭曲尺,彷彿已經認定了就是她在背後教唆這群路匪殺人,她已經叛君叛國了。
鄭曲尺頭痛地撫額。
這事……因為死了一個重要人物,變得複雜了,只怕也不能善了了。
她想,如果不將興安這一群罪魁禍首繩之以法,以鄴王的尿性,他「奈何不得冬瓜」,肯定會拿她跟玄甲軍來當「茄子」承擔下這一切的罪責,畢竟這是多麼好的一個整治藉口啊。
她轉過頭,看著興安,平靜地問道:「你當真知道他們是誰嗎?」
「不就是朝廷的人嗎?」興安回答得不以為然道。
看來,他還是知道其一的,可惜還有其二。
「沒錯,是朝廷的人,但他們卻不是你認為的那種尋常朝廷官員。」
「什麼意思?」興安神色微凝。
她指著地上那具屍體:「你殺的那個是鄴王的貼身大太監總管,相當於鄴王的左右手,你一出手就廢了鄴王的一隻手,你猜若鄴王知道了,會有多震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