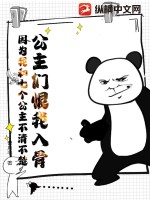燃楚竹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楚鸞抬頭道了聲“謝謝”,卻詫異地發現,幫自己解決困難的竟是謝雲鶴。
心口微微鼓脹了下,她想,這人還怪好的哩。
楚鸞捏著椰瓢的手,無意間,碰到了謝雲鶴冰冷的手指。新舊斑駁的暗紅色痂,佈滿了他的指關節,很明顯,在流放途中他被差撥公人用過拶刑,左小指已經被拶子夾得骨折。
目光沿著傷指而上,只見他的手腕上打著鐵葉鐐銬枷釘,垂下沉重的鎖鏈,腕內側的皮肉已經被磨爛了,區域性紅腫發炎,軟組織被金黃葡萄球菌感染,化膿形成了癰瘡。
鐵葉鐐銬持續摩擦著化膿的癰,該多疼!
可謝雲鶴卻連眉頭都沒皺一下,吭都沒吭一聲。
“你的手……”
楚鸞想幫他看看手上的傷勢。
但謝雲鶴在她捉住自己手腕之前,忽然後撤一步,立在槽口邊。陽光透過條狀的木柵欄,篩進牲口棚,落在男人如猛獸一般的身軀上,似老虎紋。
楚鸞抓了個空,微怔。
也是,除了那一紙婚書,他們倆差不多算是陌生人。
楚鸞不再看他,注意力重新迴轉到了病牛身上。她自牛棚槽口取了一隻細竹筒,一端塞到牛嘴巴喉嚨裡,當做導管用來引流,另一端傾入老醋,灌入了牛喉嚨裡。
耕牛灌了醋,依然趴在地上一動不動。
“嗬,不會治就別亂治,浪費了一瓢醋。”
張順爹又神氣了起來,湊到病牛臉跟前兒,陰陽怪氣道,“瞧瞧,這牛都吊翻白眼仁了。”
楚鸞驟然把牛喉嚨裡那根代替口胃管的細竹筒,給拔了出來。
耕牛喉口肌肉一鬆,瘤胃裡頭的酸臭半液半固內容物,瞬間噴濺向正前方。
楚鸞早有準備,敏捷地閃到左側面。
張順爹年紀大了,反應遲鈍些,牛被酸臭的髒東西兜頭淋了他一臉,未消化完全的鹼性有毒藜草屑,鑽進了眼角,灼得眼瞼非常痛,眼淚都刺激地流了下來,發出殺豬似的咒罵:“挨千刀的!”
神奇的一幕發生了——
原本翻白眼仁兒的耕牛,竟然緩緩站了起來,發出“哞哞”的叫聲。
耕牛通人性,它走到了楚鸞身邊,深褐色夾雜著黃斑紋的牛尾巴親暱地甩了她一下,黑色的牛眼似會說話一般。
“祖宗保佑!”
楚老太看著恢復活力的耕牛,喜極而泣,“咱家耕牛又站起來了,給它套上犁,又能把那十畝地的土翻一翻了。”
坊隅鄉親驚歎咋舌:“鸞丫頭這手藝可真不一般,竟能把瀕死的牛給醫活咯。”
張順爹腦瓜子嗡嗡嗡的,他意識到,今兒自己這張老臉算是傷透了。
此處已無他立錐之地。沒能幫財東家辦成事兒,還壞了兒子的名聲,且被牛吐了一身,他似軟體動物一樣,沿著黃泥土坯牆根,一點兒一點兒地挪到柵欄門邊兒,灰溜溜跑了。
楚鸞俯下腰,把牲口棚槽頭裡堆滿的有毒藜草,用木鍁給鏟了,丟出門去。
毒草扔了,但牛肚子是空的,得給它準備新的好草料。她拿起掛在牲口棚牆壁上的草鐮刀和草籠子。
“讓大錘去。他每日清晨、晌午,都各割一籠。”
楚老太本就偏疼楚鸞些,再加上割草本就是孫子該乾的事兒,所以才會出言阻止。
楚大錘是長孫,與阿鸞同年。因家裡窮,湊不出給教書先生的束脩,也買不起筆墨紙硯,所以縱然到了該讀書明理的年紀,也沒能上村裡唐家祖宗祠堂西側兩間瓦房改建的學堂,更沒機會像學堂裡的孩子們一樣,被童生[1]唐學究賜一個響亮、意頭好的大名兒了。
“我去割一樣的。”
楚鸞挎著草籠就出去了。
小山坡腳,長著許多紫花苜蓿,紫色成簇的花序,這種草富含蛋白質,嫩莖葉中有較多的維生素,很適合耕牛、騾馬當飼料。她彎下腰,手腳麻利地用草鐮割著。涯州是瘴區,大花蚊子和毒蟲毒蟻賊多,溫度偏高,又溼又熱,這才割了一籠,她就已經累得氣喘吁吁,身上都是汗了。右手的虎口處染上了草汁兒,指頭都變了顏色。
一道雪白的影子,迅疾地從雜草叢裡竄過。
楚鸞樂了,她看到了什麼?一條毛茸茸的白狐狸尾巴,漂亮又稀罕。
她想捉住這狐狸,怎知才剛抬腳,大尾巴狐狸就警覺地跑了,竄到了山上林子裡,毛都沒留下一根。
“看來,我不止沒有系統、沒有藥箱空間,甚至也不是什麼錦鯉體質。”
楚鸞無奈一笑,那種狐狸、野兔主動撞到身上來,一出門就能撿到鳥蛋、一下河就能撈到肥魚的美事兒,還是別想了,沒那個運氣。
她大抵,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NPC,是大胤朝的一塊磚。哪裡需要哪裡搬。
想要什麼,得靠自己的雙手努力勞動,方有可能獲得。
割完了草,她提挎著滿當當的籠子,往家裡走。路過河灘的時候,瞧見了茫茫蕩蕩的蘆葦,以及一片生機勃勃的蒲公英花田,一朵朵白色的絨球小傘,在拂拂微風中柔和地擺動著。
野花野草、野狐狸、小河淌水,還有枝頭尾巴一翹一翹唧唧啾啾的山雀兒,這一切都令人感到無比治癒。
楚鸞的腦子裡,又浮現出謝雲鶴手上發炎化的傷口。
沒有抗生素、沒有消炎藥,怎麼辦?
古代鹽比命貴,楚家太窮吃不起鹽,平日裡炒菜都捨不得放幾粒粗鹽,用鹽水消毒太奢侈太不切實際。
而在艱苦的環境下,用蒲公英煎煮出來的水清洗塗抹傷口,雖比不上抗生素,但臨床上同樣具有不俗的消炎效果。本草綱目上就記載了蒲公英搗爛敷在惡膿瘡癰上的治療方法。
楚鸞挎籠提鐮,割了好些蒲公英,捆成一抱。
河灘上生著多種野草,除蒲公英之外,還繡著綠油油的馬齒莧。馬齒莧是農村田間路旁隨處可見的雜草,生命力極其旺盛,村裡常有窮苦人家摘了當野菜吃。一茬兒摘了另一茬兒很快又長了出來,它也是一種散血消腫的藥材。
“好東西,可以做牛飼料;可以當野菜煮藥膳粥;更能和蒲公英聯和用藥,治療癰瘡。”
回到家,拉開門閂,就聽到祖母正在打探著這位罪人孫女婿的情況。
“多大了?”
“二十二。”
“比我們家阿鸞大九歲。你要多照顧、幫扶她,她年紀小。”
謝雲鶴是個行動派,他真去幫扶楚鸞了。
未婚小妻子在井邊洗臉洗手,小臉兒紅撲撲得,似粉蒸肉。他就走過去,把她腳邊的兩籠草料提到了牲口棚裡。棚子西側有個生鏽的鍘刀,刀口鈍的很,很有些年月了。他把紫苜蓿從籠裡抱出來,整齊地碼放好放到鍘刀口裡,壓著鍘刀手柄,咔嚓咔嚓,切出了細碎又均勻的草料。
而後,他把這些鍘碎的上好草料,撒上一些穀物糠皮,潑上適量的水,用一個大鏟子用力攪拌。這耕牛是老楚家最重要的勞動力,又差點中毒死了,謝雲鶴見牆邊還有小半袋豆子磨出來的粗豆麵兒,便抓了兩把放進去。
楚老太看得笑眯了眼,讚道:“這謝三郎莊稼手藝倒是不錯,像是慣做活計的,人也精幹勤快。”
楚鸞挑眉:“謝三郎?”
“他行三。上頭兩個兄弟。”
楚老太把孫女出門割草時打聽到的情況,告訴了她,“一個兄弟死在流放途中,一個兄弟染了瘴氣病,一個小妹……哎,也是可憐。那通天的權貴世家一句話,闔家老小全都淪為臉上刺字的賤籍奴隸,真是世道不靖。”
楚鸞心裡咯噔了一下。
全家都被流放了?看來,謝雲鶴身負的罪名可不小啊!
她的目光轉向牲口棚裡幹活的男人,他把攪拌好的溼潤的飼料,倒入了耕牛面前的木槽裡。耕牛舔著新鮮美味草料,愉快地咀嚼著。
連在糖村生活了一輩子的祖母都稱讚他幹活手藝好,那就說明是真的好。
由此可見,謝雲鶴跟她一樣,應該也是農村出身,自小就地裡幹活的。
“我瞧他氣質不俗,模樣又極周正。我原本還擔心他是名門士族子弟犯了天條流配到這兒,如今看吶,全然不是那麼回事,名門士族公子哥兒大多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等著女人們伺候,哪裡似他這等既會鍘草料餵牛、又知道給灶房的水甕擔水?”
楚老太感慨道,“這人吶,貴在自知。有錢有勢的時候,就該做有錢人該做的事,貧賤落魄時,就該做窮人該做的事。”
楚鸞也跟著笑了:“祖母說的有道理。”
楚唐氏雖然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村婦女,未曾讀過書習過字,卻能自個兒悟出這等道理來。《中庸》有云“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
她把那一大抱蒲公英,打井水清洗乾淨。
推開廚房柴門,迎面就見得一個破土灶,灶上蓋著一個草蓋,蒸騰出滾滾的白熱氣。揭開草蓋,裡頭是正在煮的糙米粥,泛黃的陳糙米,與麩皮一起煮。
所謂陳年糙米,就是擱了數年泛著黴味兒的劣質粟米,裡頭混雜著砂礫、鼠屎。
處理起來很麻煩,也不好吃。一旦發黴就有黃麴黴素,肝毒性強。
楚鸞心頭湧起一股淡淡的憂傷,21世紀一日三頓隨便吃的白米、細白麵,到了古代,只會出現在財東地主、富戶鄉紳們的餐桌上。
“糙米粥做晚食,沒有乾的,難怪楚家人都瘦得跟麻秸稈兒似的。”
她把粥端到春臺上,添了些柴火,舀了乾淨的山泉水入鍋,把蒲公英碼放鍋裡,另取了個草蓋蓋上。
開始熬煮消炎的蒲公英水。
總不能讓謝雲鶴用一雙傷痕累累、發炎化膿的手,天天來家裡幫忙做農活兒吧。這是招了個女婿,又不是招了個奴隸豬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