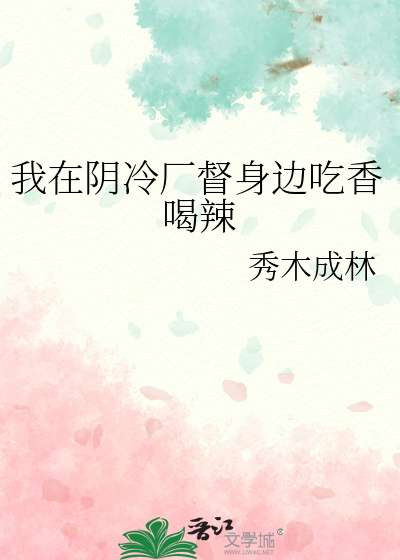心尖意 第17節
天如玉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舜音起身,仔細檢視一番,抬頭說:“再取一匹綢緞送上。”
勝雨又出門去取綢緞。
舜音趁機將摺好的小紙塞入包裹禮品的牛皮厚紙中。
不多時,勝雨匆匆返回,加入了一匹綢緞。舜音看完點頭,吩咐說:“送去後請陸刺史細看禮品是否都喜歡,若其中有不合心意的,下次便不要送了。”
勝雨記住了,抱著禮品出了門。
舜音看著她出去,反身回房,默默坐回桌後。
幾乎是數著時間在等。
所幸勝雨辦事麻利,約莫三盞茶的功夫,她便返回了,快步趕來東屋覆命。
“夫人,陸刺史看完了禮品,皆很滿意,特地手書一封謝帖,讓轉交夫人。”勝雨說著,將帶回的謝帖送到她眼前。
舜音接了,對她說:“辦完就好,我早已乏累,要歇片刻,無事不必打擾。”
勝雨躬身退了出去,還替她將房門關好了。
舜音立即去看謝帖,帖子封口嚴密,陸迢竟然分外細心。
今日借送禮之名,那張夾帶的小紙上,其實特地寫了委託陸迢的一件事情——
她稱上次寄信只顧著與弟弟敘論親情,連與穆長洲的婚事都未能細說,以至於穆長洲後來收到封無疾回信後多少有些不快。因此今日特地請他幫忙,若是後面封無疾再有來信,能幫她攔下就好了,否則只怕穆長洲查信時看見她弟弟再提此事,又要不快。
陸迢的權力有限,舜音自然明白,但她在涼州孤立無援,四周全是穆長洲的銅牆鐵壁,也就只有他可以施以援手了。
因此,那張小紙上,她又加了一句:若實在難為,只需將信退回,反正以後多的是機會通訊,只這段時日不要讓舍弟來信妨礙我與軍司夫妻感情就好。
回想到此處,舜音眼神不免動了動,倒像是真與穆長洲情深意濃了,一邊想,手上已拆開了陸迢的謝帖。
謝帖上,陸迢回覆地也很周到。他稱雖然寄信他做不得主,但收信的第一道確實是他經手。只不過若是攔了後要交到她手裡就難了,通常他經手後還是要送交軍司查驗的。
好就好在,舜音只是要求退回,並不難辦。
舜音在那張小紙最後只道慚愧,因為如此夫妻私事而勞煩他,請他恕罪,看完燒了就好,否則實在無顏見人。
陸迢在謝帖上最後的話便也多少帶了些揶揄:夫人放心,既是私事,豈能不懂,小紙已燒了。
舜音看完,起身將謝帖拿去香爐前,引了火燒去,埋入香灰。
她短日內是不會再寫信去秦州了,但時日一久,封無疾定會主動寫信過來關心,穆長洲就容易看到。雖說不一定看出什麼,但他那樣的利眼,不能掉以輕心。
陸迢現在能幫忙是好事,但她還是希望封無疾最好能心有感知,最近都不要寫信過來了。
忙完這件事,舜音將前後又細想了一遍,坐去榻上,閉上眼,在想穆長洲何時會回來。
昨夜沒能睡好,確實乏累,但即便閉目養神她也無法放鬆心神。
感覺裡只淺眠了片刻,舜音隱約聽見一聲佔風鐸的輕響,繼而身前似是罩下了一方陰影。她睜開眼,眼裡霍然出現一截袍衫衣襬,一抬頭,面前站著穆長洲。
他袍衫緊束,長身而立,似是剛回。
舜音險些以為又是夢中場景,隨即回神坐正:“穆二哥怎麼來了?”說著看一眼房門,門已開了。
穆長洲一進來就看見她一手支額斜倚在榻,在閉目養神,走到她面前,看著她臉到此刻,也沒看到多餘表情,始終沉靜如常。他開口說:“剛回府中,來看望音娘,音娘今日連房門都未出,是在迴避我?”
舜音若否認就太欲蓋彌彰了,別過臉,淡淡說:“是。”頓一下又說,“腰疼。”是提醒他昨日好事。
穆長洲目光落去她腰上,她別過臉時身也微斜,愈發顯出收束的腰肢輕軟纖柔。他看了兩眼,衣襬一掀,徑自在她身側坐了下來。
舜音餘光剛瞥見他坐下,腰後一沉,不禁一愣,才反應過來是貼上了男人的手,轉頭看去,穆長洲的手就在她腰後,眼睛看著她,忽而一按。
她立時蹙眉,輕“嘶”一聲,一手扶住榻邊。
穆長洲手收了回去,自衣襟間摸出一隻圓扁小盒:“果真是傷了,我那張弓是硬弓,確實力重,今日就是來給音娘送藥的。”
“……”舜音抬眼,他已將小盒放來她身側,恰好接近,瞥見他那隻手,她轉開眼。
穆長洲頭稍低,看著她臉笑一下:“軍中的藥見效快,料想明日音娘就不用迴避我了。”
舜音頓時轉頭看去,他站起身,目光又在她腰上看了一眼,自眼前走出去了。
第十七章
明明是挺正常的一句,聽來卻像是最後通牒。
彷彿在說,明日她就再不能迴避他半分了。
舜音又是一夜難眠。
來時決心替封無疾觀望河西防務,並未料到會有如此艱難,最多是自己女子身份不便,那也有記述見聞這個由頭遮著。誰曾料到涼州是如此境況,穆長洲又如此防不勝防……
天尚未亮她就已經醒了,幾乎是看著房中光線一絲一絲從暗到明,才從床上起身,赤著腳踩在地上,來回走了幾步後,回身平靜地穿衣,一隻手摸了摸後腰。
其實若非他那一按,後腰也沒那麼疼,但那盒藥她還是抹了,可恨的是,竟然還真是有效得很,現在腰後溫熱舒適,真就全然好了。
她輕輕咬牙,繫上腰帶,又握了握手心,低低自語一句:“豈可臨危自亂,軍中大忌。”說完已平心靜氣,走去門口,拉開了房門。
外面天清氣朗。
涼州的春日短,且來得遲,至今才算到了春光最好的時候,尚在早晨,日光已經晃眼,直照入主屋。
穆長洲看著輿圖。
目光剛剛從鄯州移至甘州,昌風走到了主屋門邊,低低向他報了一句:“軍司,夫人出房了。”
穆長洲站直,手上輿圖一合,走去門口,東屋房門開著,舜音果然從房中走了出來。
她身上穿著檀色襦裙,收束高腰,似是剛剛由勝雨伺候著梳洗用飯完,站在廊下,目光不偏不倚朝主屋看來。
穆長洲與她視線碰上,走出門,到了她跟前,上下看她兩眼:“看來我的藥還是起效了。”
舜音眼神動一下:“穆二哥的藥自然是有效的。”
穆長洲想起了昨日去她房中的情形,又看一眼她腰上,轉頭吩咐昌風:“去備馬,今日得閒,我陪夫人去城中走走。”
昌風領命,快步去辦。
舜音立即看了過來,目光一眨不眨地盯著他。
穆長洲看見她眼神,一笑:“這次不是幌子。”說完先往外走了。
舜音看他走出去好幾步,才緩步跟上,心中定了定,早已看出他如今行事琢磨不透,今早起身時就已想好,最好就是以不變應萬變。
昌風牽了他們各自的馬至府門前,弓衛只點了十人,算是輕裝簡從。
勝雨已快步送來了帷帽,舜音戴上,走出府門,一言不發地踩鐙上了馬背,看一眼身旁,今日決心只做個言聽計從的乖順人。
穆長洲在她身旁上了馬,未帶兵戈,袍衫寬著,只袖口與腰身仍緊束,否則都看不出是武人打扮,看她一眼,當先領路而出。
確實是只在城中走走。
他們沿著道路上了大街,一路熱鬧目不暇接,穿著胡衣的百姓、牽著駱駝的商旅,紛紛避官馬而行,只四周不同話語的叫賣聲不斷。
除去上次的浴佛節,舜音其實已經很多年沒有見過這麼繁華的場景,眼神往道路兩旁掃了掃,看向右前方的穆長洲。
穆長洲已回頭,忽朝她身後看一眼:“那裡一番奇景,長安絕不會有,音娘記述見聞,怎麼沒有興致?”
舜音往後看,路邊一個三層石壘的小塔,幾個胡商模樣的人圍繞一圈正在頂禮膜拜,口中唸唸有詞,如在禱告,大約是什麼西域外教的信徒,長安確實沒見過。
她擰擰眉,果真難防,轉回頭時說:“方才已看到了,只是看穆二哥已經過去,便沒有叫停觀望,反正回來時再詳看也一樣。”
穆長洲也沒停,轉頭回去繼續往前:“那是我的錯,若是再有想看的,你叫停我就好。”
舜音轉著眼去留意四下,心想還說不是幌子,哪裡是真陪她觀望風物的,竟已狡猾成這樣了。
好在一路並無什麼奇怪物事了,在大街一頭拐了過去,到了一條僻靜道路上,頓時安靜不少。
前方卻有馬蹄聲傳了過來,馬上的是胡孛兒,領著幾個人,一路如同巡視,到了跟前勒住馬,向穆長洲見軍禮,又看看舜音,像是沒想到會在此處撞見:“軍司今日本該休沐,怎又出府了?”
穆長洲說:“陪夫人出來觀望風物。”
胡孛兒恍然大悟,又瞅一眼舜音,怎麼那日帶著去走馬障小道,今日就陪著逛城了,實在想不明白,咧嘴笑道:“夫人他日若真能撰文成書,那也算是咱們涼州文采第二了!”
他嗓門時常很大,連舜音都嫌吵,故意問:“誰第一?”
胡孛兒登時回:“那還能有誰,自然是……”說著看向穆長洲,忽而噤聲不說了。
舜音不禁看向穆長洲,想了起來,當時去總管府時,也聽總管夫人劉氏說過他不愛提年少往事了,大約是真不想提了吧。
反正他也與過往大不相同了,確實沒什麼可提的。
穆長洲問:“你來此有事?”
胡孛兒正愁沒話頭,忙道:“今日輪到我領人巡防城務,軍司可要親自去查?”
穆長洲點頭:“那便去吧。”
舜音聽見,頓時鬆一口氣,扯了韁繩準備返回:“那我便回去了,今日也不是外出公幹,我就不跟隨了。”
胡孛兒馬上揮手讓弓衛送夫人回去,卻聽穆長洲道:“不用,你跟著我。”
舜音一頓,看過去。
胡孛兒也意外地看他一眼。
穆長洲回頭,打馬至舜音右側,伸手拽了一下她手中韁繩,將她原要調轉方向的馬給扯了回來,低頭看她一眼,聲音就近在她右耳邊:“音娘不是腰不疼了?”
“……”舜音頓時想起上次被他強行扯著韁繩帶回去的情形,伸手將韁繩扯了回來。
穆長洲鬆了手,打馬往前,她也只能乖乖跟上。
唯有胡孛兒眼神在他們身上來回轉悠了好幾圈,總覺得今日他們夫妻二人之間似有些不對勁,怎麼如同較勁一般?可要細說又說不上來。
沿著眼前道路往前,是往北城門的方向。
舜音來涼州至今還是第一次去北城門,只因城北臨山倚靠,地勢最尊,又離近總管府,一般此門都是官員通行居多,不是主要往來城門。
兩刻後,抵達北城門下,一行人都停了下來,紛紛下馬。
舜音下了馬也沒抬頭,即便現在北城門就在眼前,還有帷帽垂紗遮擋,也忍著沒有往城上去看一眼,只不遠不近地跟在穆長洲身邊。
城守官已匆匆下來見禮:“不知軍司親自來查,上方兵戈新修,胡亂橫置,雜亂無章,馬上便整理好了。”說完看一眼他身後跟著的舜音,在四城各處值守,常見這位夫人跟著出城公幹,可沒見過這種專查城防軍務的時候還帶著她的。
穆長洲朝身後看一眼,往上走:“無妨。”
舜音也只能跟著走上去。
一上城頭,立時有凜凜大風吹來,天際橫闊,四下盡收眼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