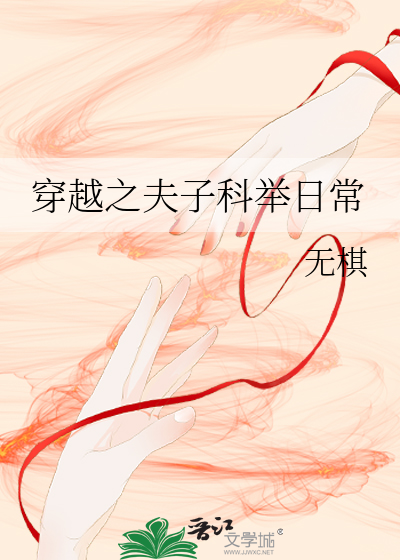道芝道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寧陽城碰上了倒春寒,連颳了幾日颯颯的陰風,一到早晚就倍感料峭。
這日沈涵初醒得很早,窗外面還是一片黑朦朦。睡眼惺忪之際,她才想起今日是禮拜六,不用上課。
她看了看牆上的掛曆,翻了個身,將頭蒙在被子裡,在做夢似的,腦袋有些昏昏沉沉,似乎到了另一個地方,一座幾進幾齣的大院落,厚重的朱漆實心大門推開,走進一個人來,高高大大,石青色的褂子,身後跟著僕役,威風凜然,是她的父親沈乾鶴。他剛踏入正廳前的院子,她的兩個弟弟就歡呼雀躍地跑到院子裡,抱住他父親的腿。
他父親抱起弟弟們,滿臉慈祥的笑容,親暱地去用鬍子磨蹭他們的臉,她的弟弟們笑得咯咯直響。
正廳菱花隔扇門後躲著一個人,還沒門的裙板高,穿著件半舊袍子,臉磕在隔扇板上,磕出一條條紅印子。她細細一看,發現是她自己,小時候的自己。
她瞪大一雙眼,靜靜地看著院子裡的弟弟們,眼裡是滿滿的羨慕。因為父親,從沒有這樣抱過她。
乳孃何媽走了過來,牽著她往內廳走。她戀戀不捨地往院子裡又看了最後一眼,何媽往一扇垂花門一拐,她也一拐,便什麼也看不見了。
何媽帶著她回到一座跨院的廂房裡,跨院子種著幾棵槐樹,鬱鬱蔥蔥的葉,六月裡常是落得滿地鵝黃色的小花。東南角有一間小佛堂,裡面有個女人常年在裡面唸經,何媽告訴她,那是她母親。
白天,她和兩個弟弟一起在家庭蒙館上學。當時清王朝已沒了,共和民國伊始,各地都推行新學,京師大學堂審定的十六門學科裡,有一門圖畫課。課本里雖是西洋的幾何圖,但先生教的還是國畫。
她一直用不好毛筆,那幾天卻一直在極認真地作一副圖,畫的是她父親,高高的個兒,寬厚的肩膀,溫和地抱著她,慈祥美滿。
先生不在,她的兩個弟弟吵得厲害,相互扔書擲筆打鬧著。一支沾滿墨汁的毛筆滴溜溜地飛了過來,剛好擲到了她畫上,她父親那張慈祥的臉,被一灘墨汙給毀了。
那是她辛苦作了幾天的畫,裡面滿滿地都是期盼和希望。她只覺得氣急攻心,“砰”地一拍桌子,執起那隻筆朝他們丟了回去。
兩個弟弟愣在了那裡,他們雖是姨太太生的,但百般受寵。她雖是正室所出,但在這家裡,爹不疼娘不愛,一直沒什麼地位。他們向來看不起她,如今她竟敢對著他們拍桌子瞪眼,簡直是反了天了。
兩個人剛剛還互相對打,如今卻同仇敵愾,一起來對付她。三個人扭打了起來。她是雖是長姐,但比他們任何一個都瘦小。以一對二,自然吃虧不少。但她也是個倔性子,吃虧歸吃虧,打還是要打的。
蒙館先生回來後,見三個學生,居然撕扯著在打架。蒙館裡遍地狼藉,亂作一團,老先生氣得鬍子都要豎起來了。將他們一個個拎到蒙館外罰站。
她父親從外面回來後,老先生絮絮叨叨向他說著他們今天的惡劣行跡。他聽了後板著臉,問是怎麼回事。兩個弟弟低頭不語,她便跑進蒙館,拿出那張被毀了的畫,顫顫巍巍地遞到他面前,小聲道:“他們弄髒了我的畫。”
她此時還是有期盼的,期盼他會問一句畫的是誰。她低著頭,臉上卻是在笑,只要父親一問,她就會指著畫上的人回道:“這是父親,父親懷裡的是初兒。”
她天真地想,只要父親今天能抱她,那她便對兩個惡劣的弟弟既往不咎。
她父親瞥了一眼,什麼都沒問,只將那畫奪了過去,撕得粉碎。她震驚了,那紛紛灑灑的碎紙片,像她幼小的心。她聽到她父親對一旁的僕役說:“將二太太找來。”
二姨太穿著明油綠的鳳蓮錦旗袍款款而來。她左手戴著的金手鐲裡,總掖著塊燻過香料的綢帕,走路時手帕隨著身子一擺一擺,那香味也一陣一陣的。
她父親將她推到二姨太面前,說:“你好好教教她,該怎麼管教就怎麼管教,等懂規矩了再讓她上蒙館。”
二姨太淺淺笑著,十根塗了鮮紅的蔻丹鮮紅蔻丹的手指絞著綢帕,應了聲是。
何媽給她梳的圓髻在剛剛扭打時被扯散了,衣服也撕破了幾塊。她披頭散髮地站在那裡,看著二姨太的笑意,看著她血一樣紅的指甲,空洞的心裡,又有了些許寒意。一直以來,她都有些怕這個女人。
後來的日子,便是噩夢的開始。二姨太每天將她反鎖在一間屋子裡,讓她背《女誡》。那屋子空落落的,只有一套桌椅。粉牆剝落,露出裡面的黃泥來;黯舊的門窗上,都是被粉蠹蟲蛀出的小洞,一股木頭的黴味。
她怕一個人呆在荒涼的小屋裡,好想逃出去,可她更怕那小屋門開啟——屋子的門每天都開啟兩次,中午和黃昏,是二姨太帶著老媽子趾高氣昂地來“巡學”。老媽子手裡拿著根竹條子。
二姨太每次“巡學”只說一個字——背。她便開始戰戰兢兢地背,背錯了,或是背不完整,她便從老媽子手裡拿過竹條子抽打她。
那竹條子又細又長,抽起人來火辣辣地疼。她痛得慘叫連連,滿屋子地逃,可那空落落的屋子,她又能躲到哪裡去。竹條子的“嚯嚯”聲下,她聽了了自己皮肉裂開的聲音,二姨太的十根手指,血一樣的紅,那是她的血,她看著二姨太惡毒的笑,心想自己一定會死在她手裡……
沈涵初驀然睜開眼,大口地喘著氣,彷彿做了一個冗長而痛苦的夢。
她看了看那窗子,窗外依舊是灰濛濛的,玻璃上印著她的影子,她的臉,臉上有一滴滴的水珠子往下落。她一吃驚,摸了摸自己的臉頰,卻是乾的。
她掀了毯子,趿著拖鞋走到窗邊,耳邊傳來淅淅瀝瀝的雨聲,水珠子打在窗子上,順著玻璃往下滑。窗外是流動的烏雲,怪不得,天一直亮不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