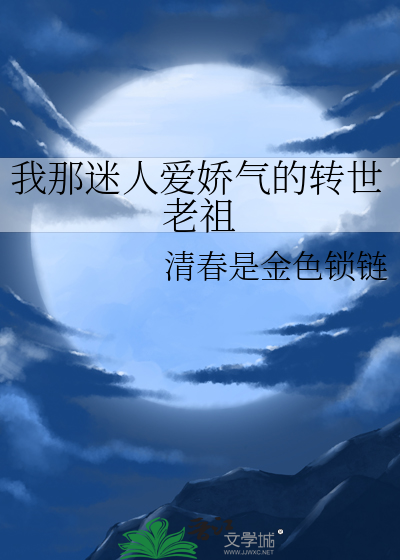子瓊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雲挽做了一個很長的夢,夢到了許多以前的事。
從她十四歲之前,與母親生活在凡間,再到後來入了太虛劍川的種種。
往事如在昨日,卻又好似久遠到是上輩子的事。
雲挽四歲那年,父親離開了她和母親,之後便再沒了訊息。
母親不得已,只能帶著她寄住到了舅舅家中,但舅舅一家人卻並不喜歡雲挽,他們認為若非是因為雲挽和那個拋棄了她們的爹,雲挽的母親原本是可以嫁個好人家的。
因著這份不喜歡,雲挽童年的生活其實過得很不好,舅舅一家雖不至於苛待她,但那時不時的冷言冷語,和不經意間的漠視卻也足夠刺痛一個孩子的心。
雲挽對父親沒有任何印象,她只知道父親給母親留了一塊翡翠玉佩,那玉佩巴掌大小,呈劍形,溫潤碧綠,不似凡品。
母親日日將玉佩戴在身上,她告訴雲挽,她的父親是一名很厲害的劍客,他終有一天會來接她們。
雲挽對母親嘴裡的“很厲害”沒有概念,她只是時不時地想,若是父親當真那般厲害,她與母親又為何會面對那麼多的冷遇?
那些零星的念頭在灰敗的日子裡一寸寸發酵,逐漸變成了一種苦悶又無奈的怨恨,所以雲挽總會下意識將那個屬於父親的姓氏從自己的認知中抹除,她討厭別人叫她“祝雲挽”。
十四歲那年,雲挽與兩位表姐發生口角,被她們推入了魚池,母親因過於焦急親自跳入水裡將她救起。
寒冬臘月,被水浸透的兩人都發起了高燒,雲挽病得很重,一連睡了七天,等她醒來時,母親已經變成了一具冰冷的屍體。
大夫說,母親多年思慮過重,本就體弱,如今在深冬落水,染了風寒,沒能熬過去。
母親去世得突然,沒有留下遺言,唯有那枚翡翠玉佩被她緊攥在手中,那也成了她留給雲挽的唯一一件遺物。
那日雲挽跪在母親棺前,捏著那枚玉佩哭得昏厥,而第二天,太虛劍川的人便找上了門。
雲挽這才知道,原來她的父親並非是劍客,而是劍仙,她也才知道,原來父親始終不來尋她與母親,是因為他早在十年前便已經身亡了。
那一刻的雲挽竟突然覺得很輕鬆,她慶幸地想,還好父親只是死了,並非是真的拋棄了她與母親。
來接她之人自稱是太虛劍川大長老崔見山的首徒虞驚意,雲挽只是一介孤女,自沒有反抗的能力,或者說她本也沒有反抗的理由。
於是第三日,她便隨虞驚意和一同前來的太虛劍川弟子離開了俗世,前往了崑崙墟。
雲挽是凡人,使不了御空訣,所以他們走得很慢,這一路上,虞驚意向她講述了許多關於崑崙墟、關於太虛劍川,還有關於她父親祝言昂的事。
太虛劍川的弟子對雲挽始終禮遇有加,並未看她年紀小便輕慢於她,但云挽自幼寄人籬下,不是傻子,她很快就明白了他們的意圖,或者說是那位大長老崔見山的意圖。
他們想要她手中的掌門令。
雲挽不想給,但她不想給的理由卻不是因為覬覦太虛劍川的掌門之位,她人生的十四年皆被困於一隅院牆之下,對“掌門”一詞根本沒任何概念。
只是她手中的這枚掌門令是母親留給她的遺物,也是唯一的遺物。
母親走時,未能留下一句話給她,若是連這件遺物也沒了,那關於母親的一切便徹底消失了。
雲挽曾恨過她的父親,也不可避免地怨過她的母親,她怨他們生育她,卻又讓她活得那般痛苦。
她恨父親一走便是十年,自此了無音訊;也怨母親優柔寡斷,對那樣一個拋家棄子的父親念念不忘、茶飯不思、憂慮成疾。
可那個在記憶中素未蒙面的父親,卻並非忘記了她們,而是早早地身隕,而她的母親,也在最後因救她而身亡,於是那份怨就變成了一種纏綿複雜的疼痛和委屈。
想去怨恨又不忍怨恨,想要懷念卻又不知該從何念起,其中的苦楚澀然不知該向誰訴說,更不知要如何訴說,她便只能將那些情緒寄託在那枚翠色的玉佩之上,隱隱作痛,卻也難以割捨。
從出發到抵達蜀洲,一共用了七日,雲挽一路舟車勞頓、惶惶不安,行至望仙道時,已是傍晚。
夕陽西下,天色漸暗,虞驚意卻告知她,每位新入門的弟子皆需用一雙腳親自爬上望仙道的石階,才能求得仙緣,這是太虛宮長久以來的規矩。
他並未多做解釋,雲挽卻反應了過來,太虛劍川這是想給她一個下馬威。
虞驚意大概也覺得為難她一個小姑娘有些過意不去,所以當雲挽向他看去時,他竟不自覺地移開了目光,雲挽便徹底醒悟,這應當是那位大長老崔見山的意思。
她也意識到,她來到這座傳聞中的太虛宮,來到了這個父親曾掌管著的宗門,並非是“回家”,而是換了一個地方“寄人籬下”。
晚霞沉入山川之間,映下一片暗色的橘光,長長的石階半隱在層層疊疊的翠色之中,一眼望不到盡頭。
雲挽知道,待到夕陽落下後,她便要在漆黑寂靜的夜裡,獨自一人順著長長的石階,一步步走上這座冰冷而陌生的龐然大物之中。
她不可避免地緊張害怕、猶豫躊躇,她站在山間石階前環顧四周,可那些太虛劍川的弟子卻無一人將視線分給她。
石階旁的守山弟子面色肅穆,似早已被歲月打磨得對一切都見怪不怪。
虞驚意最終輕輕拍了拍她的肩,低聲寬慰道:“快些走吧,登仙路漫漫,但走至黎明初升時,便能真正看到太虛宮的山門了。”
雲挽緊攥著衣袖,止不住地輕輕發抖,她深深看了虞驚意一眼,清晰地明白,在這個地方,沒有人在乎她,也不會人會憐憫她。
石階很長,在逐漸沉寂的光影中,被夜色襯成一片幽深。
沒過太久,天就徹底黑了下來,周圍並不是絕對的寂靜,枝頭被風吹得輕顫,細微的蟲鳴聲不知從何處傳來。
天地間彷彿只剩雲挽一人,這些都是她過去的十四年中從未經歷過的,未知又迷茫,陷在深深的困頓中,彷彿永遠看不清前路。
不知走了多久,雲挽終是踉蹌著跌在臺階上,被青苔蹭了一膝蓋的泥,狼狽地哽咽出聲。
直至一段雪色的衣襬闖入她的視線,她才倉皇地拭去臉上的淚,茫然地抬頭望去。
夜深露重,月輝卻澄澈而明亮,雲挽便望進了一雙如山間輕雪般的眉眼中。
青年立於夜色間,輕垂而下的雪色衣襬似清泠無垢的曇花,他安靜地垂眸看來,令人不自覺聯想到清泉水中映出的一彎月。
雲挽仰著頭,就見一道繁複的劍印在他眉心綻放,其上盈著淡淡的銀色琉光,若隱若現,似落於額間的一片霜花。
她認得出來,眼前之人身上所著的白衣,是太虛劍川統一的門服,那些來接她的弟子和虞驚意也穿了同樣的衣衫。
但不知為何,雲挽卻覺得眼前的青年與那些人是不同的。
若說虞驚意給她的印象是一位幹練的劍客,那麼這白衣青年,則更符合她對仙人的想象。
她不知道他是誰,更不知道他是否也和虞驚意一般,是受了那位大長老的指示,前來為難她的。
雲挽很害怕,她掙扎著從地上爬起來,滿眼戒備地看著他,他卻在此時開口了。
“登仙路三萬階,你已過八千。”
那聲音如想象中一般清冷疏淡,卻也格外悅耳。
雲挽不清楚他的目的,卻也在他的提醒下,少了些迷茫。
她抿緊唇,艱難地繼續邁腿向上走去。
走出一段後,她回頭看去,就見那青年依舊站在不遠不近的位置,一雙冷月般的眼眸靜靜地望著她。
她咬牙又走出一段,再次回頭,那青年仍在。
他一步步地跟著她,沒有過多的解釋,也並未再主動與她搭話。
雲挽有些不安,也有些疑惑,但在這樣陌生孤寂的黑夜中,有另一個人在,她竟不再感到害怕。
十四歲的雲挽尚只是柔弱的凡人小姑娘,她走得很慢,身後的青年也極富耐心地慢慢跟著。
從幽冷的深夜,走至了黎明初升。
當東方的天際露出金光,為巨大的仙宮鍍上了一層亮邊時,雲挽終於氣喘吁吁地站在了太虛宮的山門前。
她在最頂層的石階回頭看去,就見那青年也正抬眸向她望來,那雙漆黑寂冷的眼眸彷彿被天際的光照成了金色,而其內映著的,是雲挽沾著汗珠、略有些蒼白的臉。
她正想說些什麼時,虞驚意的聲音便從不遠處響起。
“祝姑娘,三峰長老此時正在玉清殿等著見你。”
雲挽一驚,偏頭看向虞驚意,在他不解的目光下,她再次向身後望去,可那跟了她一路的青年卻已經消失了,消失得不留一絲痕跡,彷彿她之前所見皆是幻象,又彷彿只是一個荒唐而怪誕的夢。
雲挽怔在原地,突然就產生了一個念頭。
那沉默地跟了她一路的人,似乎並非懷揣著惡意,反而親自陪著她,走過了這段最難熬的夜路。
她不清楚自己是否會錯了意,但心底還是突兀地湧出了一種陌生的情愫,彷彿那顆倉惶漂泊的心,終於找到了歸處,穩穩地落回了胸腔中。
她突然就迫切地想知道,他到底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