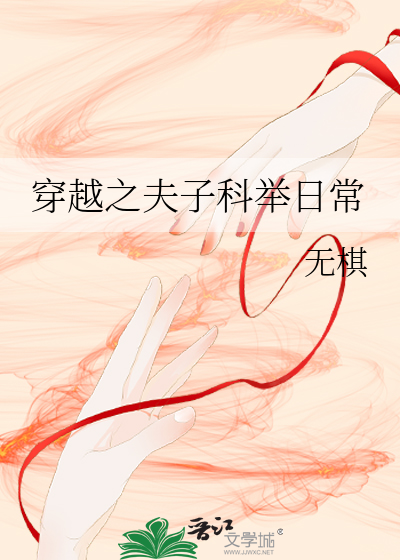道芝道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日子一晃又到了週一,寧州師範的教學樓,沈涵初和夏中昱都在廊子上休息,兩個人碰到一處,就閒聊了起來。
夏中昱突然說道:“昨天劭南來我家時,跟我提到了你。”
“哦?”沈涵初有些驚訝。
中昱道:“他說你這個人怎麼這麼客氣。”
沈涵初笑了一笑,心下明白楚劭南這樣說,是因為那晚她堅持不讓他送。其實也並非是因為她客氣,只是她是個極度缺乏安全感的人,坐在上面,總覺得四空八落的,對面開過一輛汽車來她心裡一驚,跑過一輛黃包車來心裡又是一驚,連走過一個人來她都要一驚,好像這腳踏車會隨時撞上去一般。雖然理智上她清楚是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可理智歸理智,她心裡可受不了這一路不斷的心驚肉跳。
中昱又道:“他還問我,你的性子是不是一向來這麼冷冷淡淡。我們幾個在一處時,為什麼你總不說話?有點沉悶……”
沈涵初聽了後一怔,隨即依舊笑笑,可笑得有幾分勉強。因為這雖然不是什麼不中聽的話,但也不是好話。她一向來是不太在乎別人對自己的評價的。可不知為何,這話從楚劭南口裡說出來,她心裡竟有幾分失落。
中昱直起身舒舒服服地伸了個懶腰,又道:“他又說——不過你活潑起來倒是很有靈氣的……”說完他把脖子伸得長長地探過去,一張大方臉湊到她眼前,笑著說:“嘿嘿……靈氣嗎,讓我仔細瞧瞧,我怎麼從沒瞧見過?”
夏中昱向來這麼口沒遮攔的,沈涵初本不想理他。可是他就這麼一直意味深長地盯著自己看,好像那晚她和楚劭南之間,發生了不可告人的秘密似的。沈涵初明明心裡坦蕩蕩,卻被他一雙炯炯的眼睛看得心虛起來,好像真的發生過什麼一般,臉熱辣辣的開始發燙。
幸而這時鈴聲響了,她趕緊說:“我上課去了。”便往教室裡跑,這才混了過去。
從這日後,沈涵初卻對楚劭南卻格外地注意起來。她和夏中昱在寧州師範上課,偶爾聊天時,總會說起一些關於楚劭南的事情。一提起他們的往事,夏中昱總是滔滔不絕:“劭南啊,在這寧州也算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可他為人呢,一點架子都沒有,又善於助人,沒有人不喜歡和他做朋友的。”
沈涵初便道:“楚先生倒的確挺友善的。”
“雖然友善,可厲害起來也是相當凌厲。想當年我和他還在讀書時,他就是學生中的領袖了。有一年寧州鬧災荒,周邊的災民都湧進了寧陽城裡,發生好幾次搶米風潮,譚都督便下令驅趕難民,就是劭南去督軍府上據理力爭,才讓譚都督改了主意。後來,他又組織大家四處募捐,偏偏就是他有辦法,讓那些一毛不拔的商賈鄉紳乖乖地拿錢出來募捐,接濟災民。”
沈涵初聽了,心中暗暗敬佩,又問道:“那後來呢?”
“後來……後來等他剛畢了業,譚都督就親自帶了聘書上楚宅拜訪,要聘他到督軍府的秘書處做官。只因楚伯父不願他從政,他後來才改去了寧華大學任教。劭南他博學多才,年紀輕輕就做了教授,他可是寧華大學史上最年輕的教授哩……”
“他還是《新民報》的主筆,他的報紙呀,什麼文章都敢寫,政見又常常有悖於當局,有時候可把譚都督呀,氣得可夠嗆的。譚都督雖然時常惱他,可到底是個惜才之人,真有什麼事情也還總會幫襯著他。”
夏中昱滔滔不絕地說,她便支著下巴靜靜地聽,關於楚劭南的每一句話,倒像是一粒粒種子,埋進了她的心裡。
寧陽城裡幾家知名的書局報社,都是楚家的產業。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那《新民報》。《新民報》言論犀利,不為當局所控,楚劭南親任著報刊的總編輯,一杆筆所向披靡。因而這《新民報》在舉國的林林總總的報社中,頗有威望。
自沈涵初與他們相熟後,也常被邀去那報社活動,或是一起讀書聊天,暢談古今;或者研讀稿件、評擊時弊。與這樣一群磊落的人一起,生活倒是很有樂趣。
那報社的堂屋一角有架舊風琴,沈涵初以前在法國時,參加過唱詩班,學過幾首曲子。有日午後,大家起鬨要她上去彈奏一曲,她推脫不了,只好去了。
那風琴放置在窗邊,窗外是一片碧綠的湘妃竹,紫斑點點,灑在青亮的竹節上,春日的午後,暖風吹拂,竹葉像醉了般沙沙搖曳,金色的陽光透過竹葉縫,也是斑斑點點灑了她一身,她穿著件藕白色的鏤花縐紗洋裙,烏黑的頭髮,腦後束著根朱霞色的髮帶,那髮帶上的水鑽在翠竹金光中閃著熠熠如幻,唱詩班的曲子,又有一種肅穆聖潔之感,報社的人都聽得如痴如醉。
她朝他們望過去,卻見楚劭南右手悄悄伸出大拇指,笑著對她比了比。她看著,臉含笑意,心中便湧上一陣微醺的喜悅。
到了下午,楚劭南寫完一篇社評,覺得有些口乾,去拿水壺倒水喝。經過堂屋時,看到沈涵初在書桌前寫東西,也替她倒了一杯水,走了過去擱在她面前。
沈涵初一抬頭,見是他,笑著道了句謝。他便問道:“沈小姐在忙什麼呢?”
她拂了佛手邊的幾張信紙,道:“也沒什麼,給幾個讀者回信。”原來這段日子她常在這報社,也被邀寫了些文章在這《新民報》上發表了,一來二往地,竟也積累了些讀者。
“哦?這麼快就有讀者給你寫信了?”
她拿過那面前的茶杯,呷了一口潤了潤唇,有些不好意思起來。
楚劭南便道:“你那幾篇寫法國大革命的文章我看過,寫的是真的不錯。”
她便越發不好意思起來,道:“我這小打小鬧寫的東西,在楚先生面前是班門弄斧了。”
她說這話時一偏頭,耳垂上的一對長玉環子便沙沙地打著衣領,很是靈動,楚劭南看得倒要出神起來了,慌忙移過目光,見那桌上攤著一本厚厚的書,便拿過來一看,裡面竟夾著一疊紙,上面娟秀的字型,倒是她的筆跡,便道:“沈小姐又要有新作了?那我可要先一睹為快。”
沈涵初忙搖搖頭道:“不是,那不過是我譯著玩的法國小說。”
“哦?”楚劭南饒有興趣地讀了起來,不由得感嘆:“譯得真好!我看這《新民報》上,倒是可以給你開個法國文學的專欄。”
沈涵初只當他說的是客氣話,道:“讓楚先生見笑了,要真說譯得好的,裴先生早就譯過此書,那才是行雲流水,擔得起一個好字。”
裴先生便是那裴遠笙,是聞名遐邇的大學者,尤擅譯法國文學,沈涵初一向來崇敬他,也最愛看他的書。
楚劭南將稿紙整整齊齊地擺回原處,道:“裴先生的譯文宏大壯麗,但沈小姐譯文更為細膩真切,所以,你們是各有千秋。”
沈涵初倒是詫異了一下:“楚先生也讀過裴先生的書?”
楚劭南道:“裴先生名師鴻儒,又風骨錚錚,他的書,自然得拜讀一二。”
聽他也崇敬裴遠笙,她心裡有一種莫名的高興,只謙遜道:“裴老先生文采斐然,中學西學融會貫通,我哪敢和他比。”
她說著似有些慚愧,伸手掠了掠髮絲,耳上的長玉環子隨之輕晃。
報館裡四處都是嗒嗒的打字機聲,倒有顯出一種忙碌,午後的陽光卻有幾分慵懶的,折射在她的長玉環子上,瑩瑩的光暈與她白如霜雪的皓腕,抬手掠鬢間有種說不出的韻致。
楚劭南又略一發怔,忙斂了心神道:“其實我與裴老先生素有來往,也算有些交情,只不過先生如今在歐洲遊歷,等他回國了,我定為你們引薦引薦。”
沈涵初一聽,十分驚喜,道:“那真是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