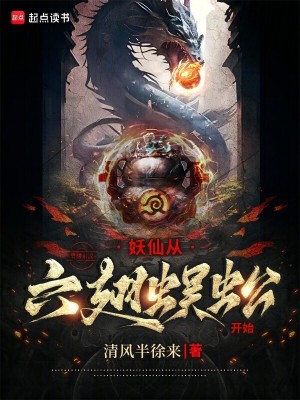空桐悅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由於下地的專業裝置還需要時間準備,明天才會送到,今日隨身帶來的都是眾人的貼身行李。行李被搬運上車,旅行團裡的人見附近正好有早市,便與司機商議後,讓他先行把行李送到客棧,人則打算去逛集市,順便解決早飯的事情。
宋伊是獨行,路過時聽到周圍有人不知在議論什麼。她走近去聽了一耳朵。談論內容是在說這山上的那座染廠的事情,染廠池子裡泡了個人,發現的時候,那人臉上一點血色都沒了。但那人穿著古怪,當地人覺得這人來路有問題,就去找了當地最有權力的杜氏家族族長來定奪。這會兒雖然送到衛生站醫治,卻是被派人盯著,估計一醒就得被盤問一通。
“為什麼不報警?”
宋伊旁聽時問了一句,那幾個本地人登時住嘴,也不繼續談論這件事,反而以一種戒備的眼神看她。在這種戒備中,他們紛紛散開,沒有回答問題。宋伊想再找個人詢問情況,卻被人拍了拍肩膀。
她回頭,頭髮花白的老先生正站在她身後,那是寧城大學歷史系的老教授塗璟。
“塗老師。”宋伊之前在學校與他碰過幾面。兩人不算很熟,但師生之間的禮貌她還是有的。
“你這麼問是得不到回答的。”塗璟示意宋伊觀察周圍,“你應該不難發現,他們都是以小團體的模式活動,再加上這周圍近年來發生的事情很多,你一個生面孔貿然岔進去,他們自然有戒心。”說完,塗璟慢慢悠悠往早市的方向走,瞧著走在前面正拉著年輕小姑娘說個沒完的自己妻子,彷彿也被她們間的好心情感染,神情放鬆。
宋伊有不解,追上去說道:“可如果事關人命,我覺得還是交給當地警方來判斷比較好。現在已經是二十一世紀,封建迷信並不可取。說到底族長只是一種長輩的代稱,並沒有實際權利。有的事交給他們判斷,到時真出問題,怕是會浪費不少時間。”
塗璟腳步放慢,與宋伊並行:“任何事物被流傳下來,總歸是有它的意義在。興許在我們外人看來很難以理解,不過在他們的世界觀裡,有一套很‘完整’的家族制度。我們此行目的不在人文流傳,所以非必要,還是不要與他們起衝突較好。”他們依靠這個制度來做事,可能有偏頗之處,不過早已習慣。
“我確實不理解。”若是精髓,傳承下來固然好,相反如果是糟粕,則不必傳承。宋伊認為,時移世易,他們的制度都是過去式,現在的法典更貼合現代行為模式。
塗璟見她那副正經的模樣,笑了下:“你們家的長輩...應該沒有下過鄉吧。”否則這孩子也不會一點概念都沒有。
宋伊搖頭,卻又說道:“家中確實沒有,不過從我堂系的長輩那邊有聽過一些。說是六七十年代那會兒,大部分的知識分子都會下鄉。那時條件不比現在,熬不過去的大有人在。若運氣好的能繼續回城讀書務工,再不濟混個村官噹噹也算可以了。”
塗璟擺擺手,笑容更深:“你那親戚沒說實話。”當然也可能他是最早一批迴城的,“或許在你們年輕人聽來做村官是好事,卻也只是外人看熱鬧罷了。做了村官,大小瑣事都會找上門,且村官的任期長,一人連任的情況也不是沒有。而最大的折磨除了肉體的疲憊,新舊制度的碰撞所造成的連鎖反應,會比你們想象中得還要慘烈。改革這種非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情,對於某些歸心似箭的人來說,是天大的磨難。”精神上的反覆拉扯是最為致命的。
“您用上了‘慘烈’這個情感色彩十分濃重的詞彙,是否...您這些話也是有感而發?”嚴謹的人用詞都是斟酌來的,宋伊覺得,以塗老師的身份,能夠說出這麼重的詞,當年的事情想必不是三言兩語可說得清的。
“當你見過太多不朽的東西...你就會意識到,原來除去天災...人心才是最大的變數。”
宋伊被他這番話打得七葷八素,對方卻一轉方才那有些沉重的情緒,邀請她去附近的攤位買吃的。
走了幾步後,塗璟又退回來說了一句話。
他問宋伊,她是不是家裡的獨生子。
得到肯定的答覆後,塗璟面上流露出思考的神情,但也只是一下,很快恢復原樣,徑自走開了。
宋伊覺著有些怪異。如果將方才那些長吁短嘆歸類成憶往昔,塗璟最後的那句話就很突兀。想必當中還是有些不便告知於人的事情。
再者...
她看向人群中,與她一道搭船來的人。
他們太招搖了。
*
空桐悅將行李稍微歸類,順帶記住數量,以免等會兒到了住店的地方搞不清。夏墨在她旁邊時不時搭把手,他眼神就沒從空桐悅身上移開過。
“你盯著我幹嘛,我臉上有花啊。”
“倒是不至於有花,不過確實很新奇。”夏墨指的是空桐悅那張不太熟悉的臉,“舒心手下能人輩出啊。”改頭換面有一手。
“有什麼好新奇的,無非是我和你們比起來勢弱些,需要保個底。正巧旅行社裡有個人在休假,我就借個東風,排程排程。”再次確認數量後,空桐悅對小皮卡司機招呼了一聲退到旁邊,省得車發動後被糊滿臉車尾氣。
夏墨跟著她退開,兩人找了個沒那麼擁擠的角落。看著人來人往,陷入了沉默。
“暴亂那晚,其實就已經找人互換了吧。”
空桐悅沒看他,數著從眼前經過的路人,答道:“看樣子舒心跟你交代過了,雖然有點趕鴨子上架,不過她的考慮也沒錯,畢竟人總不能一夜之間憑空消失,事後也不好圓場。”
“她沒說,我猜的,運氣還算好,猜對了。”夏墨語氣蠻輕快,可聽不出心情愉悅,更像是有點苦哈哈。
“合著你誆我話呢。”空桐悅側頭瞧他,對方也同樣看過來,“你這才幾天啊就成這樣了,我看我這千年冰山的外號真是取錯了,早知道該叫你大尾巴狼才對。”
夏墨聽後,擺出很無辜的模樣,攤了攤手:“人類的聯想力很豐富,再加上心有疑惑,很容易發散思維。”當時便已經產生疑惑,事後那替身都在有意避開與人過多接觸,被猜到也是因為演技拙劣。
“至於外號~隨你怎麼叫,怎麼習慣怎麼來,在這地方,有熟人總好過睜眼瞎。”多少能讓夏墨覺著安心點。
夏墨見這會兒空桐悅的目光停留在自己身上,似是有話想說,卻又見她嚥了下去,來回幾次後才給出斟酌後的回答:“怎麼猜到的。”
“沒有藥味。”
那夜夏墨給空桐悅塗過藥,梁綺還給她留了薄荷膏,即便不是特別重的氣味,但湊近還是能夠聞到一些的。後來在漁具店的那個人,儘管她連空桐悅掌心的過敏都複製了,可身上半點藥味都沒有,還有鞋子上那不該出現的溼泥,都在透著古怪,便也能猜出這人有問題,
但對方沒有做出格舉動,而且空桐悅身邊的人也沒有太多異樣,處在某種預設不言明的狀態,夏墨就猜到這事長輩們知情,或者就是他們組織的。於是夏墨禮貌性給一之宮魅提個醒。剛剛又試了空桐悅一句,一試就知道答案。
空桐悅撓撓頭:“做人別太精了,容易捱打。再說,你我都是因為舒心來帽兒山,證明目的相同,相煎何太急。”
“也未必相同。”
“嗯?”空桐悅眯了眯眼,察覺到微妙,“我怎麼覺著有點危險呢?”
“那就當一陣風,聽過就罷了。吃早餐麼,我請。”
話題轉的可謂是相當生硬。他不說,空桐悅也不會追問到底。
“路上吃過麵包了,不餓。你要真好心,就把我那三萬多的門錢抹了吧,逢年過節我一定感謝你。”
“這不行,一碼歸一碼。”這是經過夏墨深思熟慮後的答覆,聽得空桐悅直翻白眼。
她給他比了個大拇指,表示他牛。
“吃早飯麼?”
這話好像剛說過。
“吃,怎麼不吃啊,吃窮你。”空桐悅露出很虛假的笑容,“容我找個攤位先,吃垮你。”
走出幾步發現身後沒人跟上,她轉身,見前幾秒還在說著請客的人正低著頭看手機,手指在螢幕上敲打,像是在傳送訊息。
“邊走邊玩小心近視。”
夏墨把手機收回去,邁步跟上:“人生幾十載,開銷那麼大,你總得容我做點生意賺點錢吧。”
“你做哪門子生意?”
“保密,總之是穩賺不賠。”
*
曹宅
曹達裕給曹老爺子的賬本是早就預留好的,在當中添了幾筆。確實會讓他捱罵,不過也只是傷皮不傷筋的水平。
反觀曹達裕的大哥曹達慷,兩人是截然不同的性子,若是將曹達裕稱為不學無術的混子,曹達慷就是一絲不苟的刻板。他近乎是在被告知後,當日就把賬本送到了老宅,曹達裕則有意拖拖拉拉,磨到後面才看似不情不願地交上去。
查賬是很漫長的過程,尤其曹老爺子年紀大了精力有限,偏又信不過別人選擇自己接手,沒個幾日怕是解決不了。碼頭被查的曹達裕也就懶得殷勤,安排好一些預訂單的轉接後,選擇吃吃喝喝。
閉著眼,翹著二郎腿在躺椅上,在忙碌的宅子裡顯得相當愜意。
他的快樂並沒有持續多久,‘討賬’的便來了。
頭頂蒙上一片陰霾,曹達裕睜開眼,發現曹達慷站在他跟前,手上還拿著單子。
“哥來了,坐坐坐,我叫人給你泡茶。”
“這怎麼回事?”曹達慷把手裡的單子往曹達裕身上一甩,“我盤口上的三號倉庫,裡面多了批建材,可我記憶裡並沒有這筆生意,管事的說是你簽字調過來的。為什麼不過賬?”
曹達裕眼珠子轉了轉,然後從躺椅上站起,賠著笑臉:“這...你也曉得,我那不是被警察暫時封了麼,就借用下你的地方。我那單子是預定的,肯定不能耽誤啊,否則人以後不跟我做生意了。至於為什麼不過賬...嗐,那建材我只收了定金,而且建材是分批到的,十天半月才能到一批,我這不好做賬啊。”
“放屁,那建材一週前就放在我那兒了,但凡防護做差點都能長蘑菇了!如果不是老爺子要查賬,這事兒你還要瞞我多久?預訂單有它的演算法,你接手碼頭也有一段日子,我不相信你一問三不知。說,這批建材的來歷是不是有問題!你不說我就大查,查到有問題我直接把你送進局子裡!”事出反常。本來平日裡他這麼說也就過去了,偏偏老二這會兒被查,很難不讓曹達慷多想。
一聽要鬧大,曹達裕不免有些發慌,大概還是心虛作祟,趕忙拉住曹達慷:“別別別啊,這建材的來歷真沒問題,最多就是...價格方面有點問題。”
為了避免被其他人聽去,曹達裕把曹達慷拉進屋裡,關上門,好一陣解釋。
……
事情說來複雜,歸結起來也簡單,繞不開一個錢字。大概是上月中旬,C市暗標批下來一塊地皮做房地產專案,規模不算很大,卻也不小。透過一些朋友的訊息曹達裕得知這是個外包專案,有些心動。曹達裕自知沒做房地產建設的本事,可還是不想放過肥肉,便打起了房地產建材的生意。湊巧比較相熟的朋友裡有與之相關的,雖然不是抓著貨源的人,卻有別的門路。
他查到外包的公司裡有多位股東,因此公司內基本上大事都需要股東舉手表決,相當於湊錢組局。曹達裕和朋友借用些許門路,找到了當中一位股東,在這局裡投錢加了個槓桿。又在貨源採購上週旋,明面上他是隻拿到建材運輸權,實則也分了一杯羹。大富大貴不至於,小賺一筆還是有的,屬於他自己的小賺一筆。
原本他是想另開一個地方儲存建材,結果第一批建材的速度超乎預料,只能暫放碼頭。後沒隔幾日,他收到風聲說警察在暗中查案,曹達裕不想將這事捅出去,就冒險把東西轉移到曹達慷的盤口,推算時間,等到碼頭解封,第二批建材應該也會到,恰好銜接。
放著放著他就放寬了心,又轉頭忙別的,就給忘記了。結果沒成想警察沒發現,他的好大哥倒先發現了,現下東窗事發,曹達裕只能選擇割地賠款。
他很清楚,以他的本事若是做出頭鳥只有被打掉的份兒,他必須依傍參天大樹才可以活得恣意,必要時候放血割肉不可避免。
曹達慷再刻板,到底是商人,並不會與錢過不去,一番天人交戰後,還是答應幫其隱瞞。至此也算告一段落。
*
帽兒山
昨日夏墨找的嚮導很準時,所有的人入住沒多久便來了。不過夏墨有意讓自己的存在感不高,他的影蹤也無人在意,稍微消失個一天半天的也無妨。
嚮導是開車來的,夏墨讓嚮導稍等片刻,他需要回屋取些東西。上樓時看見尤薇正在樓梯口拿那幾罐沒開封的油漆。
尤薇抬頭看了眼夏墨,又瞥見在門口停著的車子,對他說了一句:“爬山的話最好穿鮮豔點,要是迷路也容易被找。”
夏墨道了聲謝,快步上樓。
他的東西早早就收拾過裝在包裡,放在床尾的地上,一拿便可以走。
大抵是有些急了,拿包時抓到了床單,將床單帶了起來。床單被掀起一片,露出裡面的床墊和床架。正欲伸手將其抹平,目光掃到床架時,動作停下來。
他蹲下身,用手將床單再掀開了點。
在床架和床墊交合的縫隙位置,有一道深紅甚至偏黑的痕跡,手指在縫隙上抹動,指尖帶下一些深紅色的粉渣。
油漆...還是血?
他索性將床墊直接抬起,露出另一面。當他看到後,他確認了答案。
軟硬適中的純白床墊的另一面,是大片的紅色,近乎覆蓋了床墊的一半,在床墊邊緣能看到連成行的紅點,像是滴落造成的。
這是血。
而且是大量的血。
能造成這種出血量,絕對不是輕傷,致命傷也不是沒可能。再回頭看床墊上那一串紅點,就更篤定了夏墨的想法。
在睡夢中或昏迷中的某個人,躺在床上被人襲擊,尖銳的利器刺進身體,可能是一下,也可能是多下,造成大量出血。
事後,這家客棧的人並沒有急著處理現場,甚至膽大到繼續保留床墊,讓人入住。。
“這個地方,之前到底發生過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