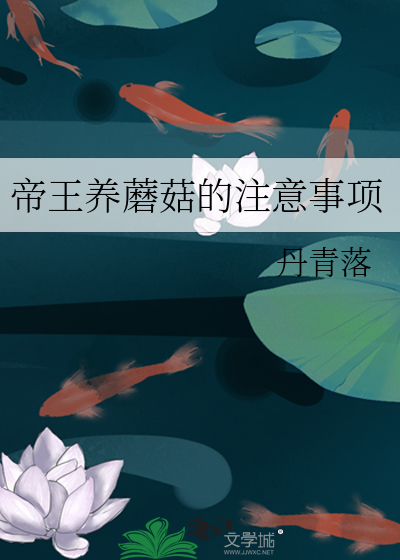一語不語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皇帝出現在午門,御座之前。
眾大臣在行禮之前,赫然發現跟在皇帝身旁的,除了司禮監的幾名太監之外,居然還有張周。
更讓他們驚訝的是,張周堂而皇之從他們身邊路過,往午門的門洞之外走去。
“諸位卿家,今日是會試放榜之日,有些事該有定議。”朱祐樘道,“東廠,把人帶進來吧。”
隨後蕭敬得令後,快步走出午門口,對錦衣衛做了傳令。
在場的大臣也很好奇,皇帝這是要做什麼,等過了半晌,看到一群身著青衫的讀書人,在錦衣衛的押送之下前來,他們更是摸不著頭腦。
而先前已走出去的張周,轉身跟這群人站在了一起。
這些士子的數量,合起來,有四五十人之多。
劉健回頭看了遠處那些士子一眼,趕緊問詢道:“陛下,這是要作何?”
朱祐樘指了指遠處那些士子道:“他們中,有很多是在到京備考會試時,見過程敏政的人,有的則只是在外間議論鬻題的人,東廠嚴查之後選了這些人過來,他們都或多或少牽扯到案中,今日朕要行廷鞫之事,自當將他們都叫來,一併說個清楚。”
“這……”
劉健臉色不太好。
皇帝要親審此案,倒也沒什麼,但一下子叫來這麼多普通的讀書人,事可就不會太小。
這好像跟息事寧人的初衷相悖。
“將涉案另外幾人,也帶過來吧。”朱祐樘又下令。
“是。”
這次蕭敬則輕鬆淡然了很多。
隨著東廠又押送了幾人來,在場官員也只能認出為首的一人,是翰林學士程敏政,而在程敏政身後左右,各有一名看起來比較邋遢的讀書人,其實是唐寅和徐經,而再後面還有三個人,看樣子都不像是讀書的,更好像是給人打雜的僕從。
“宣讀。”
朱祐樘這次是對戴義說的。
戴義走出來,拿著一份奏疏,卻並不馬上宣讀,而是做了解釋道:“諸位臣僚,這一份乃是徐經的供狀,他在北鎮撫司內,供述在入京見程敏政時,曾以金幣賄賂於程府的知客,並有程府知客的口供佐證。三名知客也都做了認人,確定乃徐經無疑……同時在程府的知客手中,搜到行賄受賄的冊子,詳細羅列過去數年曾拜訪過程學士計程車子所向他們所繳的賄賂。”
“陛下之意,去年九月之前的不算,單就以十月及以後到京參加會試的舉子,前去拜訪的人,一併叫來,以此來做現場的指認,看誰有前去拜謁,並有賄賂,行夤緣求進舉動者!”
等戴義把話說完。
隨即他將徐經的供狀,還有程敏政的上奏做了當眾的宣讀。
在場大臣一片譁然。
連劉健、徐瓊和白昂這三個提前得知訊息的,都以為皇帝準備以犧牲程敏政和徐經為結果,平息外間議論,做到息事寧人。
現在他們才知道……皇帝準備玩個大的。
不是說張周、徐經和唐寅涉及鬻題,最後也只有徐經和唐寅去拜訪程敏政的證據?
那也別就這幾個人涉案了,但凡去見過程敏政的,尤其是給程敏政家送過財物的人,一併都給拿了!
這叫什麼?
擴大影響,轉移矛盾。
之前近乎所有人的矛頭都對準了張周、唐寅和徐經,但有了這群人在,事情變得複雜,那三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就不再重要,輿論就會轉向對士子夤緣求進之風的批判。
閔珪急忙出來道:“陛下,如此牽連擴大,是否有損於朝廷的威儀?”
朱祐樘冷聲道:“好端端的會試,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就能捅成個鬻題大案,令朝野不安。如今朕不過是想求個答案,難道這不是諸位卿家想要的?”
皇帝就差說,你閔珪現在又覺得擴大影響不好了?
你們攻擊程敏政涉及鬻題的時候,好像一個個都沒為朝廷的安定著想,感情現在你們覺得事情已超出伱們的控制,所以就要勸朕罷手?
“指認吧!”朱祐樘厲聲道。
……
……
五十多名到場的考生,都是本次會試的舉人,去拜訪程敏政的人很多,不是舉人的並不會被擒拿,當然其中也有一些在外面議論鬻題案比較兇的考生,一併給拉來做個見證。
現場指認這種事,總是需要一些無關人等過來當陪襯的。
“就是他,順天府的袁業,他在去府上時,曾拿了六兩的紋銀,還有一提江南的茶葉……”
說是三個程府的知客,其中有管家、門子、護院,直接過去指認出曾去過程府並送過禮的,直接就被錦衣衛給拉出來。
“冤枉啊!”
“冤枉什麼?要不是去見過,怎可能會被人認出來?連禮都對得上!”
錦衣衛的人也不慣毛病,指認一個拉出來一個。
才不多時,就已經拉出二十多人,這些人或多或少都送了禮。
那邊的指認還在繼續中,而跪在午門前的程敏政則一臉悔不該當初的神色,低頭一臉自責懊惱,簡直是在恨自己生而為人。
說是禮物給下人的,但其實多數還不是進了他自己的口袋?
程敏政也是在想,別人都這麼幹,為什麼我不能這麼幹?
“嗯嗯。”
朱祐樘清了清嗓子。
那些回頭在看指認熱鬧的大臣,都回過頭來。
“諸位卿家,朕這麼查問,是否有失公允呢?”朱祐樘問道。
在場的大臣都不知該說什麼。
現在是徐經一個人送禮的事?送禮的人那麼多,又不止徐經一個,嚴格來說……這麼查才是最公平的。
朱祐樘道:“朕也知曉,沒當會試臨近,各處的考生彙集於京師,總會有人想攀附朝中名儒,以藉此獲得名聲,之前朝廷並未有明文規定如此不可,也給了一些人可趁之機。相信除了程敏政之外,有受謁接見士子的人也不在少數吧?”
大臣們也都不作聲。
在場都是文臣,誰沒見過考生?考生來見的時候,帶點禮物的也不少,有不認識的或是貴重的也給推辭了出去,但有很多本身就是世家舊交的,來送點禮誰會拒之門外?
就好像李東陽……每年去拜訪他的書生,有上百號人之多,難道每個人都是空手去的?
“朕便在此定下規矩,以後再逢大比、春闈之前,任何官員不得接見於各地士子,即便平時要見的,也不可受束脩拜師之禮,但凡相見不得談論考題等事。”
朱祐樘現場定下規矩。
“謹遵御旨。”在場的大臣現在好像沒法對程敏政恨得起來。
程敏政這是犧牲自己,給朝廷立了個規矩呢。
有的人還在想,幸好這次陛下讓程敏政來當主考,鬻題的髒水只往他頭上潑,不然我去當主考,可能所得的結果一樣。
……
……
朱祐樘定完規矩之後,就沉默下來,似在等那邊指認結束。
等過了小半個時辰之後,終於把所有人都指認完畢,本來五十多名立在那的考生,只剩下不到十個人,而張周還在那好端端站著。
“陛下,已查問清楚。”蕭敬過來,當著大臣的面通稟,“如今被拿下的,都是去見過程敏政的考生,有四十二人,其中有三十六人曾帶了價值二兩以上的財物先去相見,這是詳細的名單和財物饋贈情況。”
說著,蕭敬將禮物的清單呈送給皇帝。
朱祐樘道:“那些士子都認了嗎?”
“有幾個不認的。”蕭敬道,“只是少數。”
“嗯。”
朱祐樘臉上多少有惱色。
連大臣都覺得那些打死不認的考生是在找死,程府的人都把他們認出來,而且別的人也都老實認了,結果這幾個還死咬著不肯承認,這是想進詔獄鬆鬆骨頭?
蕭敬道:“不認的人中,多數是在談論涉及鬻題的,其中有幾人還在外大肆張揚,說程敏政跟張周、唐寅、徐經暗中有書信的往來等等……”
“混賬!”
朱祐樘怒道,“他們自己本身就去做了夤緣求進之事,卻刻意中傷於他人,此等人最是不可饒恕!若他們在會試中榜名單之中,一概革除,令其永不得參加會試,也不得為官!這種人,朝廷不需要!”
蕭敬奏請道:“回陛下,已查閱過呈送禮部的貢士名單,此幾人都不在列。”
這一說,在場大臣都明白了。
越是文章寫得狗屁不通,越喜歡搞攀附權貴找後門那一套,而在事不成之後還越無的放矢議論別人試圖攪得朝野不安。
“士子的風氣,就是被這群人搞得不寧,人心渙散,連禮部會試的公義都要攻訐,居心何在?”
朱祐樘此時似乎已絲毫不懼怕鬻題案擴大影響。
因為已經有了現成的“背鍋俠”,這幾位俠客,自己跑去給程敏政送禮,沒得到鬻題,回頭卻攻擊別人……
但凡把事公之於眾,輿論的發洩點就不再是會試的公正性,而在這幾個小人身上。
他們的舉動,還斷了別人攀附的門路。
以後再想透過會試之前拜訪名儒積累名聲,此路可就不通了。
朱祐樘道:“諸位卿家,朕如此處置,你們可有認為不妥之處?”
在場沒人願意出來當這個壞人。
許久沒在朝堂上說話的李東陽走出來道:“回陛下,臣也認為應當革除這些人的功名,黜落為民,以正視聽。”
“好。”
皇帝也不著急。
反正現在矛盾已經被轉移,或許這幾人中真的有被冤枉的呢?
之前是希望輿論早些平息。
現在卻是希望輿論再多溜溜。
朱祐樘點頭:“李閣老一向是為文人之表率,你的建議朕認為非常恰當。先將這幾人收押北鎮撫司內,審問結束之後,再行懲處!至於其餘曾給程敏政送過禮的人……”
本來徐經都以為自己的仕途就此完蛋了,但現在他好像又燃起一些希望。
法不責眾啊。
又不是隻有我一個人這麼幹的。
那麼多人一起落案,要不陛下和諸位閣老、尚書的都手下留情?
李東陽再提議道:“以臣認為,若曾有過夤緣求進之舉的,本次會試若有考中,當黜落,可贖杖刑,發地方黜充吏役。”
徐經心裡一沉,還是完了。
送過禮的,中進士的要被黜,沒中進士的也要交錢贖刑發地方當小吏,那豈不是說以後再沒機會考會試?
也僅僅是比革功名的小人強一點。
朱祐樘道:“那沒送禮,只是曾有拜謁的呢?”
“不問。”
李東陽這麼說,其實也是考慮到自身的情況。
這麼多人來拜訪自己,送禮的也不少,皇帝沒深追究都算是好的,如果單純只是去見見程敏政,也沒有鬻題的證據,就要問罪,那以後恐怕朝中的大臣和士子都要人人自危,文人之間的社交也要斷絕。
“有道理。”朱祐樘此時說這話,其實就是生生在把巴掌往在場文官臉上打。
反客為主。
朱祐樘又道:“程敏政身為翰林學士,臨財苟得不避嫌疑,有玷文衡遍招物議,令其致仕,居於京師不再過問朝事!”
“老臣謝陛下恩典。”
程敏政跪謝。
他在沒有受過刑罰的情況下,取得致仕的結果,既能平息議論,也能讓自己好過一點,程敏政是不敢有怨言的。
朱祐樘又看著蕭敬問道:“對了,張周應該是沒有牽扯到此案吧?”
蕭敬微笑道:“回陛下,貢生張周,從開始就未曾到過程學士府上,二人也未有過書信的往來,自然不會牽扯進內。”
“嗯。諸位卿家也該聽到,不該再議論,以後還要同殿為臣。”朱祐樘點點頭,也是要提醒在場文官。
張周是朕的心腹愛將,你們再談論就有點不識趣。
朕就差告訴你們,現在張周已經是進士,你們以後抬頭不見低頭見,對他好點,也是對你們自己好。
“唐寅呢?”朱祐樘指了指跪著的唐某人。
蕭敬道:“唐寅只跟隨徐經前去拜訪,送禮之事他並不知情,所謂鬻題,也無實證。”
朱祐樘道:“那他的事,就不問。至於另外一人……戶科給事中華昶,以風聞奏事,多有不查不實之處,當嚴懲。”
涉案的人等,基本都已各自有了歸屬。
而剩下一人,也就是華昶。
論罪,其實華昶沒罪,但他卻是始作俑者,是將事態擴大的元兇。
皇帝更恨華昶非要把張周牽扯進內,這才是皇帝覺得華昶不可饒恕的。
“陛下,言官奏事,不該問責。”閔珪道。
朱祐樘搖頭:“若所奏皆都不經過詳查,便以道聽途說來奏事,此風一開,朝堂還有何威信可言?令華昶調南京太僕寺主簿,罰奉半年……其餘涉案人等,著三法司以情節輕重,酌情論處。”
“事已至此,會試放榜及此案議定之事,可一併對外宣之。”
“再有妄自橫議者,與罪者同論!”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