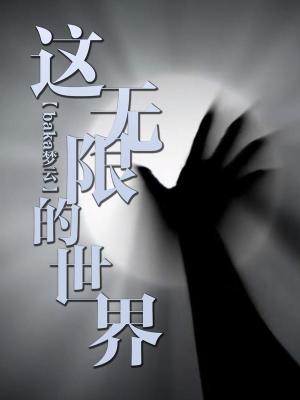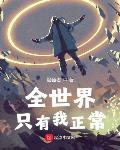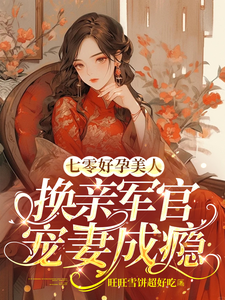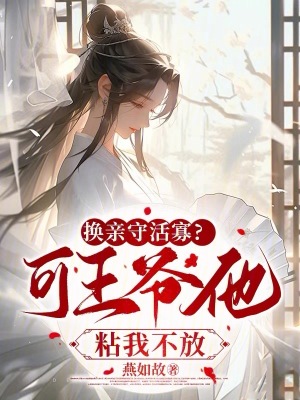第一百一十六章 雖死不可回也
酒釀番茄番茄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還有,各郡國設在洛陽的郡邸和國邸,臣也派人密切關注著,進進出出的,力求嚴格管理。
一來,是防止有趁亂摸魚、假公濟私的長途販運牟利之徒,二來,是防止有郡縣的地方官員,藉機多運貢品進京,以行賄朝臣。”
聽蕭何補充的這兩條,劉季一面生疏地剝著離支果的堅硬外殼,一面深深瞅了他一眼,指著蕭何對眾人道,
“你們都仔細琢磨琢磨他方才說的兩條。
我就說嘛,沒在底下辦過二十年差的人,絕說不出這些門道來。”
漢初君臣均出自布衣,對於蕭何言下所指出的幾處關鍵所在,都心知肚明。
各郡國在洛陽開設的諸多郡邸、國邸,屬於官辦的機構,遠來之人,如要在邸中免費住宿、歇腳,需要當地郡守開具傳,也就是官方的通行文書。
一旦拿到了傳,不僅到達京師後能入住條件優越的郡邸,沿途關津也暢行無阻,不必繳納任何關稅,還可以沿途使用道邊傳舍,享受官府提供的免費食宿。
此外,打點到位的商賈,手中握有傳令,便能無償呼叫官府的驛傳車馬運送私人貨品,由此省下的人力物力與運費,不可小覷。
這些利用官方名義運送到京的貨物,往往藏在各郡的郡邸中,作為貯物倉儲場所,公器私用。更有膽大包天的,竟然公開在郡邸裡擺攤開市,直接販售。
貨物遠途運輸售賣,成本中最大的一部分,便是運費;
而這部分耗資既已省去,再以正常市價出售,對於商人來說,漁利甚豐。
因此,自秦時的上計始,進京上計一事便是不言而喻的肥缺,上計吏每每假公濟私,或攜親帶眷進京遊玩,或趁機夾帶私貨販賣,或無故為商賈們私開傳令,這是各郡大員間公開的秘密,也正是蕭何的題中之義。
***
而他所說的第二條,更是影響深遠。
各地送來的珍奇貢物,除了獻給皇帝外,必有冗餘。而這些刻意多帶來的特產,便名正言順成為賄賂京師朝臣的藉口,畢竟,朝中有人好辦事啊。
今日,在上計吏陸陸續續已抵達京師之刻,蕭何方將此事開誠佈公地攤在日光下來議,其用意不消說,是打算借劉季金口玉言,明確出個章程,以矯正長久以來的不正之風。
“唔,我明白你的意思,你這番提醒很及時。
而且,你敢這麼說,也是不怕得罪人啊。”
劉季將晶瑩剔透的離支果肉湊到眼前看看,又猶疑著放進嘴裡,邊嚼邊說,
“那就傳我的意思,自此次上計始,非上計吏員而私自憑傳進京、私偕人貨、住宿郡邸者,皆坐食贓為盜。
還有,這條不妨寫進律令裡,以儆效尤。
至於那些已經混進各處郡邸的,相國,咱們就乾脆得罪到底,狠狠心從嚴處置,殺雞儆猴吧。”
“臣遵旨,陛下聖明。”
蕭何滿臉喜色,深深籲出一口氣,如釋重負。
劉季忽咂著嘴,捏著半個離支環顧四周,
“這個什麼離支果,清脆爽口,甜膩多汁,我此生竟從未吃過,你們也都來嚐嚐啊。
長沙國與南越毗鄰,想來氣候地氣也相近,不知長沙國種不種得出此果啊?
若是能種,以後讓吳臣時常給我送些來罷。”
他正期待地看著蕭何,卻聽得一把溫柔的女聲道,
“陛下此言既出,恐怕長沙國的黎民百姓,日後要守著離支樹餓死了——”
***
劉季一驚,猛地回頭看向呂雉,她緊緊抿著唇,秀眉微蹙,不怒自威,目光冷峻得令人不敢逼視,
“孟子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皇帝愛吃離支的訊息一旦傳出去,王公貴族必會群起效仿,這不是逼著長沙國將萬畝良田桑田,都改種離支嗎?
若遇到個災年水患,陛下是指望長沙國人以離支充飢嗎?
況且,長沙國山高水遠,一路勞民傷財,只為向京師運送離支,如此行徑,當真不怕萬世恥笑?”
在眾人看來,皇后慣常溫和內斂,任勞任怨,即便常有靈光閃現的精絕之言,但總還是信奉韜光養晦,不肯多搶一點風頭的。
可此番話中,卻冷得似隱隱結著一層霜,可見她是真的動怒了。
劉季被當眾駁了面子,臉上訕訕的,但心知皇后說的是正理,滿心尷尬惱怒沒理會處,忽然瞥見遠遠的殿角里,默默坐著一名史官,正就著木牘奮筆疾書。
他惱羞成怒,不禁疾步走過去,瞪著眼質問那史官,
“你胡亂記了些什麼,給我看看!”
那史官年輕蒼白的臉上閃過一絲驚惶失措,但隨即鎮靜了下來,他以手護住簡牘,認真地答,
“陛下方才說了什麼,臣便記些什麼,並不敢胡寫。
君舉必書,如實記載國君的言行,是臣的職責所在。
這些記錄,是預備給後嗣看的,不是給陛下看的。”
“那麼說,你也記下了我欲向長沙國索要離支?”
“陛下自己說,‘不知長沙國種不種得出此果’,臣如實記錄而已。”
“……這話不能記,你且速速削去罷,恕你無罪。”
皇帝掃了一眼他身前案上的銅削刀,語氣嚴厲,沒有絲毫商量的餘地。
“臣,做不到。”
史官深深伏跪在地,頭也不抬,堅定地回。
***
“你竟敢抗旨?”
“秉筆直書,書法不隱,是臣所奉行的正道。”
“你的正道,莫非比皇帝還大?”
“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
臣的道,比性命還大。”
“我看你也是活膩了——”
劉季早憋了一肚子火無處發洩,忽然暴怒,揚起一腳將史官面前的長方形矮案踹翻,案上的筆墨刀札等物咕嚕嚕滾了一地。
宮人們早嚇得跪了滿地,瑟瑟發抖,任鬆漆硯盒打翻在地,墨汁緩緩淌出,把地面洇得黑擦擦的,也無人敢上前收拾。
眼看遇到了不畏強權的硬骨頭史官,旁觀的呂雉卻無比羨慕,這一切,是她前世所不曾經歷過的。
秦漢時期的史官,譬如秦和西漢時期的太史令、東漢時期的蘭臺令史等,雖為朝廷正式的職官設定,卻基本承襲先秦的史家立場,被賦予了極大的書寫自由,任他們寫下一家之言。
然而,自唐代以降,史官制度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史官改為史館,成立了正式的官方修史機構。
有了史館,便由集體修史編書,並經朝廷重臣宰相監修,確保萬無一失。
儘管史館編纂得更加全面、完整、詳實,但史官們每欲記一事、載一言,往往擱筆相視,反覆討論,個人意志蕩然無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