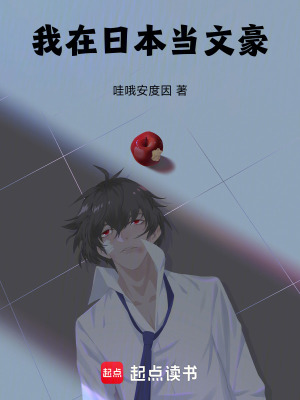荒野浪人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為什麼呢?因為這種蛇有它自己的風格,它尾部快速震動會發出聲響。這種聲響會嚇走它的敵人和入侵者。”他在自問自答,我不解其意。
“藏起你的毒牙,不要搖動尾巴,做那人海里的一滴水。這是渡者八律第一條。”地產經紀人神情肅穆。
“渡者八律?”這又是什麼鬼東西,我暗自思量。很久以後,我才明白,這是用無數個殺人者生命堆砌出來的生存指南,想要活得長久一些,就要恪守這些戒條。
悠長的汽笛從江邊傳來,最後一班輪渡了吧?已是深夜,酒已乾、肉已盡,桌上一片狼藉,絲瓜告辭而去。
他走後我枯坐了良久,他這次來講述的那些渡者三規、六道、八律就象烙印在了我腦子裡,有進無退,唯死而已。
耐著性子等了幾天,老曹頭的電話終於來了,所謂的訓練終於如期而至,老曹頭在電話那頭語速很快,他告訴我,訓練第一課就是練膽。我能聽出他聲音裡的興奮,和刻意壓制的陰笑,我感覺到了一絲不安,噩夢可能再度拉開序幕……
他給了我一個地址,西寶興路633號,聯絡人朱顏,還有一個電話號碼,說是到了,直接打這個號碼,自然會有人接洽。這是什麼地方,我一無所知。電話裡同時要求不準使用任何交通工具,必須跑步前往。我拿出地圖一看,地圖上直線距離至少十公里,每天來回跑步十公里,等於一天一個半馬,這死老鬼葫蘆裡又不知道賣的什麼毒藥。
第二天天氣很好,趁著早晨太陽還未顯出猙獰,我踏著晨曦的露水出發,跑步前往西寶興路633號。出乎意料,並沒有想象中那麼疲累,腿登在地面,只是微微用力,身體就象箭一樣的竄出去,肺部呼吸綿長有力,不像從前奔跑個幾百米,我就喘成了滿是窟窿的風箱。
我穿行在人流和車流中,象是在撒歡的金毛獵犬。我故意跑到逆向的非機動車道上,在即將撞上他們的千鈞一刻,再迅速避開,助動車、腳踏車的急剎總是先響起,緊接而來的就是你腦子有病吧、神經病等等斥罵,最後我哈哈笑著跑回人行道,降低速度以免超過腳踏車道上的助動車,怕引起圍觀。渡者八律第一條-收起你的毒牙,不要搖動尾巴,做那人海里的一滴水。
只花了三十五分鐘,我已經到了老曹頭提供的地址,只是額頭上略微有些汗水,很是意猶未盡,沒能耍開的感覺。擦了擦額頭的汗,我停下腳步,眼前三棟八層的宏偉建築呈幾字排列,鑄鐵欄杆將三棟樓和人行道區隔開來,柵欄裡高大挺拔的喬木鬱鬱蔥蔥,樹冠遮天蔽日,倒是個幽靜的所在。
入口是一條窄窄的柏油馬路,兩車道,青黑的路面,白色的地面標誌,沒有一片落葉,異常乾淨。我徑直往裡走,崗亭裡竄出了一箇中年男子,卻是個保安,他伸手將我攔下。
“先生,現在不能進。”
“什麼?什麼?”我特別的疑惑。
“現在不能進。”保安加重語氣重複了一遍。我第二遍才聽清追悼會三個字,頓時眼前冒出點點金星。
“這裡是?”我狐疑的問保安。
“滾啊!過會再來吧。”保安先生有些不耐煩,揮揮手示意我離開。
我足足愣了五分鐘,呆在原地,老曹頭啊老曹頭,你果然又擺我一道,我暗自咬牙切齒,又想起那個聯絡人朱顏,撥通電話。電話裡是個女人,聽聲音乾脆利落,年紀應該不會超過三十歲。
“您好,哪位?”
“老曹頭讓我來找你的,我在633號門口。”
“噢噢,你已經到了啊,這樣,我還沒有到,你在附近稍微等我一會,我半小時內就到。”我之前還怕對方貴人事忙,現在看來倒是多慮了,老曹頭還是很罩得住。
蹲在人行道的樹蔭下,我眉頭緊皺,心裡卻是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實在是忐忑的很,這所謂練膽到底是什麼名堂,我暗自祈禱這殯儀館僅僅只是個碰頭地點。
一聲尖銳刺耳的急剎車從遠處傳來,我驚訝的看過去,一輛紅色的敞篷跑車快速的滑過來,沒錯,我很確定是滑過來。輪胎與地面接觸的部位已經冒起了黑煙,那車就這樣一路漂移到我面前,堪堪停下時輪胎與馬路牙子親密無間到不足十公分。我能聞到橡膠輪胎經過高速摩擦的焦臭。車裡一個女子,圓圓的一張臉,有些嬰兒肥,齊肩的捲髮,膚色雪白,二十七八左右的年紀。她正瞪著一對杏仁眼側頭看我。我四下左右看看,似乎也沒有別人在場。
“老曹頭說的就是你嗎?”她有些疑慮的問我。
我站起身,點了點頭,看看手機,這才過去不到十五分鐘,好傢伙,這速度!
“上車!”她努了努嘴,示意我坐副駕駛位置。我上車後,那車向右拐彎,徑直駛入了寶慶殯儀館。崗亭裡的保安笑嘻嘻的跟她打招呼,朱老師早。那女子卻不予搭理,冷冷的給了個白眼。車輛的電動欄杆慢慢升起,我的心卻象入了水的秤砣一樣,筆直的沉下去。
跑車緩緩駛入地庫,光線驟然暗淡,我略微側頭去打量那女子,她目不旁視,有暗香襲人,淡淡的若有似無,是這個季節裡綻放的玉蘭花的味道。我卻聞到那香水味裡一絲不一樣的氣息,是陰冷的、黯淡的、淒厲的、慘烈的死亡氣息。這氣息似曾相識,酷似李明死那天,對對對,就是那天的感覺。
“看你妹,沒見過美女啊?”朱姓女子出口成“髒”……
我尷尬的轉過頭,我頭一次跟漂亮姑娘處於這樣近的距離,心跳不由暗自加速。
“沒有……我沒有看你……”我聲若蚊蠅的解釋,也不知道她聽的見聽不見,我的臉有些發燙。這姑娘脾氣好火暴啊,我這樣想著。
“冊那娘,又搶老孃的214車位,冊那娘!”姑娘一邊罵著魔都本地粗口,乾淨利落的從車裡跳出去,請注意,是跳出去!我抬眼看,眼前的車位裡停著輛黑色的小車,車很普通,桑塔納兩千。魔都的大街小巷每天穿梭著數萬輛這個牌子的出租,因此我也認得。
可是這諾大的地庫四周空空蕩蕩,壓根就沒有停幾輛車。至於為個車位發偌大的脾氣?停旁邊不就得了。
很久以後,我跟朱顏熟絡了以後,她告訴我,每一個人都有個幸運數字,這既關乎運氣也是她個人的堅持,一絲一毫也不可馬虎,任何看似偶然發生的事件都有它的機率,而看似沒有任何關聯的事件其中隱藏著命運的密碼。214是她的幸運數字。
我目瞪口呆,眼前身形小巧的姑娘,她暴跳如雷,歇斯底里一腳一腳的踹著車門,左前門被踢得一點點扭曲變形,已經凹了進去,刺耳的警報在地庫裡迴盪,保安驚惶失措的從值班室裡奔跑過來。邊跑邊大聲喊,“朱老師!朱老師!消消氣!消消氣!”
“冊那娘!我的車位,這幾百個車位空著,非搶我的?觸我黴頭是吧?”姑娘的氣勢益發凌厲,還是不住腳的一直踢,一直踢,一直踢。砰!砰!砰!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剛剛去上了個廁所,也不知道誰就把這占上了,我今天晚上就去買黃油漆,給您漆成一圈黃線,保準下次沒人再敢停您的車位了!朱老師,咱別踢了呀……”保安是個四十上下的中年男子,既不敢上去拉她,又怕一會車主找他賠償,一張臉苦的簡直要滴下水來。
“不用你賠錢,老孃自己賠,你叫這傻逼立刻給我挪開!”姑娘仍然是怒罵不絕於口。事態愈演愈烈,正自糾纏的時候,傻逼來了……不對不對,是桑塔納的車主來了。我坐在跑車裡,一時也是不知如何自處。
“你腦子有毛病是吧?你踢我車門作什麼?”傻逼是個大腹便便的男子,腦袋當中禿了一塊,左邊的頭髮卻留長,梳理過去蓋住那塊禿。腋下夾了個黑色手包,手腕上明晃晃的一塊金錶,人未到肚子先到了,看著象是個生意人。
他上去就推了朱老師一把,姑娘一個踉蹌,眼看她一連倒退了好幾步,不嗔不怒,杏眼圓睜咬著嘴唇在冷笑,我立馬跳出車,橫在二人中間,打算做個和事佬。雖說不熟,總是個年輕姑娘,怕她吃虧,我剛要開口。
“你走開!”姑娘一把將我掀到旁邊去了,她徑直走向胖子,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朝著胖子就是一腳,只是一腳……
那胖子“嗷”的一聲捂著褲襠就跪下了……一個車位引發的血案就此發生。胖子這一跪,頭髮散亂,支援中央的長髮掛在臉的左側,有如風中飄絮,又似綠原勁草。手包掉在地上,已經管不了了。兩隻手死死捂住褲襠,眼淚已經下來了,腦袋當中那塊禿幽幽反射著地庫的燈光。
“你他媽的也不打聽打聽,老孃是誰,死胖子。”她惡狠狠的指著胖子的那塊禿頭大罵,隨後跳上紅色跑車,將車往後倒了幾米,這跑車的轟鳴聲瞬間響徹地庫。
在場其他三個人,胖子、保安、我,頓時面面相覷,不知道這姑奶奶到底要幹嘛。我腦子一轉,不好,老天呀老天!她這是在給自己留出助跑距離,說時遲,那時快……
“砰!”一聲巨響,那車一頭撞向了桑塔納。然後像剷車一樣一直把桑塔納推出了249號車位。桑塔納尾燈只剩了一個,後保險槓碎裂,碎片撒了一地,後車蓋彈起,汽車警報淒厲的響著,像是一隻哀嚎著的獨眼蛤蟆……
瘋子啊!這他媽的全是瘋子!絲瓜、老曹頭、還有這朱顏,就沒有一個正常人類,當然,變態裡挑一挑,絲瓜略微正常一些,我真是啞口無言。看保安的神態倒沒有多吃驚,顯然是早就領教過這位的厲害,他是擔心賠錢多過驚訝。
老曹頭確實是給我找了個膽氣第一的好老師,這位膽子豈止是大,簡直能包天……
這聲巨響過後,殯儀館的工作人員紛至沓來,有人認識地上那胖子,就走上去一邊扶他一邊開解,胖子太過沉重,扶的那位很吃力。胖子步履維艱的站起來,兩條腿並不攏,詭異的張開,好像腿裡夾了個西瓜,小腿一直在顫,顯然創鉅痛深。
“周老闆你招惹她幹什麼,館長都不敢惹她,這寶慶殯儀館上上下下三百多口子人,誰見了她不是躲著走,你去惹她幹嘛……”
“她誰啊?”胖子先將頭髮拉回去支援中央,這人倒是很重視自身形象。接著小聲的問,吃了這大虧,也是很有些悔不當初,他欲哭無淚的看著自己的車。
“她就是我們館的‘朱老師’,你這買賣還想不想幹了……”扶的那個小聲說。
“算我點背……”胖子看了看車,又看了看頭髮有些凌亂的朱老師,神情立馬萎頓,就像是隻洩了氣的皮球。
朱老師坐在車裡冷笑不止,嘴裡一口尖利細碎的白牙露出來,泛著寒光。214車位彷彿是個巨大的巢穴,而她就是那巢穴中的母狼。這一畝三分地果然是她的,跺一跺腳,地動山搖。
“別說老孃欺負你,死胖子,這一千,拿去修車。你要是不服,我隨時候著。”她拍了一千塊在周老闆手裡,轉身就走,走過我身邊的時候,輕輕的踢我一腳,示意我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