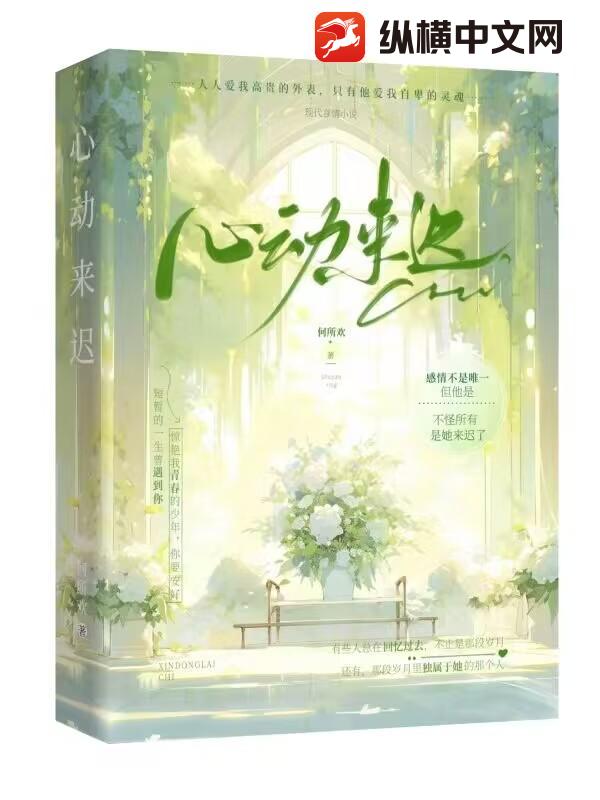桑家靜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他……或許是軍中謀士吧。”
總之,他不可能是宇文晟,她跟他在鄉佐見證下籤訂的婚書、戶籍簿,都明明白白寫著“柳風眠”這個名字。
再者,她可沒聽誰說過宇文晟會是個有眼疾的,所以會不會是宇文晟早預料到有埋伏,故意讓柳風眠當箭靶替身,替他擋害?
再引申到他當初在營寨附近溺水一事,或許也是這般遇上危機了。
秋將她放了下來,呆臉悶悶不樂,覺得自己準備了那麼久,最後卻功虧一簣,是一名刺客的恥辱。
“你確定他真不是宇文晟?”
鄭曲尺斟酌了一下,反問道:“當時在營寨裡,我近距離接觸過宇文晟,他眼神深不可測,比死屍更駭人,可柳風眠有眼疾,你剛沒看到,他眼睛上蒙了紗布?”
“……哦。”秋有氣無力應一聲。
鄭曲尺沉凝著走了一段時間,回過頭奇道:“你一直跟著我做什麼?”
任務失敗,他不是該幹嘛幹嘛去嗎?無論是告黑狀還是正常彙報任務都隨他。
秋垂下眼:“我沒有地方住。”
“所以呢?”
他偏過臉,理直氣壯:“我看過,你修的新家很漂亮,我也要住。”
“……”鄭曲尺暗吸一口氣。
何等厚顏無恥之徒啊!
她還清晰記得不久前,因為她打算拒絕刺殺任務,她被他當成叛徒打算清理門戶,這會兒他怎麼能毫無愧疚之心想住進她家裡?
想屁吃吧他。
鄭曲尺果斷拒絕:“沒多餘的房間。”
這也是大實話。
當時他們一家急需落腳點,又窮又急的,她只能規劃出三間平房做剛需,若以後人口多了再修建。
但這個問題對於秋而言,並不是大問題:“我可以繼續跟你住同一間啊。”
“我大哥跟么妹膽小,你來路不清,還經常神出鬼沒,會嚇著他們。”
“你們父母是墨家弟子,你們三兄妹也是,可你為什麼要一直要瞞著他們,不讓你大哥知道你在替墨家做事?”秋不理解。
這件事情鄭曲尺也不清楚,但她知道,桑大哥對於他們的過去,父母的死亡,甚至包括她曾經在墨家使用的名字,這一切都厭惡且避諱。
倘若讓他知道她在替墨家當刺客,她都不知道他會做出什麼樣的事來。
她不想再跟秋說這些,正想轉移話題時,她忽然想起一件被她忽略掉的事情來。
她緊聲道:“你之前說,鉅鹿國的人引宇文晟他們去春出渡,是因為在那裡早就布好機關陷阱?”
“嗯。”
“什麼樣的埋伏,憑方才那三十幾名騎兵能不能破得了?如果出戰的不是宇文晟,而是其它人呢?”
秋:“鉅鹿國的司馬陌野武功不及宇文晟十分之一,但兩人交手,他卻每一次都能夠從宇文晟手上僥倖逃脫,靠的就是他一手變幻莫測的機巧術。”
這一句話,算是解答了鄭曲尺心底的全部疑惑。
“一個孩童如果手握利器,也是能殺得了飢腸轆轆的惡犬。”
連宇文晟都應付不了鉅鹿國的機械殺器,其它人就更不用說了。
“你怎麼了?”秋歪著頭盯注她,總覺得她現在好像正面臨著一種很艱難的抉擇。
鄭曲尺眼中醞著最後一絲希望,問秋:“你幾歲了?成親沒有?有鄴國的正規戶籍嗎?願意入贅嗎?”
秋被她連番的問話整個怔愣了半晌,才道:“十五,沒有,沒有,不願。”
鄭曲尺很失望,因為她好不容易說服自己既然秋敢自己送上門,她就敢老牛吃嫩草,不去想那個騙了她的倒黴贅婿,管他去死。
但她做夢都沒想到,這棵嫩草竟然連十六都沒有,她就是再喪心病狂也啃不下嘴啊。
“shit!”
鄭曲尺低咒一聲,頭一轉拐個彎,然後拼足了全部勇氣跟不知明的怒意,就朝春出渡的路奔跑而去。
風揚起她面巾跟衣襬,她跟只憤怒的小鳥一樣,要把被“綠皮豬”給偷走的“鳥蛋”給搶回來。
秋一驚,追上去:“尺子,你去哪裡?”
鄭曲尺牙齒咬得“格格“作響,眼裡閃著一股無法遏制的怒火。
暗罵道,宇文晟這個狗東西,自己倒好懂得躲危險,偏偏要讓她那柔弱不能自理的夫婿去冒險,他還有眼疾啊。
如果他這一趟死了,她剛新婚的人,豈不轉頭就成寡婦了?
當然這個不重要,重要的是鄴國這個催起婚來不要命的國家,連年輕寡婦也得參加送親隊伍,為國家添兒添女做貢獻。
而下一次,她可不知道自己還有沒有這麼幸運,能夠遇上一個像“柳風眠”一樣合適的人選了。
所以她給自己定下一個底線。
在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況下,也不會輕易放棄他。
——
春出渡是在福縣郊野的渡口,這個地方因近年持續大旱,河水乾涸,早就廢棄不用了。
鄭曲尺到了渡口,沒有第一時間上去,而是找了一個高一點、可以隱蔽的位置,打算先觀察一下情況。
她看到了已經露出河床的碼頭處,血蜿蜒蔓延成枝蔓的形狀,倒了不少的人,看得出來不久之前有兩隊人馬在此互相廝殺。
看周圍沒有了其它人在,她才跑過去。
她深吸一口氣,刨了刨地上伏倒的人,對方身上的冰冷與血腥味道,令她指尖有些發麻。
忍著不適扒拉一遍,她不知道是該鬆一口氣還是頭痛,這裡面並沒有她那個倒黴的夫君。
哐、哐、哐!有什麼金屬聲劇烈碰撞的聲音在東邊的河灘隱約傳來。
鄭曲尺眼一轉,看了看沒有遮擋物的河灘,選擇迂迴的方式,從河灘上的樹坡小心翼翼地靠近。
手藝人的謹慎小心,算是刻在她的骨子裡了。
她蹲在一棵櫟樹旁,將掉落的橡子踢開,輕巧地分開眼前半人高的枯黃野草,朝下一看——
只見河灘上,正進行著一場驚心動魄的戰鬥,一方黑甲軍豎起木盾正抵擋著另一方的遠端射殺,雖死不退,雖傷不撤,只因在他們後方有一個被鎖住手腳、手腕跟腳踝全是血的男子。
那人臉上又重新戴了一張黑白麵具,但根據他身上的衣物判斷,應該就是“柳風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