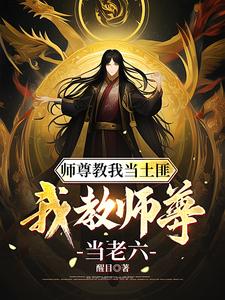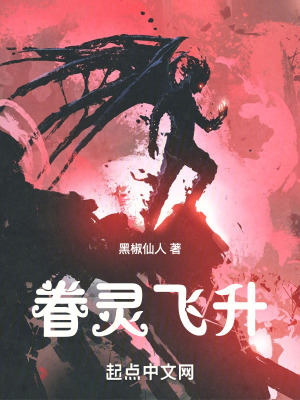第288章 陛下,才是最憋屈的人啊···
血狸奴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沒到時候?”
“太子這話,究竟是······”
短短不數日,太子劉勝真對匈奴人的態度,便以長安為中心,迅速朝四面八方散播開來。
倒也不是說整座長安城,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太子宮、放在了劉勝的一舉一動上;
而是因為此番,匈奴人再度入侵漢邊,相較於過往這些年,實在是有些‘非同尋常’······
“這些年,匈奴人雖也是歲歲叩邊,但自先帝繼位之後,已經很少大舉南下了;”
“雖說每年秋後,邊地都有零散的匈奴騎兵出沒,但大都是少則十數、多則數十人而已,極少聽說有百人以上成群的匈奴胡騎。”
“也不知今年,這是怎麼了?”
東市外的茶肆,八卦黨們本能的聚在了一起,又極為自然的聊起了最近,發生在北方邊地的事。
而在這樣的日子,還能有空聚在茶肆、還敢說起這些事的人,不說有多麼滔天的背景,也至少是有一些訊息渠道的。
這不:有人一發問,立時便有好幾個人激動地跳起,顯擺起自己‘掌握更多資訊’的優越感來。
“嗨~”
“可不就是去年,關中大豐收,匈奴人又在年初的冬天遭了白災嘛~”
“——自己過的緊緊巴巴,全年都吃不上一頓飽的;”
“又聽說俺們漢人糧米富足,那些個披髮左衽、率獸食人的胡蠻,還坐得住?”
“牛羊掉膘,婆娘不下奶,娃兒餓的哇哇哭,可不就盯上俺們漢家了嘛······”
嘈雜中,一大漢羊做灑脫的一番解讀,頓時引得在場眾人連連點下頭。
去年的關中,確實迎來了最近十數年最大的一次豐收。
至於原因,自然是前一年,關中全面積、大範圍‘歉收’,也從某種程度上,保留下了田地的不少肥力。
根據內史、御史大夫等屬衙的匯總:關中去年的整體平均畝產,竟達到了足足四石一斗!
按照太祖高皇帝‘賜民戶田百畝’的標準,平均算下來,關中每一戶農戶,去年都收穫了四百一十石米糧。
三十稅一的稅率,便是十三石多、不到十四石的農稅;
再加上每‘丁’四十錢,也就是摺合接近一石糧食的口賦。
毫不誇張的說:去年,關中百姓的整體平均淨收入,達到了三百九十石糧食以上!
相較於吳楚七國之亂爆發的天子啟新元三年,戶均一百多、不到二百石的淨收入,足足翻了一倍不止!
如此豐收,若是放在往年,雖然也足夠讓人高興,但考慮到‘穀賤傷農’之類的因素,這場豐收給農戶帶來的利好,其實也非常悠閒。
但在今年,情況卻明顯不同了。
——前年秋收之後,尚還沒有獲封為儲君的劉勝,奉命負責糧價平抑一事;
之後,劉勝順理成章的推出了治粟都尉,並制定了‘少府掌治粟都尉,對關中糧價進行宏觀調控’的大政。
在當時,農戶們大都還以為:劉勝這一手治粟都尉、宏觀調控糧價,單純是為了不讓糧價暴漲,給糧價劃定一個上限,免得百姓吃不起價格暴漲之後的高價糧。
而在今年,迎來全面大豐收,又隨即開始為‘穀賤傷農’而擔憂起來的關中百姓,才總算是明白了治粟都尉,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官署;
宏觀調控糧價,又是多麼有利於窮苦農戶的善政。
——前年,關中大範圍歉收,治粟都尉透過售賣平價糧,將糧價死死鎖定在了百錢,乃至七十錢以下;
這確保了關中絕大多數農戶,都能買得起足夠整個家庭半餓不抱的熬過那一年的糧食。
而今年,關中全面豐收,治粟都尉也還是站了出來,毫不遲疑的發出通告:以每石四十錢的價格,無限量購入糧食!
四十錢一石,雖然較去年,乃至往年的糧價都稍低了些,卻也還是讓整個關中,都被一陣歌功頌德的讚歌所籠罩。
——開什麼玩笑!
——四十錢一石,還是無限量購入,還要什麼腳踏車?!
這要是放在過去,來這麼一場大豐收,那關中的糧食商人們,指不定鼻孔要昂的多高!
諸如‘今年關中不缺糧食’啦~
什麼‘愛賣不賣,你不賣有的是人賣’啦~
甚至是‘我家倉庫快滿了,要賣就抓緊,過期不候’之類的話術,都會成為糧商們從農戶手中,壓價購入糧食時的說辭。
在某些時候,甚至可能會出現某個農戶,因為實在賣不出手裡的糧食,便只得到處奔走,求爺爺告奶奶,甚至是送禮疏通關係;
為的,卻只是把手裡的糧食,以勉強不算白菜價的價格賣出去。
賣糧都需要求爺爺告奶奶,乃至是走關係送人情,量具、運費,乃至是交付幣種等彎彎繞,自然也就是題中應有之理。
但現在,有少府治粟都尉在,一切,就都回到了正常的軌跡。
——糧商們,並沒有因為今年的大豐收,而端起‘糧食紅利’的架子;
如往常般,提前和農戶聊好價格,又在秋收當天派去運糧的車馬,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整個關中近百萬戶農戶,四萬萬餘石糧食,少府治粟都尉明明連三分之一都沒吃下,但糧價,卻被‘治粟都尉’四個字,穩穩頂在了四十錢以上的價格。
簡單來說:治粟都尉的存在,讓糧食豐收的紅利,真正落到了辛勤的農戶手中,而不是被糧商米賈,以及商賈背後的權貴所分食。
而在這‘日子過得越來越好’,而且是肉眼可見的越來越好的微妙時刻,匈奴人十數年,乃至數十年未曾有過的大規模入侵,無疑是在以長安為中心的‘泛長安’地區,引起了巨大轟動······
“嘿!”
“要俺說,都忍了這麼多年了,早就該跟小娘養的匈奴人幹一場了!”
“——就連家裡的娃兒,那都是不打不成器;”
“那些個蠻子,若不狠狠打上一通,它能老實?”
人群中,嘴炮黨開始發力,頓時引得眾人矚目。
待看清那嘴炮黨,是一個身高七尺有餘,虎背熊腰、滿臉橫肉的彪形大漢,眾人又各自將頭別過去,不再看向那嘴炮黨。
——和後世的嘴炮黨、鍵政家截然不同的是:如今這個時代,很少有‘站著說話不腰疼’的人。
至少在這貫徹整個社會的尚武之風影響下,幾乎沒有人,會在有關戰陣、外族的事上放嘴炮。
便說此刻,圍聚於茶肆內的眾人,就有至少九成的把握:萬一真打起來,那放大話的‘嘴炮黨’,肯定會回家拿上長弓、短劍,並前往內史自發報名,甘願成為一個運糧民夫。
但有嘴炮黨的地方,往往也同樣有理智者。
“話是這麼說,但真要細算下來,太子說的,其實不無道理。”
“大家夥兒想想:過去這些年,我漢家為何要忍辱負重,給那匈奴北蠻送去公主和親,又陪嫁各式財貨?”
“——還不是我漢家的步卒,追不上匈奴人的胡騎嘛?”
“過去這些年,先太宗皇帝、陛下省吃儉用,在代、趙北境興建了不少馬苑,不就是為了養馬,好組建騎軍嘛?”
“就說這回,他匈奴北蠻大舉南下,沿途卻壓根兒沒顧上搶掠,只徑直跑去雁門,毀了雁門苑、擄走了苑中馬匹。”
“這不就等於是說:他匈奴人,也怕俺漢家組建騎軍,再派騎軍對陣匈奴胡騎嗎?”
“匈奴人怕了,那不正說明俺們漢家是對的?”
“若是不對,匈奴人也不至於嚇得大舉南下,耗費糧餉無算,卻只為毀去一個雁門苑了······”
這話一出,茶肆內詭異的氛圍,才總算是被一陣稀稀拉拉的呵笑聲驅散了些許;
那彪形大漢聞言,也並沒有再固執己見,只頗有些憋悶的咬咬牙,又極盡不甘的點下頭,同時不忘勐拍一下大腿。
“唉!”
“道理俺都懂!”
“就是憋屈!”
“——俺漢家泱泱大國,赳赳武風!”
“竟容他小小一個匈奴,欺負到了這般地步?”
“特孃的!
!”
便見那理智者聞言,呵笑著起身,又悲古懷秋般,長嘆出一口氣。
“唉~”
“說憋屈,誰不憋屈?”
“俺們憋屈,旁人就不憋屈了?”
“——真要說起來,陛下,可比俺們憋屈多了······”
“畢竟忍辱負重的,是陛下;”
“屈辱和親的詔書,也是陛下親手蓋下印璽的······”
···
“連俺們都覺得憋屈,陛下能不憋屈?”
“太后能不憋屈?”
“更別說太子,才剛十五六歲,正是血氣方剛、少年熱血的年紀;”
“能不憋屈???”
“說到底,和親嫁的,那都是劉氏宗室女,都是陛下、太后的晚輩,更是太子血脈相連的姐妹;”
“可即便如此,陛下、太后,乃至是先帝,都在忍。”
“為的,不就是再多準備準備,免得一場決戰打下來,就把俺們這些莊稼漢給壓垮,讓先帝的齊天恩澤,都付諸東流嗎······”
有了這句話,茶肆內的氛圍,才終於竹簡趨於正常。
——在先前,茶肆內的眾人雖大都不開口,但幾乎每個人的目光中,都能看見不時閃過的兇光!
而現在,在聽聞那句‘不都是為了我們嗎’之後,眾人一改先前,那見誰都恨不能一口吞下的兇狠,只此起彼伏的長吁短嘆起來。
“是啊······”
“俺們農人、莊稼漢,雖說也有血性、骨氣,但也終歸是憋屈慣了;”
“可陛下、太后,那可都是威儀自具,打自從孃胎裡出來,便從不曾低過頭的人······”
“為了俺們這些農人,陛下、太后強忍屈辱,再三嫁女和親。”
“若俺們再說三道四的,可實在有些不知好歹了······”
···
“也不知道這次,匈奴人又是什麼藉口?”
“——嗨······”
“——說是幾年前,我漢家送去的公主,其實是個假公主;”
“——匈奴人‘不堪其辱’,才大舉南下叩邊,討個說法······”
“嘿······”
“說的比鳥叫都好聽······”
···
“那陛下這回,只能嫁個真公主過去了?”
“——不大清楚。”
“——若再行和親,應該大抵如是了。”
“唉······”
“嬌生慣養的宗室女,卻要嫁去塞外苦寒之地······”
···
“誒?”
“俺聽說,這匈奴人,還會娶自己的母親做婆娘?”
“——嘖嘖;”
“——沒開化的蠻子,懂個屁的禮教人倫。”
“——茹毛飲血、率獸食人,說的可就是這些蠻子。”
“哈?”
“這是真的?”
“匈奴人,真的吃人肉、喝人血?”
“——可別一口一個‘匈奴人’了;”
“——就那群蠻獸,能叫人嗎?”
“倒也是······”
···
熙熙攘攘的交談聲,隨著茶肆外響起的一陣嘈雜,而短暫中斷了片刻;
待一行車馬浩浩蕩蕩走過,茶肆內,才再次響起一陣滿帶屈辱,又極盡無奈的嘆息聲。
“那,是典客的車架吧?”
···
“如此陣仗,是要去迎匈奴人的使者?”
···
“唉······”
···
不知不覺之間,日落西山,夕陽西下。
茶肆內的八卦黨們,也都帶著各自的憋悶、愁苦,拜別了各自的朋友,先後朝北城的各個方向散去。
——再有半個時辰,便是宵禁。
對於長安城北半城而言,宵禁,便意味著黑暗。
而在這微妙的關頭,即便是平日裡徹夜燈火通明、瑟笙不絕的尚冠裡,也難得陷入一陣死寂。
唯獨皇宮。
唯獨長樂、未央兩宮,在這夜幕即將到來時,仍亮著堆堆篝火、點點燭光。
沒人知道長樂宮內,竇太后在做些什麼、說些什麼、想些什麼;
也沒人知道未央宮宣室殿內,天子啟又召來了那些人,正商量著什麼事。
但所有人都清楚:這一次,漢家大機率還是要退縮、還是要委曲求全;
而先前,被整個長安,乃至整個天下寄予厚望,寄希望能‘血氣方剛’的太子劉勝,卻在這個夜晚出現在了······
不是未央宮;
而是長樂宮長信殿內,和祖母竇太后、姑母館陶主劉嫖,以及年幼的‘未婚妻’、準太子妃陳阿嬌,同坐在了上首御榻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