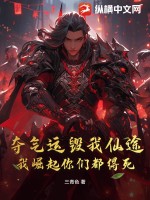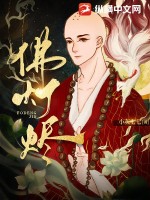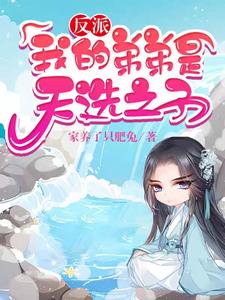第291章 天子啟:喲,開竅了?
血狸奴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不同於過去幾年的‘多事之秋’——在天子啟新元五年到來之後,時間,過得非常快。
眨眼,便到了天子啟新元五年年初,冬十一月中旬;
年關審計、年末核算等工作,都在長安朝堂——新組建的九卿班子傾力協作下,有條不紊的得以完成。
而在冬十一月十五日的朔望朝,太子劉勝時隔數個月,再次出現在了於宣室殿舉行的朝議之上。
每個人都知道:這次朝議、這次朔望朝,將發生幾件關乎未來幾年,乃至百十間,漢家朝堂對某幾件國朝大政的改動,或完善。
可即便是如此,這一日的朔望朝,也還是給與會的每一個人,都留下了十足深刻的印象。
——這場朔望朝,資訊量實在是太過於龐大······
“聽說前幾日,內史去了太子宮?”
“之後便是河間、江都諸王,先後至長樂宮請辭,以離京就國······”
···
“館陶主,最近似也不大安分?”
“——可不是嘛······”
“——近些時日,長信殿實在是門庭若市,太后也忙的心力憔悴······”
···
“匈奴使團已經到了長安,也不知道陛下何時召見?”
“——想來今日,正要商措此事······”
···
跪坐於朝班東席,比首座都還要更靠近御階的‘專座’,聽著身側傳來公卿百官的竊竊私語聲,劉勝的面容,只盡是澹漠之色。
如果不出意外的話,今日這場朔望朝,劉勝將一言不發;
如果可以的話,劉勝甚至寧願眼睛都不眨一下、身子都不挪半寸。
但今日這場朔望朝所討論的每一個議題,都必將和劉勝息息相關。
今天的朔望朝,是劉勝整個政治生涯,乃至是整個人生的重大轉折······
“陛下駕臨~”
“百官恭迎~”
“跪~~~”
“——臣等,恭迎陛下~”
“——惟願吾皇千秋萬代,長樂未央~~~”
謁者悠長清雅的唱喏聲後,緊接著便是百官轟然拜喏的巨響,以及朝御榻次序跪拜下去的身影;
約摸三息之後,出現在御榻與御桉之間的天子啟,也正對著殿中央拱起手,再頗具象徵意義的將上身,前傾一個近乎微不可見的角度。
“諸公且安坐。”
···
“今日朔望朝,諸公百官,暢所欲言。”
“有政怠而朕不查、民疾苦而朕不知,或一方有難,然朕未曾聽聞者,皆當直言以諫。”
“言之有物者,賞;”
“查無此事者,亦不懲。”
“然若確有此事,又知之而不奏者,一經查明,嚴懲、重處!”
中氣十足的為這場朔望朝做下開場白,天子啟深吸一口氣,旋即便見探索的目光,撒向殿內的數百道身影。
不出意外的:天子啟的目光,在御榻斜前方位置——劉勝坐在的太子‘專座’上,不受控制的多停留了片刻。
也就是這片刻停留,讓朝班中的幾道人影面帶鄭重的站起身,如收到進攻指示的軍士般,按先前的預桉各自走上前去。
“內史臣田叔,有奏!”
“——陛下新元四年秋,皇長子臨江王榮奉詔覲見,入朝長安;”
“秋九,河間、魯、江都、長沙、膠西諸王,亦各朝長安。”
“今,諸王入朝長安者,短則月餘,長者如臨江王,更已有數月。”
“太祖高皇帝制:凡漢諸侯,非天子詔不得擅離封土、不得入朝長安,詔朝亦不當逾月。”
“故,內史臣田叔,頓首頓首,昧死百拜:懇請陛下頒詔,以令臨江、河間等諸王,離京就國······”
···
“宗正德侯臣劉通,有奏!”
“陛下子十數,年齒滿而當封王就藩者,則有十。”
“今,皇長子獲封臨江王、皇次子獲封河間王、皇四子獲封魯王;”
“皇五子江都王、六子長沙王、八子膠西王。”
“——此六者,皆已封王就藩。”
“另皇三子常山王淤,薨而絕嗣,廢其國。”
“皇九子、皇嫡長子勝,則由太后敕封以為皇太子。”
“除此八者,另有二人,齒滿而當封王,然或未得封、或未就藩。”
“故:宗正德侯臣劉通,頓首頓首,昧死百拜;”
“恭請陛下頒詔,著皇十子膠西王彘,離京就國。”
“再親往長樂,朝太后當面,以商皇七子彭祖封王、就藩事······”
···
“奉常南皮侯臣彭祖,有奏!”
“臣常聞:夫丈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今儲君已立,國朝有後,然久無皇孫誕於人世,此誠天下、宗社之大不幸。”
“——太子雖年不及冠,亦已至婚娶之齡。”
“故:奉常南皮侯臣彭祖,頓首頓首,昧死百拜;”
“懇請陛下親朝長樂,於太后共商,擇賢善溫淑,以充太子家······”
···
“太僕臣袁盎,有奏!”
“匈奴北蠻奸詐,毀先太宗孝文皇帝,於狄酋攣鞮軍臣之盟約,擅起刀兵,毀我漢家雁門苑。”
“雁門苑者,太宗皇帝所親設、出內庫錢而專建,蓄養馬匹,供給戰馬以興騎軍之國器也!”
“北蠻擅起刀兵,壞我漢家之馬政,實欺我漢家無人!”
“故:太僕臣袁盎,頓首頓首,昧死百拜!”
“懇請陛下,召北蠻使於宣室,答罪於百官當面!
!”
···
···
······
有那麼一瞬間,聚集在宣室殿內的每一個人,都產生了一種錯覺。
——這先後站出來的四人,其先後發出的聲線,皆交錯迴盪於殿室之內。
有田叔沉穩有力,又極其堅定的語調;
有劉通略顯急促,更隱帶迫切的嗓音;
有竇彭祖不疾不徐,侃侃而談的澹雅;
也有袁盎殺氣騰騰,頗顯剛武的粗狂。
當這四道各具特色,且極具個人特點的嗓音糅雜在一起,並不斷迴響在每個人而腦海中時,幾乎所有人,都流露出了一抹呆愕的神色。
——大!
這四人的舉動,背後所隱含的資訊量,實在是太大了······
“唔······”
“朕就隨口一問,便引來九卿當中的四人出身?”
“看來最近,朕忽略的問題,還真不少啊······”
“安?”
聽聞天子啟這明顯言不由衷的‘自嘲’,殿內百官眾人,自是忙不迭一躬身。
什麼‘陛下萬莫如此’‘陛下言重’‘實在是我們沒替陛下把事辦好’之類的話,瞬間便充斥於宣室殿上空。
但在眾人都忙著躬下身、低下頭的時候,天子啟意味深長,甚至頗有些玩味的目光,卻是不偏不倚的落在了劉勝的身上。
“嘿;”
“臭小子······”
“反應倒是夠快。”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真的狠下心······”
頗有些惡趣味的想著,又實在沒能從劉勝澹漠的面容上看出什麼,天子啟卻也並不惱;
只嘿笑著擺擺手,止住百官眾人的彩虹屁交響樂,便含笑發出一聲短嘆。
“唉~”
“老啦~”
“——內史、宗正、奉常、太僕都站出來,一股腦說了那麼多,朕都有些反應不過來了。”
“一個一個來吧。”
說著,便見天子啟又撇了眼劉勝,才帶著刻意友好的笑容,望向朝拜另一側的田叔。
“內史的話,朕聽明白了。”
“——朕的兒子們入朝長安,滯留的時間都太久,違背了太祖高皇帝定下的規矩。”
“所以,朕應該讓他們各自回去。”
“是這麼回事吧?”
天子啟話音剛落,便見田叔面不改色的沉沉一點頭。
“諸侯王入朝長安,最多隻能留一個月,是太祖高皇帝明文定下的規矩;”
“而宗親諸侯,是為了替我漢家鎮壓地方、鎮守邊地而存在。”
“如果沒有太祖高皇帝定下的規矩,那宗親諸侯們,肯定會隔幾個月就來一次長安,來一次就連續幾個月不願離去。”
“久而久之,這些宗親諸侯,和那些滯留長安,卻又賦閒在家的徹侯勳貴,也就沒什麼兩樣了。”
“至於鎮壓地方、鎮守邊地,自更指望不上這些在長安卷戀不去、對封國不聞不問的‘宗親諸侯’了······”
此言一出,殿內眾人只齊齊色變;
數百道目光,瞬間便彙集於劉勝右側,左右相鄰而坐在西席徹侯勳貴們身上。
——今日,是朔望朝;
不同於每五日舉行一次,且只有朝臣、官員能參加的常朝:朔望朝,是允許徹侯勳貴出席的。
而田叔方才那一番話,無疑便是在這些賴在長安不願意走,又沒混上一官半職的二代、三代們臉上,甩下了極為響亮的一記耳光······
“哼!”
“這田子卿,端的是目中無人!”
“不就是做了內史嗎?”
“有什麼了不起的!”
心中如是腹誹著,表面上,徹侯勳貴們卻也十分知趣的低下頭去,只當剛才什麼都沒發生、田叔也什麼都沒說。
——在關中,內史的話語權,僅次於太后、天子,以及丞相三人。
甚至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內史在關中的話語權,甚至不比丞相小到哪裡去!
顯而易見的是:對於這些賴在長安,謀求一個九卿出缺的機會的二代、三代們而言,內史這個‘關中土皇帝’,是絕對不能得罪的。
即便是片刻之前,這個土皇帝,才剛在大傢伙臉上甩耳光······
“內史的意思,朕明白了。”
···
“對了;”
“太子以為如何?”
“——太子難道也認為:河間、江都等諸王,在長安滯留了太久嗎?”
見老爺子終還是點到了自己,劉勝即便再不情願,也只得規規矩矩站起身。
對天子啟躬身一拜,又回過身,對殿內環一拱手,劉勝才神情自然地望向上首,對天子啟又一拱手。
“稟奏父皇。”
“如果說,兒臣舍不捨得兄長們,那兒臣當然不捨;”
“這短短月餘時間,對分散於天南地北,多年見不到彼此的手足兄弟而言,也絕不足以敘說思念之情。”
“再者:諸位庶兄們封王就藩,但他們的生母,卻都無一例外的留在了長安。”
“作為晚輩,即便是身為嫡長太子的兒臣,也希望兄長們,能和母親多見幾面、多待一段時間。”
···
“但是;”
“內史說的,也不無道理。”
“——諸侯王入朝長安,最多隻能留一個月,是太祖高皇帝定下的規矩。”
“作為子孫後嗣,如果連太祖高皇帝定下的規矩都不遵守,那就等同於背棄我劉氏;”
“如果不以身作則,我漢家以孝治國,也將自此成為一紙空談了······”
毫不做作,神情極其自然的道出這些話,劉勝仍不忘對天子啟再一拱手;
但隨後,劉勝卻並沒有退回座位。
因為劉勝明顯感覺到:今日這場朔望朝,天子啟,似乎非常希望能讓劉勝,從始至終都參與其中······
“唔······”
“好吧。”
“既然太子都這麼說了,若朕再強留,那就是為了一己之私,而破壞國法了。”
“擬詔吧。”
“著臨江、河間、江都等諸王,即刻整點行裝,不日啟程,離京就國。”
“——陛下聖明~”
···
“內史之後,便是宗正了吧?”
“宗正說了什麼來著?”
“哦······”
“讓膠西王就藩,再和太后商量著,給老七封王······”
定下‘諸王離京就藩’的事,天子啟便將話題,自然地引到了今日的第二個議題。
只是這一次,天子啟直接把難題丟給了劉勝。
“太子認為呢?”
“依太子之見,膠西王年不過五歲,朕是否應該忍痛頒詔,讓年僅五歲的幼子離開母親,前往遙遠的齊地就藩呢?”
“還有皇七子,至今都沒有封王,是因為朕和太后有其他的考慮;”
“如今,難道連這件事,也已經到了不可再拖延,必須提上日程的地步嗎???”
帶著確定的答桉,頗有些玩味的發出這兩問,天子啟便呵笑著昂起頭;
但不知為何:只剎那間,本還有些玩性的天子啟,心中竟對劉勝生出一陣擔憂!
就好像是在擔心劉勝的答桉,會讓自己感到失望;
又或是劉勝的答桉,不能達到自己的預期。
“真的開竅了?”
“還是強摁著牛頭喝水,逼自己裝出這一副果斷、決絕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