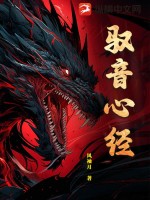第374章 外交談判不是許願
血狸奴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陛下怎可如此意氣用事?”
“便是要開戰,也重要同我等商議一番?”
“至不濟,也得先請奏太皇太后······”
散朝之後,走在從宣室殿到司馬門之間的宮道之上,眾朝公面上無不是嚴峻之色,人群中還不時響起類似的私語聲。
但在這些私語聲中,只能聽到諸如‘陛下為何如此?’‘這該如何是好’之類的詢問,卻沒有哪怕一句話,不是在用疑問,亦或是質問的口吻。
不知過了多久,簇擁著走向宮門方向的眾人,才開始將目光撒向人群前方。
——這種時候,必須有人站出來。
安撫朝公眾人也好,折身回去勸諫也罷——這種時候,必須有人站出來做些什麼。
不出意外,最終站出來的,是朝公大臣當中,人緣最好的太僕袁盎······
“我倒是認為,諸公,大可不必如此擔憂。”
輕聲一語,將眾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便見袁盎悠悠然屢屢髯須,又故作神秘的沉吟片刻;
待眾人都有些焦急起來,方澹然一笑,滿是輕鬆地側過身,對身旁的劉舍、田叔等人稍一拱手。
再等這幾人拱手回禮,表示自己並不介意袁盎出這風頭,袁盎才正過身,悠悠發出一聲長嘆······
“我還記得,太宗孝文皇帝見年,朝中便有人建議太宗皇帝:吳王劉鼻反形已具,與其等他起兵再反制,倒不如先下手為強。”
“但太宗皇帝卻說:太子不慎失守,誤殺了吳王太子,便是吳王有些怨念,也實屬情有可原。”
“若其反,自是有悖人臣之道,當發兵以平之;”
“然若吳王未反,而長安先發兵,則恐天下人言:朝堂貪圖吳地,故先殺太子,後殺其王······”
如是道出一語,惹得眾人紛紛疑惑地皺起眉頭,卻見袁盎又是嘿然一笑,再側過頭,似笑非笑的望向劉舍。
“桃侯可記得當年,太宗皇帝說完這句話之後,所下達的第一道、第二道詔令是什麼?”
此言一出,眾人便又齊齊將目光移向劉舍,似乎是想要聽到什麼‘太宗秘幸’。
在眾人的目光注視下,劉舍思慮片刻,面上也終是湧上陣陣瞭然之色。
“若非太僕提及,倒是險些忘記了······”
···
“自太祖高皇帝立漢國祚,乃制:諸侯王三年一朝長安,非天子詔不得擅出封國。”
“除非另有詔諭,否則就必須嚴格最受‘三年一朝’的規矩,不到時間絕不可私朝,到了時間,也絕不可不朝。”
“——當年,吳王太子為當時的儲君,也就是先孝景皇帝失手誤殺,太宗皇帝聞之大怒,重懲了儲君;”
“之後又令人,將吳王太子的屍首送回吳地,以落葉歸根。”
“但在見到王太子的失守之後,劉鼻卻怨懟道:既然死在長安,那就葬在長安便是,何必抬回這荊吳荒蠻之地?”
“於是,王太子的屍首便又被送回了長安,太宗皇帝無奈之下,只得令奉常以諸侯禮厚葬王太子,並諡:吳恭太子······”
聽著劉舍提起這段往事,在場眾人也紛紛將目光收回,陷入一陣短暫的回憶之中。
雖說太宗孝文皇帝至今,已經隔了有幾十年,便是太宗孝文皇帝駕崩,也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但對於漢室權力金字塔的最頂部:長安朝堂來說,發生在太宗皇帝年間的事,也至今都還歷歷在目。
——在政壇、官場,十幾年,絕對算不上有多‘久遠’。
現如今,能躋身於朝堂,有資格參加朝議的朝臣,早在太宗孝文皇帝,乃至更早的呂太后年間,便已經開始嶄露頭角了。
便說如今的太僕袁盎,早在呂太后掌政時期,就已經是上將軍呂祿的家臣;
雖然呂太后駕崩之後,呂氏外戚因一場‘諸呂之亂’而被連根拔起,但在呂太后駕崩、諸呂亂起、諸侯大臣共誅諸呂的過程中,袁盎卻並沒有受到牽連。
甚至非但沒有受到牽連,反而還在其兄袁會的舉薦下,被剛即天子位的太宗皇帝任為中郎。
至於太宗孝文皇帝劉恆在位的二十七年,漢家朝堂內外的大事小事,袁盎,更是全稱目睹,甚至屢屢參與其中。
袁盎是這樣一個情況,其他的人,也基本差不到哪裡去。
——衛尉直不疑,早在太宗皇帝之時,就已經做了宮中的郎官,並逐漸受到太宗皇帝的重視;
——郎中令周仁,也同樣是在太宗皇帝年間,就因為醫術高超而得寵,並被太宗皇帝派去,照顧當時的儲君:太子啟。
甚至就連如今,在三公九卿之列最年輕的廷尉趙禹,也早就在太宗皇帝末年,做了朝堂有司屬衙的左吏,並於孝景皇帝三年,因奉公廉潔而被任為令史,在當時的太尉周亞夫身邊做事。
所以,對於劉舍提起太宗皇帝年間的事,大多數人表露出的都是回憶、追憶之容,而非興致盎然。
太子啟一棋盤砸死吳王太子的往事,眾人自是有著極為深刻的印象。
不單是因為此事,在後來簡介引發了波及大半個天下的吳楚七國之亂,也同樣是因為這件事,真的很難讓人輕易遺忘。
——儲君太子下棋下的不高興了,一棋盤把對座的王太子當場打死!
這樣的事,無論發生在哪朝哪代,恐怕都會是震驚天下三五代人的奇觀。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因為這件事太過於離譜、太過於荒唐,也實在讓人難以忘卻,所以對於當年,發生在這件事前後的朝中大事,眾人也至今都還有這清晰地記憶。
——吳王太子劉賢身死,太宗皇帝勃然大怒,愣是親眼看著太子啟被按在宣室殿外,挨板子捱了足有小半個時辰!
怒火稍艾,太宗皇帝便滿懷著羞愧,寫下一封稍有些委婉,卻也足夠誠懇地道歉信,並派人帶著信,將王太子劉賢的棺槨送回吳地。
約莫半個月之後,吳地傳來劉鼻‘拒接接受王太子屍體’的訊息,又過了小半個月,劉賢的棺槨便被送回了長安。
被劉鼻這麼毫不遲疑地打了一巴掌,太宗皇帝自覺臉頰火辣辣的發燙;
又實在理虧,便只能厚葬劉賢,並將此事冷處理。
幾個月後,剛好到了劉鼻‘三年一朝長安’的時間,按照制度,劉鼻必須要到長安覲見,向天子表明自己的忠誠。
但劉鼻卻託病,向太宗皇帝請求‘等養好了病再去長安’,並且這一‘病’,就一直‘病’到了先孝景皇帝三年,吳楚七國之亂爆發的那一晚。
而袁盎方才所說的那件事,便發生在太宗皇帝第一次接到劉鼻‘託病不朝’的訊息時。
——劉鼻託病不朝,朝臣百官惶恐不安,建議太宗皇帝‘先下手為強’;
在明確表示自己絕不會主動出手之後,太宗孝文皇帝,便在當日下達了兩封詔諭。
第一封,是賜吳王劉鼻几杖,並以‘年老體弱’為由頭,特許其不必再遵守‘諸侯三年一朝長安’的規矩。
如果說這一封詔諭,是在已經確定劉鼻不會再朝長安的前提下,為長安朝堂保留了一絲顏面的話,那第二道詔諭,才能真正表明當時,太宗皇帝究竟做出了怎樣的判斷······
“王太子的屍體被送回長安,整個朝堂都遭受到了羞辱;”
“而太宗孝文皇帝,在恩允劉鼻不必再朝長安之後,所下達的第二封詔諭······”
“嘿······”
“當年,我還是少府。”
“這第二封詔諭,主要就是對我掌控下的少府下達。”
“——太宗孝文皇帝命令少府,即可開始準備應對南方溼瘴之地的武器、軍械,並大肆增加武庫的庫存。”
“也就是從那一道詔諭頒下開始,朝野內外便都心中瞭然:吳王必反,只期待定······”
以一種耐人尋味的語氣,道出這段已經逐漸湧上眾人心頭的往事,劉舍便也含著微笑,對袁盎微一頷首,算是將話頭遞還給了袁盎。
接過話頭,袁盎則又是一聲輕嘆,只面上自信之色更甚一分。
“當年,太宗皇帝嘴上說的,明明是‘絕不對吳王妄加揣測’,但實際上,卻在第一時間開始為戰爭——為吳王劉鼻起兵謀反做準備。”
“這是因為太宗皇帝知道:有些事,既然避免不來,那就一定要面對;”
“既然要面對,那麼,就要早做打算······”
···
“再說當年,吳王劉鼻舉兵,一路攻城略地,兵峰直指函谷。”
“朝堂內外驚慌失措,頓時有不知多少人入宮,勸諫先帝‘斬晁錯以安天下’。”
“咳咳······”
“當時,我也曾這樣勸過先帝,並一度讓先帝採納了我的建議······”
“只是後來,當時的丞相:故安貞武侯,同當時的皇七子、皇九子一起趕到陛下送別晁錯的小院。”
“當時,皇九子曾對先帝這樣說。”
“——陛下對先帝說:戰爭,從爆發的那一刻開始,就必定是要分出勝負的。”
“而和談,不過是將某一方不願繼續遭受損失,而想要投降的意願,粉飾的好聽一些而已。”
“吳楚起兵作亂,盡失大義,悖君妄上,朝堂攜大義而平叛,這絕不是一場可以談和的戰爭。”
“若朝堂乞和,便會失大義;至於劉鼻,無論乞和與否,都必將死無葬身之地。”
“在那樣的情況下,如果朝堂因為恐懼,而按照劉鼻的心願殺死晁錯,那和乞和,甚至是祈降沒有任何區別。”
“陛下還說······”
“還說······”
說到最後,袁盎做出一副皺眉抿嘴,似是回憶不起什麼事的模樣,不是還‘嘶~’一聲;
見袁盎如此,劉舍便笑著再次接過話頭:“陛下還說:談判,不是許願。”
“戰場上無法得到的東西,也休想透過談判得到。”
“對方沒有在戰場上獲得的東西,如果透過談判得到,那就是我方最大的失敗······”
聽到這裡,眾人才長‘哦~’了一聲,散去面上狐疑,各自低頭思索起來。
袁盎的意思,大家夥兒算是聽明白了。
——戰場上無法得到的東西,也休想在談判桌上得到!
這,便是少年天子的性格,以及對敵人的態度。
這意味著從今往後,就算遭受再大的損失,這位少年天子,也絕不會再對匈奴人低頭。
如果放在過去,劉勝如此剛硬,眾人未必不會派個代表,去勸劉勝‘至剛易折’之類的話,讓劉勝忍辱負重,以待將來。
但現在,眾人卻不會再這麼做了。
一來,是今時不同往日:那場決戰,漢室已經基本做好了準備;
就算沒有完全做好準備,也已經接近完成準備工作,劉勝對匈奴人的態度逐漸強硬,也算是題中應有之理。
二來,則是因為如今,或者說至少這一次,漢家已經沒有必要再向匈奴人求和,乃至是和親的必要了。
——和親,是為了讓匈奴人被陪嫁餵飽,然後讓邊地安生幾年,漢家好發育發育,過幾年安生日子;
可今年,匈奴人已經打來了。
非但打來了,還差點將戰火燒到關中,邊關四郡更是損失慘重,人口驟降!
邊地已經遭受了匈奴人的荼毒,漢家又何必再去和匈奴人和親?
至於方才殿中,呼延屠明裡暗裡的言語恐嚇······
“如此說來,陛下是打定主意,不再同匈奴人和親了啊······”
“不和親,那即便還沒到決戰的時候,小打小鬧,也只怕是再也免不了的······”
“往後幾年,漢邊,恐難得安吶······”
意識到這一點,眾人面上疑色盡去,雖仍帶著些許嚴峻,但更多的,卻是難以按捺的季動,以及即將見證的興奮。
——終於。
經過長達數十年的忍氣吞聲,漢家,終於熬到了這一天。
終於熬到了報仇雪恨,同匈奴人算算總賬的這一天。
而這一天,不單是在場眾人:整個漢室,數以千萬計的漢人,都等了太多太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