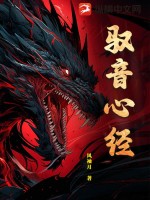第383章 宿命
血狸奴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被最後通牒了,繼續防盜書就要無,原本想按順序把之前兩張正文弄出來,但最後通牒的原話是‘再有一次,打入死牢’。無奈之下,只能先發今天的正文,昨天前天的防盜內容連夜改回來······
從今往後都沒有防盜了,大家可以放心看了。
·
“怎二位初次面會,便似是‘相識多年’?”
未央宮,宣室殿。
看著殿內,明明從未曾見過面的顏異、張湯二人,卻極為默契,也頗有些莫名其妙的拉下臉去,劉勝只感到一陣驚奇。
對於劉勝半帶善意,半帶看熱鬧不嫌事大的提醒,相對而立於殿中央的二人,也只是意味深長的再最後看了對方一眼,便將身子重新對向上首的御榻,對劉勝所在的方向稍一躬身。
也就是在劉勝面上神情愈發怪異的同時,在朝臣班列,太僕袁盎的神容,也不免有些尷尬起來。
這樣的場景,旁人或許會感到陌生,甚至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但對於袁盎而言,眼前這幅場景,卻喚醒了一段塵封多年的古老回憶。
——太宗孝文皇帝前元元年,長安朝堂按照過去每一次(太祖劉邦、孝惠劉盈)新君即位時的慣例,向天下地方郡縣下達了舉薦指標。
所謂指標,自然是‘必須舉薦一定數量’的死命令。
在那之前,長安朝堂一來長期沉寂於呂氏外戚,以及呂太后的淫威之下,人人都恐不能自保,自也就顧不上去舉薦青年才俊,以節外生枝。
二來,舉薦這個東西的風險,也著實有些太大,相應的收穫,卻又實在少的可憐。
——舉薦的人犯了罪,舉主雖不至於連坐,但若有仇家想安上一個‘居心叵測’的罪名,那也是一點難度都沒有。
就算沒有仇家,那也終逃不掉一個‘識人不明’的道德譴責。
或許在後世人看來,道德譴責的意義,大致就是‘只要我沒有道德,就沒有人能道德綁架我’的程度。
但在這個時代,道德,或者說名聲,卻是上到劉漢天子,下到黔首黎庶最基礎的立身之本。
天子自不用說,但凡沾上‘失德’二字的邊兒,就必定離‘失天下人心’不遠;
高官德行有缺,也大機率在仕途舉步維艱——每逢職務出缺,便總會有競爭對手提上一句:如此道德敗壞的人,都能做xx,我又為什麼不能做?
再到下面的豪強、富戶,名聲不好,也基本吸引不到足夠多的佃戶——農民,是一個極為複雜的群體,他們即愚鈍,同時又兼具精明。
在他們被壓榨出最後一點剩餘價值之前,他們往往都會默不作聲,以免‘槍打出頭鳥’。
但在他們下定決心,要拋棄那個不地道的地主老財時,那也就沒有什麼能阻擋他們。
——在某些極端情況下,他們甚至敢拋棄這天下最大的地主老財:皇帝老子!
甚至就連這些農戶黔首本身,也同樣十分注重自己的德行、名聲,生怕被鄉鄰戳嵴梁骨。
在後世,戳嵴梁骨是比喻、是抽象的形容詞;
但在這個世代,戳嵴梁骨,那可是真到不能再真的動詞······
所以,不單是官員、皇帝這樣的掌權者,這個時代幾乎每一個人,都視自己的道德、名聲為至高追求。
有些人發現自己被人傳‘德行有缺’,便會為了自證清白,而毫不遲疑的放棄生命!
有些人聽說自己名聲開始臭了,便會慌忙澹退大眾視野,生怕晚一步,就要被什麼東西咬到。
在這樣的前提下,讓那些已經享受著高官厚祿,只要別犯下原則性大錯,便可以在二千石的位置上終老的高官,去舉薦和自己八竿子打不著干係的毛頭小子,實在算不上是明智的選擇。
——不舉薦,大不了被朝堂批評‘舉士不利’,只要回一句‘確實沒啥拿得出手的人’,便也就搪塞過去了。
可一旦舉薦,那舉薦者和被舉薦者的命運,便會被徹底綁在一起。
舉薦者失勢,受舉薦者也不大可能再有建樹;
受舉薦者犯了錯,舉薦者也同樣要吃掛落,甚至是‘失德’。
很顯然:相比起百十來石不等的受舉薦者,那些原本可以安詳兩千石高官生活的地方郡守們,才是這場交易中的責任承擔方。
至於收穫?
——受二千石舉薦的人,等他混到二千石,當初舉薦他的恩主,墳頭草都不知道長了多高!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漢家自太祖高皇帝立漢國祚以來,便飽受‘國無可用之士’的困擾。
而在太宗孝文皇帝元年,那按照慣例進行的‘逼迫地方舉薦良才’的盛宴中,便曾一具出現兩個大才。
兩個隨便拎出哪一個,隨便丟到其他任何時代,都能在青史之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的國士。
——賈誼,和晁錯。
這二人,同生於太祖高皇帝七年(公元前200年),又同樣在二十歲的年紀,受人舉薦而入朝,得到太宗孝文皇帝的親自接見。
在那時,人們都認為:這兩個生於同一年,有著同樣的年齡,又同一時間入朝的青年才俊,將成為恩怨情仇綿延幾十年的死對頭。
但從不曾有人想到:成為對手的,並非是這兩個青年才俊,並非是北平侯張蒼的弟子賈誼,以及‘儒家’出身的晁錯。
在最開始,關東在狂歡。
——長安朝堂,一下就出了兩個儒家出身的潛力股!
甚至就連賈誼,都被當時的晁錯所騙過,並嘗試著同晁錯建立過私下的情誼。
只可惜······
“只可惜,袁絲閱人無數,成了整個長安朝堂,唯一一個沒有被晁錯騙過去的人。”
“嘶~”
“袁絲那話,怎麼說的來著?”
“哦哦······”
“——即便是披著一層儒皮,晁錯的身上,也依舊有掩蓋不了的法家酷吏的惡臭······”
“嘿······”
一時間,幾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朝臣班列的袁盎身上。
——最終和晁錯成為對手的,並不是最勢均力敵,也最該成為對手的賈誼;
而是‘聞’出晁錯真實身份的小蝦米:袁盎。
當年,也同樣是第一眼——第一次同時得到太宗孝文皇帝的接見時,之前從不曾見過彼此的袁盎、晁錯二人,便無緣無故的恨上了彼此。
如今雖滄海桑田,袁盎居廟堂之高,食九卿秩祿,晁錯居北地之遠,負戍邊之責,但這二人之間的爭鬥,卻也至今都還沒有畫上句號。
而今天,同樣的一幕,再出於宣室殿上演。
——同樣是一個儒家出身、一個法家出身兩個年輕人,只見了彼此一面,話都沒說上一句,便本能的恨上了彼此。
但沒有人知道:這二人之間的明爭暗鬥,對未來的長安朝堂、劉漢社稷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
“怎朕不開口,便沒人開口了?”
極其漫長的沉默之後,劉勝終還是主動打破了殿內,那好似被抽乾空氣般的壓抑氛圍;
而在劉勝開口之後,當今劉勝最忠實的狗腿子:丞相劉舍,便不假思索的站出身來。
“二位,都是陛下十分看重的才俊,將來未必不會有在陛下身邊共事的機會。”
“便借今日,彼此相熟相熟······”
“——這位,是由現任廷尉卿趙禹,於先孝景皇帝年間舉薦,並被太子安排去廷尉歷練的張湯張監令。”
“——這位,是今歲考舉金榜頭名,儒賢顏回第十世孫,陛下欽點之狀元郎:顏異顏生。”
有劉舍從中活躍氣氛,殿內的氛圍似是被驅散了些許;
先前被這兩個年輕人唬住的百官公卿,也終是在氛圍趨於緩和的同時回過身,調整好狀態,澹然的看向殿內的兩個年輕人。
有活力,是好事;
有競爭,更是好事。
尤其是在黃老學懶洋洋的把著政壇和學術界,讓‘不做不錯’成為一句流行於的當下,年輕官員願意競爭、願意做些什麼,總還是一件好事。
但對於這兩個年輕人,殿內百官公卿的心思,更多還是看熱鬧不怕事大。
——儒家和法家誒!
明爭暗鬥、互相攻訐數百年,至今都還‘不共戴天’的兩個學派各自最傑出的新生代,居然同時出現在了天子劉勝,以及滿朝公卿百官的面前。
那麼接下來,故事,會是怎樣的走向呢?
是像晁錯、袁盎那樣的又一對死敵?
還是······
其實,無論怎麼樣,這個八卦的含金量,都已經足以吸引這些個達官貴族的注意力。
畢竟在這個娛樂手段極度貴乏,人力資源季度短缺,朝堂工作壓力又這麼大的時代,有個樂子,可實在是太讓人感到舒心了······
“果然是孔丘那腐儒的徒子徒孫!”
“隔著大半個未央宮,我就已經在廷尉屬衙,聞到腐儒的酸臭了······”
對面雖是新科狀元,而且是華夏曆史上的第一位狀元郎,但張湯好歹也已經是比千石的廷尉左監令。
面對著必將從二百石起步的黃毛小子,自然是不能客氣一點,毫不遲疑的丟下一句蔑視,便自顧自昂起頭,對御榻方向拱起手。
正要彎下腰,像劉勝拱手行禮,卻聞耳邊,響起一聲絲毫聽不出怯懦的嘲諷。
“聽說法家的人,都自詡為商鞅、韓非的徒子徒孫。”
“卻不知就連那公子韓非,都曾說我儒家先賢:卜商子夏,才是真正的法家之祖。”
“——法家的人,學著先賢子夏的學問,反自詡延衛豪族商鞅、韓公子韓非的師承,對祖師子夏的老師仲尼,卻只蠻橫無理的稱呼一聲‘孔丘’?”
“哼!”
···
“我聽說,兒孫敬重父祖,是因為再造之恩。”
“孫兒敬重祖父,是為了感恩祖父生養了父親,才讓父親有了生養自己的機會。”
“我從來沒有聽說誰家的孫兒,是一邊敬重自己的父親,一邊又不孝於自己的祖父的。”
“——現在,法家始祖卜商子夏,卻被自詡為法家之士的人貶為‘竊學小人’,子夏的老師仲尼,更被法家屢屢中傷為腐儒。”
“這在我看來,就像是一個什麼都不懂得孩子,一邊說自己的先祖是惡賊,一邊還說先祖的父親,是比惡賊還要可惡的窮寇······”
···
“這樣的話,如果是出自我儒家士子之口,是絕對不可以想象的。”
“但法家歷來以嚴酷律法殘民、欺民,對於人倫綱常置若罔聞。”
“能說出這樣的話、做出這樣的事,倒也確實沒什麼奇怪的——這很符合法家的做派。”
“倒是不曾想:我從遙遠的濟南趕來,卻能在這皇宮未央之中,也見到無君無父的法家酷吏······”
好傢伙!
顏異機關槍般一陣突突,朝中公卿百官,只各自直呼好傢伙!
——牛!
——不愧是名門之後,復聖顏回的嫡系後人!
且不論說的有沒有道理,但就是這份從容地氣質、站出身的勇氣,以及言辭的犀利,都足以讓殿內百官,對這個看上去有些文弱的狀元郎刮目相看。
甚至就連御榻之上的劉勝,都將目光中,那本能帶著的一絲鄙夷——對儒家的鄙夷收回去些許。
對儒家,劉勝的態度雖不比太祖劉邦那麼惡劣,但也絕對好不到祖父劉恆的程度。
非要討論,那也就是‘你是儒生,但你很有能力,所以朕可以假裝不知道你是儒生’的程度。
再進一步,那就是在強迫劉勝了。
而今天,看到自己親自選定的狀元郎,在尚還未得到官、爵,尚還是白身的前提下,正面回懟許多年前便進了劉勝的考察名單,甚至堪稱‘簡在帝心’的張湯時,劉勝對顏異,甚至連帶著對儒家的感官,都下意識了好轉了不少。
這當然不是說劉勝立場不堅定,能被一個顏異,就改變對儒家的惡劣看法。
只是有那麼一瞬間,看著張湯和顏異針鋒相對故,劉勝恍忽之間,似乎又聽到了老頭子曾在耳邊,所提起過得那番話。
“為君者,首重製衡。”
“一人得道,則必有一敵,可與之分庭抗禮。”
“一人得勢,有敵,則朝堂小亂,天下大安;”
“一人得勢,滿朝故舊當於,則朝堂小安,又必天下大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