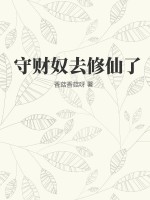第365章 又一個魏尚?
血狸奴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在等候周亞夫的空檔,劉勝也不由暗自思慮起來。
對於晁錯,劉勝的個人情感,其實是非常複雜的。
單從上位者、為君者的角度來看,晁錯這個人的才能,其實非常出眾。
——要知道當初,也就是太宗孝文皇帝自代地入繼大統之時,晁錯可是和同樣年紀的賈誼賈長沙齊名的人物!
雖然在後世人看來,晁錯二字,遠沒有賈誼二字具有辨識度,但至少在太宗皇帝年間,或者說是從二人最後的結局來看,晁錯無疑是那個更快適應廟堂的一人。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便說晁錯在和賈誼的競爭、較量中大獲全勝——至少是在當年那個時代取得了更大成就,也是完全挑不出毛病的。
畢竟賈誼賈長沙名頭再大,在太宗皇帝年間,也不過是個鬱郁不得志,最終又抑鬱而終的諸侯王太傅;
而晁錯則是先為《尚書》博士,之後又歷任太子家令、少傅,之後更是在先孝景皇帝繼位之後先後履任內史、御史大夫。
若非武勳方面的短板實在過於明顯,爵位也是在低的有些離譜,早在先帝之時,晁錯就本該過上一把丞相的癮。
也就是說:拋開沒有軍功、不是徹侯這一點不論,單就才能而言,晁錯是具備成為丞相的能力的。
晁錯之所以主動請求外放邊關,也恰恰是為了補足這最後一塊短板,為自己的丞相之路掃平最後一塊障礙,以名正言順的頂著徹侯之爵,坐上自己夢寐以求的丞相寶座。
但當年那件事,卻至今都讓劉勝耿耿於懷,於‘棄用並殺死’和‘原諒並重用’之間糾結至今,都始終無法做出最終決定······
“太廟啊······”
“開了這個先例,往後我劉氏的宗廟,那可就別想有安寧······”
“唉······”
“晁錯啊晁錯······”
御榻之上,劉勝一陣唉聲嘆氣,似是憤恨,又更似恨其不爭;
而在殿內,眾人卻依舊回味著方才,劉勝反覆強調的那句:朕,很冷靜······
“陛下,是想告訴我們什麼?”
“亦或是先前,太后同陛下說了什麼······”
弄不明白劉勝心中所想,也不明白劉勝想要表達的意圖,眾人思慮再三,終也只得將此事暫時放在一邊。
不多時,周亞夫應詔入宮,與劉勝相互見過禮,便也直入正題。
“稟陛下。”
“依臣之見,匈奴人此番南下,一反往年,南下多於秋後之常態,而於開春之時。”
“從這個角度來看,雁門、北地、上、代四郡的守將縱有禦敵不力、戒備不嚴之嫌,卻也還情有可原。”
“——畢竟沒有人能預料到匈奴人,會在開春之時入侵北牆,而且是集結如此重兵南下。”
“真要說責任,恐怕陛下首先應該追求長安侯,沒能按時將訊息送回長安的罪責。”
“自有漢以來,長安侯一脈便世受皇恩,就算無法送回‘匈奴大舉南下’的訊息,也至少應該送回去年冬天,匈奴人遭遇了天災或兵禍的訊息。”
“如果有訊息送回,邊關必定會加強戒備,最終的戰況,也必定會比現在好上太多······”
開口第一句話,周亞夫便將一大半的責任,毫不遲疑的甩給了遠在匈奴草原幕南的長安侯,或者說是東胡王盧他之。
但對周亞夫推卸責任,而且是替自己的得意門生推卸責任的舉動,劉勝卻也並沒有做出什麼反應。
周亞夫說的有道理。
至少有一半道理。
——匈奴東胡王、漢長安侯盧他之有沒有責任,這當然是有的;
但也僅僅只是理論上的責任而已。
實際上,無論是長安中央還是匈奴單于庭,其實都很清楚老盧家腳踏兩條船,雙面間諜玩兒的飛起;
這次的事,頂了天去,漢家也頂多只能警告一下盧他之,除此之外,也並不會有其他過繼的舉動,例如‘不再聯絡老盧家’之類。
畢竟老盧家,是漢室瞭解匈奴內部事務的唯一渠道,往後,能用到老盧家的地方還多著呢。
這也就是為什麼周亞夫的話,只有‘一般道理’的原因。
——盧他之有沒有責任,還真不大好說;
但遭遇入侵的北地四郡守將責任不大,卻是確如周亞夫所言:有疏於戒備的責任,但也實屬情有可原。
畢竟誰能想到匈奴人,會前所未有的在開春之時發起進攻呢?
要知道自有漢以來,漢匈雙方之間的每一次大戰,都無一例外是在秋後!
與此同時,匈奴零散遊騎南下打草谷、搶東西,也有九成以上是在秋後;
即便是剩下一成,也極為均勻的分佈在夏、秋二季,極少有發生於開春之時。
所以,對於周亞夫如此刻意的為北地四郡的守將逃脫責任,劉勝並不感到不滿,甚至是比較認可週亞夫的結論。
對於劉勝的反應,周亞夫顯然也並不意外。
——畢竟先前,也在太子宮‘共事’了幾年時間,對於劉勝的脾性,周亞夫也算是比較瞭解。
確定劉勝能接受自己的說法,周亞夫稍沉吟片刻,便繼續說了下去。
“再說這禦敵不力的責任。”
“匈奴人此番南下,遭受匈奴兵峰荼毒的北地四郡當中,作為直接和草原接壤的邊郡,北地、雁門二郡首當其中。”
“——作為邊郡,尤其還是和草原接壤的邊郡,這二郡本該全年枕戈以待,以備賊子侵擾。”
“所以此戰,北地郡守晁錯、雁門郡守郅都過失更大,上、代二郡的過失則稍小。”
“其一者:上、代並不與邊牆毗鄰,也並不與草原接壤,雖然位處北方,但防備相對鬆懈也並沒有什麼不對。”
“其二:上、代所遭遇的兵禍,其實大都是因為雁門郡被匈奴右賢王部所‘攻陷’,導致上、代二郡失去了屏障,從二線變成了前線。”
···
“如此說來,此戰犯下最大過錯的,便該是雁門郡守郅都。”
“因為郅都要承擔的,是雁門、上、代三郡為匈奴所馳掠的責任;”
“而晁錯,則只需要承擔北地被戰火荼毒的責任。”
“至於上、代二郡,需要承擔的責任幾近於無······”
聽聞周亞夫這番言論,殿內眾公卿只眉頭齊齊一皺;
便是御榻上的劉勝,面上也頓生狐疑之色。
——周亞夫,真就這麼耿直?
自己的得意門生郅都,就這麼毫不遲疑的腿上‘此次戰敗第一責任人’的位置?
還是說,在劉勝不知情的情況下,周亞夫和郅都之間,生出過不愉?
短暫的疑惑之後,眾公卿便次序露出瞭然之色,引得劉勝又是一齊;
暗下稍一思慮,總算明白周亞夫想要表達的意圖,劉勝終是怪笑著搖搖頭,旋即陷入短暫的思慮之中。
按照周亞夫的說法,匈奴人此番南下,對北地、雁門、上、代四郡造成的巨大破壞,這四個郡的守將都需要承擔戰敗責任。
但責任的大小,按照這四位守將犯下的過錯依次排序,分別是:首犯雁門守郅都,次犯北地守晁錯,最後,才是上、代兩郡的守將。
乍一看,周亞夫似乎真的是‘大公無私’,將自己的得意門生推上的‘戰敗第一責任人’的風口浪尖。
但稍一想就不難發現:周亞夫這是在拐彎抹角的保晁錯。
——按照周亞夫的這套說辭,此次戰敗的第一責任人,是雁門郡守郅都。
可郅都在此戰中做出的決策,卻並沒有什麼原則性的錯誤。
被右賢王部偷襲,雁門郡第一時間阻止起防線;
發現為時已晚,野外的控制權已經無法奪回,郅都又毅然決然放棄城池外的一切區域,下令雁門各地緊閉城門,依城而守。
雖然此舉造成了雁門郡不再具備阻攔匈奴人的能力,使得雁門以南的上、代兩郡遭災,但同樣下令軍隊、百姓撤回城池內,並緊閉城門的上、代兩郡,也勉強將損失控制在了最小的限度。
說得再直白一點:當時的郅都,壓根就沒有其他選擇;
除了放棄野外,下令全郡縮回城池自保,郅都別說是更好的選擇了,連差不多的第二個選擇都沒有!
所以,即便從結果來看,這次北地四郡遭受荼毒,雁門郡守郅都要負首要責任,長安中央也很難因郅都‘下達錯誤戰略決策’而治罪。
頂天了去,也就是一個防備不嚴,導致匈奴人偷襲得手的罪責。
而問題的關鍵,也恰恰就在這裡了。
——作為此次戰敗的第一責任人,郅都尚且還只是個‘戒備不嚴’的罪責;
那作為次要責任人的晁錯,又能以什麼罪名懲處?
頂破天去,也就是同樣一句‘戒備不嚴’,然後以‘郅都戒備不嚴導致三個郡遭災,晁錯戒備不嚴導致一個郡遭災’,而位列次要責任人的位置。
如果是按照這個規格來劃定責任,那晁錯最後遭受的處罰,至多也就是一個罰俸,外加一句‘許其戴罪立功’······
“倒是不知條侯,同晁錯也有些私誼?”
思慮片刻,似是調侃的道出一語,卻見周亞夫滿面嚴肅的搖搖頭。
“臣同晁錯,並無私誼。”
“只事實如此。”
“——此戰之罪,實非晁錯之故,亦非郅都無能。”
“實在是吾漢家之步卒,在匈奴騎兵佔據野外的情況下,幾乎不可能在同等兵力下奪回野外。”
“換而言之:此戰之罪,罪在我漢家無騎······”
見周亞夫又道出一聲,還不忘再次強調此次戰敗,並非北地四郡守將的過錯所導致,劉勝也不由面色稍一肅。
“條侯的意思,朕當然明白。”
“但還請條侯不要忘記:匈奴賊蠻此番南下,被戰火所荼毒的,並不單隻有北地四郡。”
“——戰火,燒到了關中。”
“——甚至燒到了甘泉宮、燒到了距離長安不過數百里的地方!”
“要知道自有漢以來,無論是諸侯反叛,還是匈奴入侵,戰火都從不曾波及關內!”
···
“而這場戰火之所以會波及關中,正是因為北地近乎不設防,匈奴人自草原出發,一路直撲蕭關,幾乎沒有遇到任何阻礙。”
“短短六天,匈奴人就從河南地,把先鋒送到了甘泉山——送到了朕的眼皮底下。”
“說的誇張下,便說匈奴人的胡刀,架在了朕、架在了太皇太后的脖子上,也絲毫不為過。”
“在這樣的前提下,條侯,難道還要說晁錯無罪嗎?”
陰惻惻發出一問,劉勝的目光便死死鎖定在了周亞夫身上,好似是要將周亞夫整個人看穿。
而在劉勝這明顯有些警告意味的話語之後,周亞夫,也終還是道出了那先前,始終不曾有人膽敢說出的事實。
“大約四年前,先孝景皇帝頒佈詔諭,改地方郡守為太守,改郡尉為都尉;”
“而在改制之後,被改成都尉的郡尉,從先前掌一郡軍事兵馬的官職,變成了單純領一部都尉的武職。”
“那陛下知道:一部都尉,有多少兵馬嗎?”
“——五千人。”
“五人為一伍、二伍為一什,五什為一屯,二屯為一曲;”
“五曲為一隊,二隊為一校,五校便為一部,也就是一部都尉,亦或是‘一軍’。”
“也就是說:自陛下改制,將郡守改為太守、將郡尉改成都尉之後,天下各地的郡國兵,都統一改成了每個郡個一部都尉,總計五千兵馬。”
“即便是邊關,也同樣如此······”
如是說著,周亞夫不由又是一陣哀嘆,方繼續道:“陛下知道北地郡的五千人,如今剩下多少人嗎?”
“——一個不剩。”
“匈奴單于攣鞮軍臣親率主力近十萬,於夜半十分突襲朝那塞,駐守於朝那塞得北地都尉部五千將士為了拖延匈奴人,死戰至最後一兵一卒!”
“而在兩週一夜的浴血奮戰之後,北地都尉全軍覆沒,整個北地郡,便再也沒有了哪怕一個領著朝廷糧餉的正卒······”
···
“有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難道勐將,就可以打無兵可用的仗嗎?”
“可即便是沒有兵馬,晁錯也還是徵集起了近萬青壯,奮力作戰,將匈奴人的腳步稍放緩了些。”
“非要說晁錯有哪裡做的不夠完美,那也就是沒有和北地都尉孫戊那樣,馬革裹屍,為國捐軀······”
“能在北都都尉全軍覆沒,無一生還的情況下,仍舊靠青壯阻止起防線——上一個做到這種事的人,是雲中守魏尚。”
“如今,我漢家難道不是出了又一個魏尚嗎?”
···
“當年,魏尚的威名遍播草原,匈奴人甚至為魏尚捏了泥像,以早晚祭拜。”
“陛下卻想要讓臣等,討論應該如何懲處晁錯?”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臣只能說:陛下,還真不愧是太宗孝文皇帝的子孫。”
“只是如今,晁錯蒙受此等冤屈,曾為魏尚開脫的馮唐,卻已經不在長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