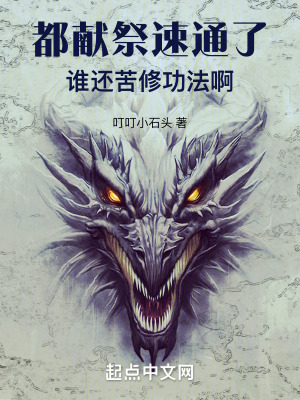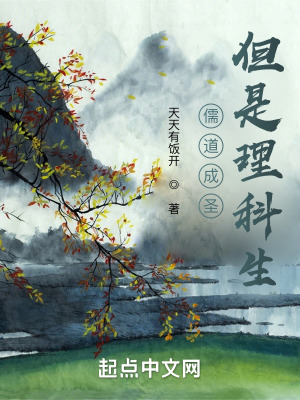第385章 那就打!
血狸奴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不到一萬匹戰馬。
每一個曾居於廟堂之高,並對軍隊,尤其是騎兵部隊建設有些許瞭解的漢臣,都不會不明白這意味著什麼。
就拿匈奴人的戰鬥編制:萬騎舉例,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匈奴人的‘萬騎’編制,都不會達到滿編,即一萬名騎兵。
按照匈奴內部的地位排序,最高規格的部隊,是直屬單于庭的匈奴本部。
而單于庭本部的‘萬騎’,往往才有資格維持萬名以上騎兵的滿編編制。
再往下,便是左、右賢王,以及左、右谷蠡王四位攣鞮氏宗種組成的‘四柱’,可以各自擁有一到三個各以八千騎兵為滿編的‘萬騎’。
再下,則是那些原本不屬於匈奴,因戰爭而被征服、納入匈奴的部族,如樓煩、折蘭、白羊等,可以擁有兩個以內,每個滿編六千人的標準萬騎。
最差的,則是那些即不屬於匈奴,也不願意被匈奴征服,戰敗之後也不願投降的奴隸部族,會被整編為‘別部’,也就是雜牌軍。
這些奴隸雜牌軍的萬騎,則是以四千滿編。
瞭解過匈奴人最基本的騎兵部隊編制:萬騎,以及‘萬騎’編制在不同情況下的人數,接下來,便是這幾種‘萬騎’的基礎配備。
——單于庭本部萬騎,作為匈奴單于庭最核心的力量,甚至是攣鞮氏鎮壓、統治草原的依憑,自是一切都以最高規格。
滿編一萬人的萬騎,光是常年跟隨單于大帳,於草原南北巡遊的,便足有六個!
這六萬人,無一例外,盡是以青銅兵器傍身,人均配備三匹馬,常年只需要維持戰鬥狀態,同時又享受著貴族生活的本部勇士。
至於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等具備單于大位繼承權的宗種,雖然每個萬騎都只有八千人的編制,但也都能保證一騎三馬,以及三兩個人裡,湊出一件產自秦少府的青銅武器。
再到每六千人為一個萬騎的普通部族,或許湊不出多少青銅武器,除了頭人,更是很少有人能身著甲具,但一騎三馬,也還是最基礎最基礎的配備。
而最差的奴隸別部,每個萬騎四千人的編制,也至少能保證一騎雙馬,也就是每個萬騎配備八千匹戰馬的配製。
瞭解過這些,再看方才,袁盎所說的那句‘至多也只能湊出不到一萬匹馬’,就能知道如今漢室的騎兵部隊建設,究竟處於怎樣的階段了。
假設:今年秋後,漢匈雙方之間爆發一場中規模以內的戰役,那匈奴一方的軍隊組成,大概會是右賢王、右谷蠡王各兩個萬騎,總計三萬兩千人;
樓煩、白羊、折蘭等漢室的‘老熟人’各兩個萬騎,共計三萬六千人;
再加幾個幕南部族各出一個萬騎,另外帶上三五個努力別部,匈奴一方的兵力,便會達到十萬左右。
反觀漢室這不到一萬匹馬,單就戰馬數量而言,很可能只能對標匈奴人的某一個奴隸別部——四千人,八千匹馬。
更何況這樣一場中規模戰役,漢室不可能將所有人騎兵力量,整編成一支只有四千人的純騎兵部隊。
匈奴人兵力達到十萬,漢室一方再怎麼說,也得有同等數量的兵力吧?
同樣是十萬人,按照漢室的軍隊編制,便是至少四路獨立的‘軍’。
而在戰時,無論是這四路軍隊彼此之間的資訊共享,還是這四路軍隊內部的指令下達,乃至戰場上的開胃菜:斥候戰,都需要漢室為精銳斥候部隊,配備足夠數量、足夠質量的戰馬。
所以說到底:就如今漢室這點戰馬,能給斥候部隊配齊戰馬,並留下一部分,作為各戰鬥部隊彼此之間溝通的通訊設施,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至於戰場上的正面對抗,也還是和過往數十年一樣:匈奴人以近乎全騎兵,對陣近乎全步兵的漢室軍隊。
而這,也正是此刻,被劉舍聚集在相府的公卿高官,默契的流露出憂慮之色的原因······
“自太祖高皇帝,與攣鞮冒頓會獵平城,又不甚身陷白登之圍,戰車,便已不再為我漢家所重。”
“之後的數十年時間裡,匈奴人連年入邊,我漢邊戍卒以戈矛、材官巨盾、弓弩相抗,終也勝少敗多。”
“時至今日,太宗孝文皇帝、先孝景皇帝兩代先帝勵精圖治足三十餘年,我漢家之兵,仍難得一部都尉盡為銳騎。”
“陛下又性烈如火,已決心不再與匈奴和親······”
“唉······”
“也不知經此一役,我漢家兒郎、關中良家子,又能得幾人安然而歸?”
如是說著,田叔便苦嘆著搖搖頭,一邊皺眉思慮著戰事,一邊輕輕捶打起酸澀的大腿。
而在堂內,大部分當朝公卿,也都各自頂著暗暗發青的眼圈,為接下來的事而發起了愁。
——自太祖高皇帝立漢國祚,尤其是在平城一戰之後,兵種剋制,就是重視漢室面對匈奴人時,最感到無力的一大戰略劣勢。
這就像是後世網遊裡的肉湯,面對敵方高機動射手的感覺一樣:這壓根兒就是一個彪形大漢,用手掌按住小孩子的前額,然後嘿笑著看小孩不斷揮舞雙拳,卻怎麼都碰不到面前的敵人。
這種無力感,激發了漢家歷代先皇省吃儉用,就算自己吃差一點,也要多養幾匹馬、儘早完成騎兵部隊建設的決心;
自然,也催生出了‘為騎兵部隊建設爭取時間,遂以和親暫時穩住匈奴人’的屈辱對外政策。
時至今日,漢室的騎兵部隊建設還遠沒有完成,為穩住匈奴人而出現的和親政策,也被當今劉勝決然停止。
那麼接下來要發生的事,自然是一目瞭然,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陛下不再行和親,那戰爭,就一定會到來。”
“——就算不是今年秋後,也會是明年、後年的秋後。”
“反正不管何時,都早晚會到來。”
“至於以步對騎的劣勢,我們這些在行伍之間沒什麼建樹的人都知道,由先帝手把手教出來的陛下,自更不可能不知道。”
“或許陛下,也有著自己的考量吧······”
···
“這些事,不是我們需要關心的,也不是我們關心了,就能得到解決的。”
“大戰在即,我等世受漢恩、世食漢祿,就應當為陛下排憂解難。”
“至於軍隊的事,自有將軍們同陛下商議······”
沉默中,劉舍滿含鄭重的一語,只引得在場眾人各自點下頭。
劉舍說的沒錯。
事情已經到了如今這個地步,單純的發愁,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
與其去想那些不可能完成——至少是短時間內無法完成的事,倒不如想想在現有的條件下,如何才能做到最好。
尤其是在這樣一場雖還未爆發,但基本已經確定會發生的戰爭之前,作為漢家權力中樞的長安朝堂,應該做出哪些努力,好在戰爭爆發之前,為漢家贏得更多籌碼。
劉舍看向賈貴,賈貴沉沉一點頭——少府沒問題。
自太宗孝文皇帝至今,三十多年來積攢下來的錢、糧等後勤物資及武器軍械,能輕而易舉的支撐起一場中規模以內的戰役。
劉舍再看向田叔,田叔也微微點下頭——內史沒問題。
關中百姓今年並沒有被頻繁徵勞,大部分人都將精力放在了照顧自家田畝之上。
在戰爭爆發之後,內史可以第一時間發出徵調令,徵發關中百姓以民夫、軍卒等身份,成為這場戰爭的重要參與力量。
最後看向袁盎,只稍一對視,劉舍便悠悠發出一聲長嘆,卻也沒有再多說什麼。
“近幾日,少府、內史、太僕,各自去向陛下和太皇太后請奏,並言明今日之事。”
“得到陛下和太皇太后的許可之後,便各自做好準備吧。”
“——少府準備好調配軍糧,以及鹽、肉、醋布等物什,並儘量再早一些弓羽箭失。”
“雖然武庫、內帑都有不少箭失,但大戰在即,箭失無論如何都是不嫌多的。”
“——內史同關中地方郡縣通個氣,讓各地做好徵勞的準備,一俟詔書發出,必須儘快組織起運糧隊伍,向邊關輸糧。”
“按照陛下的性格,甚至很可能不等大戰爆發,運糧隊伍就要提前出發······”
“至於太僕,也同陛下、太皇太后說明狀況吧。”
“剩下的,就看陛下和將軍們如何商量,太皇太后又是什麼決斷。”
作為丞相,劉舍未必傑出,但也絕對是合格的。
至少在眼下,劉舍知道自己這個丞相能做什麼、該做什麼。
對與戰爭關聯最大的太僕、內史、少府做下之令,又交代其他有司屬衙各司其職,儘量不要在未來這半年給朝堂添亂,劉舍便站起身,送走了被自己招來相府的朝中同僚。
而在同一時間,也確不出劉舍所料:在未央宮宣室殿,天子勝正眉頭緊鎖,雙手揹負於身後,昂起頭,檢視著面前那面被掛起的巨大堪輿。
在劉勝身側,則是周亞夫同樣愁容滿面的神情,以及不時響起的碎碎念······
“這場仗,真的不是時候。”
“尤其陛下新君繼立,且還未加冠、親政,不再和親,也是陛下親自做出的決定。”
“萬一戰果不理想,只怕明年開春,陛下加冠親政的事,也會出現一些意料之外的變數······”
周亞夫的視角比較高,或者說是比較宏觀、全面。
在根據劉勝的要求,指出這場戰爭可能爆發的時間、地點,以及匈奴人可能投入的力量之後,周亞夫很快便指出這場戰爭可能對漢家造成的影響,恐怕並不侷限於戰爭本身。
如果這場仗是去年爆發,那就是先帝屍骨未寒,劉勝父喪未罷,漢軍將士懷著哀痛、悲壯踏上戰場。
無論戰果如何,天下人都只會同情劉勝——小小年紀沒了爹,又扛起了天下的重擔,結果孝喪還沒脫下身,匈奴人就打過來了······
若是明年爆發,也還勉強可以接受。
屆時,劉勝將完成加冠、大婚、親政等一系列掌政流程,將真正成為君臨天下的漢天子。
在那時爆發戰爭,天下人會感到憤慨——陛下未冠喪父,好不容易加冠親政,結果都還沒在皇位上坐熱,這幫強盜就來欺負少弱之君!
可偏偏這場戰爭,即將爆發於今年。
——先帝駕崩的哀痛逐漸從天下人心中澹退,劉勝加冠親政在即,卻又還沒正式親政的隘口。
從積極的角度來看,這場戰爭的爆發,或許能為劉勝贏得一部分同情。
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大機率不會太好的戰果,將讓劉勝蒙受‘沒親政就做出如此孟浪的決斷,直接導致戰爭的失敗’的指責。
而後,自然就會衍生出類似‘還沒親政都鬧出這樣的事了,親政那還了得?要不還是再等兩年,等穩重一點再說吧’之類的輿論。
而這樣的輿論一旦坐實,劉勝加冠親政的那一天,恐怕就要取決於竇太皇太后的心情了······
“這些事,不必再多言,多說也無益。”
“條侯還是說說這場仗,我漢家究竟應該如何籌謀佈局,才能立於不敗之地吧。”
將話題拉回戰爭本身,不動聲色的道出一語,劉勝便稍有些尷尬的輕咳了兩聲。
立於不敗之地,聽上去,似乎是在說‘怎麼都不會輸’;
但無論是說出這句話的劉勝,還是聽到這句話的周亞夫,其實心裡都明白:劉勝真正想要表達的意思,其實是‘不輸就行’。
意識到這一點,周亞夫也只得稍撥出一口濁氣;
從新昂起頭,望向面前那張巨大的堪輿,思慮良久,才終於側身望向劉勝。
“臣斗膽推斷:匈奴人不來則已,來必叩關武州。”
“參戰的,應該會是右賢王為首的老熟人們,兵力至少在六萬到八萬。”
“而在這場戰爭當中,我漢家唯一的優勢,便是知敵必來,也知道他們大致什麼時候來。”
“我們可以提前佈局,匈奴人也會篤定我們會有所準備。”
“所以,我們或許可以利用匈奴人的這個想法,出其不意,打殘甚至殲敵一部。”
“或許只有這樣,我漢家才可以在這場戰爭中,立於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