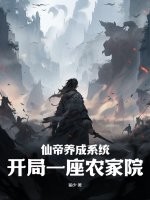第387章 戰爭機器的轟鳴
血狸奴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所以條侯認為,匈奴人必定會在今年秋後,自代北的馬邑-武州一線叩邊。”
“兵力大致在六萬至十萬之間,時間在秋八月十五之後,冬十月元朔之前。”
“為了抵禦匈奴人針對馬邑-武州一線的入侵,代北必須要在秋八月初十日之前,調入不下五萬兵力。”
“而根據少府的推算,這五萬兵力在代北駐守兩個月,再加上往、返,徵、散等事宜,總共需要耗費軍糧四十萬石。”
“其餘一應物資、軍費的消耗,也大體能維持在三萬萬錢之內······”
長樂宮,長信殿。
經過同周亞夫之間的專業交流,得以明確得知漢匈雙方軍事實力對比、戰略處境之後,劉勝幾乎是在第一時間,便來到了母親賈太后、祖母竇太皇太后所在的長樂宮。
同劉勝先前的預料並無不同:在聽到自己給出的資料之後,竇太后那鮮少會出現變化的澹然面容,也不由湧上陣陣遲疑之色。
事到如今,今年秋後的戰爭,基本已經可以說是板上釘釘。
——匈奴人肯定會來,漢家也絕不會服軟,東亞怪物房當前位面唯二的大塊頭之間,必將發生一場激烈的‘摩擦’。
而在這次摩擦當中,匈奴人考慮的是能得到多少、能賺多少;
反觀漢家,則只能考慮要付出多少,怎樣才能虧的少一些······
“自太宗孝文皇帝御駕親征,卻被濟北王劉興居的叛亂打亂佈局,並隨之為我漢家定下休養生息、積蓄力量的方針至今,已經過去了將近四十年。”
“在這四十年的時間裡,太宗孝文皇帝、先孝景皇帝都是一邊勵精圖治、省吃儉用,一邊又在匈奴人面前忍氣吞聲,忍辱負重。”
“我聽說最近,關東的儒生們之間,似乎出現了一種說法。”
“——說是太宗孝文皇帝、先孝景皇帝在位,可以被並稱為:文景之治。”
“嘿;”
“他們說的倒是輕巧。”
“說是大治、盛世,誰又知道太宗皇帝、孝景皇帝,為這治世花費了多少心血,忍受了多少屈辱?”
···
“多年隱忍,終於到了皇帝這一代,我漢家,也總算是排淨了內憂,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長城以北的匈奴人身上了。”
“皇帝,不會不知道自己肩上,究竟扛著多麼重的擔子吧?”
沉聲道出一語,引得劉勝緩緩點下頭,便見竇太后悠悠嘆出一口氣,手虛握成拳,下意識在大腿上輕敲起來。
一邊敲著,嘴上也不忘一邊說道:“四十萬石糧食,折價不過兩千萬錢,確實算不上多。”
“投入五萬人的軍隊,總耗費在三萬萬錢以內,也著實讓人生不出反對的念頭。”
“——至少比起如今,存在少府的數百萬萬錢,這不過區區三萬萬錢,還遠不至於傷筋動骨。”
“但既然做了,皇帝就要考慮清楚:這三萬萬錢,能為我漢家換來什麼。”
···
“太宗孝文皇帝之時,朝堂曾有過大致測算:大約三百萬萬錢,就足夠讓我漢家擊敗匈奴,並從此再也不必遭受外族侵擾。”
“那皇帝要砸在馬邑-武州的這三萬萬錢,可以為我漢家換來什麼呢?”
“換來的東西,值不值這三萬萬錢——值不值‘逐滅匈奴所需耗費’的百分之一?”
“如果不值得,那與其打,還不如就拿這三萬萬錢的一小部分出來,該和親和親,該賄金賄金。”
“若是值得,那皇帝不妨說說:這場仗打的值,又值在哪裡?”
以儘量平和的語調道出這番話語,竇太后便深吸一口氣,試探著將正臉面向身旁的孫兒劉勝。
而在竇太后身側,天子勝則是在母親賈太后隱含擔憂的目光注視下含笑低下頭,沉吟思慮起來。
這仗打的值不值?
當然值。
如果不值,劉勝就根本不可能在開春之時,那麼硬氣的拒絕匈奴人的和親提議,甚至由此徹底改變漢室對匈奴的一貫外交、戰略策略。
同樣的道理:如果不值,那在開春之時,竇太后也根本不可能由著劉勝胡來,而是會在當時就做主答應和匈奴人和親,並順便將劉勝臭罵一頓。
——沒那金剛鑽,劉勝就不會攬那瓷器活!
竇太后乃至滿朝公卿大臣,也不會允許劉勝那般任性妄為。
換個角度來說:既然劉勝在開春之時,順利拒絕了匈奴人,那就說明在其他人看來,也已經到了對匈奴人強硬一些的時候。
至少竇太后肯定這麼認為。
明知這一點,劉勝心中自也就沒有了太多複雜的情緒。
深吸一口氣調整好鼻息,再組織一下語言,劉勝終是再度抬起頭,自信滿滿的望向身旁,這位掌握著漢家天下、宗廟社稷的女人。
“秉奏皇祖母。”
“這三萬萬錢在今年砸在代北,孫兒認為,還是非常值當的。”
“只是孫兒所認為的值當,和皇祖母認為的值當,恐怕會稍有些出入?”
劉勝略帶俏皮的一聲試探,自引得竇太后溫笑點下頭,又稍一頷首,一副“願聞其詳”的架勢。
得到竇太后這個表態,劉勝也終是甩開了所有顧慮,將自己的想法和盤托出。
“方才,皇祖母提到此戰,我漢家要投入的四十萬石糧食並不算多。”
“事實也確實如此——四十萬石糧食,折價不過兩千萬錢,無論是相府國庫還是少府內帑,都能很輕鬆的拿出這四十萬石糧食。”
“皇祖母還說,此戰所需要花費的三萬萬錢,也不過是少府內帑存錢的百一之數,便是盡打了水花,也根本無傷大雅。”
“但孫兒從不曾忘記這些年——過去這近四十年的時間裡,太宗孝文皇帝、先孝景皇帝為了攢下這三萬萬錢,究竟忍受了多少常人無法忍受的屈辱。”
“所以別說是三萬萬錢、少府內帑存錢的百一之數了——就算是三百萬錢乃至三十萬錢,只要不值當,孫兒就絕不會辜負太宗孝文皇帝、先孝景皇帝多年來的積累。”
“至於這三萬萬錢花的值,究竟值當在哪裡······”
嘴上一邊說著,劉勝手上也不忘從懷中掏出一本以白紙堆砌的薄冊;
講冊子遞上前,同時也沒忘細心的為已近乎喪失視力的祖母,細述起冊子上的內容。
“這是丞相和內史奉先孝景皇帝之令,逐條彙算出來的——自太宗孝文皇帝前元三年,至先孝景皇帝九年期間,我漢家在和親、陪嫁等事上的花費。”
“先帝彌留之際,將錄有此書的竹簡交給了孫兒,直到近些時日,孫兒才令人將其抄錄於紙上,單獨成冊。”
“皇祖母不妨猜猜:丞相和內史,最終得出了一個怎樣駭人聽聞的數字?”
···
······
“——二十六萬萬錢!”
“自自太宗孝文皇帝前元三年,至先孝景皇帝九年,這前後不過三十三年的時間裡,我漢家為了穩住匈奴人,透過和親、陪嫁等方式,足足花了二十六萬萬錢有餘!”
“這還只是和親、陪嫁的花費。”
“在和親、陪嫁的同時,我漢家的邊牆,也仍舊在連年不斷的遭遇匈奴人的掠奪。”
“而這一項——同匈奴人作戰的軍費,陣亡、傷殘將士的撫卹,還有被匈奴人掠走的百姓、錢糧物資,根本就不包含在這二十六萬萬錢之內。”
“或者應該說:這些耗費,根本就龐大到無法計算······”
···
“方才皇祖母說,這三萬萬錢砸下去,怎麼也得換回一些東西,至不濟也要砸出些響動,才算沒有辜負太宗孝文皇帝、先孝景皇帝的殷殷期盼。”
“條侯先前也說過:就像是商人外出遊商,需要得到足夠的回報一樣,匈奴人每有南下扣邊,也總是會不忘考慮到‘能得到什麼’。”
“但在孫兒看來,國家層面的對抗,並不能像匈奴人那樣,以搶到多少人口、物資、錢糧為重。”
“——對外作戰,當然需要換得和投入相差無多的回報,但這個彙報不一定得失搶掠得來的奴隸、財貨。”
“正如此戰,孫兒想要靠著三萬萬錢換來的,便是一些看不見、摸不著,卻又對我漢家,對天下人彌足珍貴的東西······”
自信滿滿的一番話語,倒也沒有引來竇太后太明顯的情緒變化,只微微一點頭,便再次等待起了劉勝的下文。
便見劉勝稍一沉吟,再調整一下鼻息,方繼續道:“自太宗孝文皇帝,乃至是太祖高皇帝以來,我漢家,都早已習慣了看到匈奴人,就趕忙商籌和親事宜。”
“至今凡漢六十餘年,和親,更是已然成為了天下人習以為常的事。”
“——在太祖高皇帝之時,同匈奴人和親,幾乎全天下的人都感到屈辱;”
“——呂太后時,攣滴冒頓書辱呂后,更是惹得天下人無不悲憤!”
“——但到了太宗孝文皇帝之時,天下人聽說朝堂要同匈奴人和親,卻大都只會丟下一句‘也只能如此’。”
“再到先孝景皇帝之時,天下人更是一聽說匈奴使團到了長安,就再也沒有關注這件事了。”
“就好像天下人都早已習以為常,篤定朝堂會像吃飯、睡覺一樣,不假思索的和匈奴人和親。”
“最讓孫兒感到揪心的是:事實,也確實如此······”
···
“自高祖立漢,我漢家飽受諸侯之內憂、蠻夷之外患。”
“歷代先皇自忍辱負重,暗中積蓄力量以待時日,從不曾忘卻太祖白登之圍、呂后書辱之恥。”
“但天下人呢?”
“過去這麼多年的時間,我漢家的皇位,都已經傳到了第七代天子,天下人還記得我漢家,究竟為何要同匈奴人和親嗎?”
“——恐怕沒多少人記得了······”
“如今天下,恐怕已經沒有多少人,記得我漢家和親的初衷,是對匈奴人虛與委蛇,以贏得時間強大自身了。”
“過不了多少年,恐怕關東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孫兒問父祖:漢家為何要忍受如此屈辱,同北蠻匈奴和親?”
“父祖卻只得搖頭答道:似乎從盤古開天闢地開始,漢家,就一直在和匈奴人和親了······”
聽著劉勝語調低沉,又坑錢有力的話語聲,竇太后面上笑意稍去;
待聽到最後這一句‘從盤古開天地就在和親’時,更是全然不見絲毫溫和之色。
面色陰沉的思慮良久,又緩緩側過頭,伸手探向身旁的孫兒。
待劉勝趕忙拉過祖母的手,又好似強調般捏了捏,竇太后才終是深吸一口氣······
“皇帝覺得,是時候了嗎?”
“是時候,和匈奴人撕破臉皮了嗎?”
“北境的許多馬苑,都還沒開始產出戰馬;行伍之中,也幾乎不見多少精騎······”
“——如果單看騎兵、戰馬,那確實還不到時候。”
“——但若是考慮到再拖下去,我漢家的風骨就要被歲月壓彎、壓軟,孫兒認為,恐怕已經不能再拖下去了。”
“——就算是為了讓天下人知道:我漢家從來不打算對匈奴人低頭,這一仗,孫兒也必須得打!”
“——孫兒要讓全天下的人,乃至匈奴人都知道:漢家的新君、尚未親政的兒皇帝,也依舊是個難啃的硬骨頭!”
“——而且這塊骨頭,比過去任何一塊都更硬!”
“——這不是因為孫兒,真的敢奢求自己強於太祖高皇帝、太宗孝文皇帝、先孝景皇帝。”
“——而是因為孫兒以渺渺之身,卻站在了我漢家歷代先皇的肩膀之上,方得以睥睨蒼穹······”
有那麼一瞬間,竇太后的眉頭,幾乎是肉眼不可見的皺了一剎;
但在片刻之後,那獨屬於漢太后的雍容,以及那獨屬於竇太后一人的——昏暗、無神,卻又令人莫民心季的渙散雙眸,再次出現在了長信殿之內。
也正是隨著竇太后換換立起的身軀,這個名為‘劉漢’的戰爭機器,方開始發出厚重的轟鳴。
“賈大郎做少府的事,皇帝儘快辦吧。”
“既是要戰,那少府的位置,就必須得有人坐著······”
···
“明年開春,皇帝行冠禮。”
“叫太常記著些,早做準備······”
···
“叫周亞夫來見我。”
“這麼多年不見,倒還真有點想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