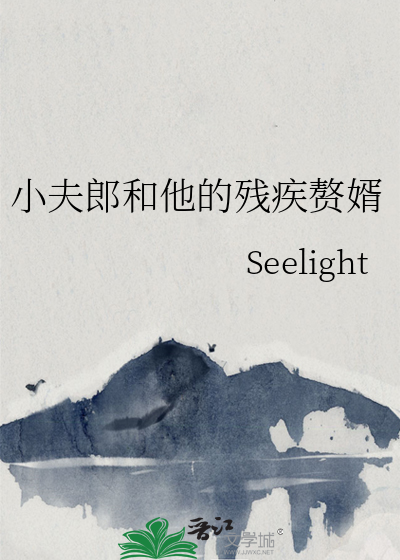春未綠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自古哀兵必勝,這個舒兆中這一手玩的還真好。”有兩名士子在不遠處站著,指指點點。
這兩人都是滎陽本地大戶,一位姓楊,並不是出自弘農楊氏,但因為其伯父中進士之後,家中又行商,有權又有錢就比舒家這種驟然曇花一現的家族活的好多了。另一位則姓趙,出自河北士族清河張氏,舉家搬遷到此,二人附學鄭家,卻又覺得鄭氏子弟一代不如一代,私底下沒少笑話。
楊士子笑道:“舒兆中的姑父聽說在南京任個小官,三年五載也不會回來,舒家本就破落。他還敢在鄭狀元面前玩這一招,真是傻。”
張士子則意味深長道:“我看鄭狀元方才寥寥數語,就令我茅塞頓開,可見他實在是很有才學有名望之人。若是能收你我二人在門下,我們科舉必定能中。”
二人說完又看向鄭灝如何行事,只見他對榮飛榮達使了個眼神,二人不費吹灰之力就抬走舒兆中,舒兆中被甩了出門,從頭到尾鄭灝都沒有再說二話。
舒兆中都嚇傻了,他沒想到鄭灝是來真的,大戶人家不都是非常講究臉面的嗎?更何況舒家還是鄭家的姻親呢。
可鄭灝想我鄭灝行事,誰又敢說什麼?我毋須為了個嫖賭之人,來浪費唇舌。
他如此行事,令人膽寒,那楊、張兩位士子一凜。
接下來原本想效仿舒兆中的人,都灰溜溜的走了。
這次大考,剔除品行不端文墨一文不通者十人,另有二十五人在下舍,中舍十五人,上舍十人,在九月徑直過來讀書就成。
有教無類可以,但品行差,有不良嗜好就是不成。
本來年輕人逛青樓也沒什麼,但是嫖賭放在一起,日後引奸引盜也說不定。
麗姝見他回來的這般晚,情知他守孝在身,肯定不會在外吃酒席,故而讓廚房做了幾樣清粥小菜過來,親自服侍他用。
“你坐下來吧,你也忙,倒是總惦記我。”鄭灝看麗姝這樣埋首故紙堆的樣子,就知道她多累了。
麗姝笑道:“那是,我常常聽我爹說任親民官的不容易。你出自翰林,又是這樣的身份,平日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倒是我,什麼樣的人都接觸過,所以啊,那些人難不倒我,尤其是針對道德綁架。只要我沒有道德束縛,那些道德就休想來綁架我。”
“反正記住這點,沒人能把我如何了?”
鄭灝點頭:“你說的極是,今日那個舒兆中頭都嗑出血了,我把他叉出去了,據說摔了個鼻青臉腫。”
麗姝很詫異:“又是這個舒家?我看上次那位舒姑娘,雖然是個荊釵布裙的女兒,但好歹為人敦厚,怎麼舒家其餘的人都是這般不知道輕重。”
“誰理他呢?我其實私下早就打探好幾個素來有惡習的子弟,這舒兆中成日跟著那富戶少爺胡混,欺男霸女不說,混跡賭坊妓院,簡直是五毒俱全。這樣的人,遲早也會壞我們鄭家的名聲。”鄭灝想甚至危害更大。
麗姝卻道:“我聽說舒家就這一個兒子,舒姑娘那麼大的姑娘都那般寒酸,可見舒家境況很不好。你把他趕出去了,怕又得鬧一場。”
鄭灝看著麗姝,捏了捏她的下巴:“我不怕。”
麗姝看了看他的臉:“真是稀奇。”
這事兒還真的被麗姝猜準了,舒兆中被丟出去後鼻青臉腫,回到舒家之後,舒大奶奶很快就找到舒氏這裡來了。
舒氏正掰了小兔子模樣的窩頭給靈姐兒吃,靈姐兒吃了半個,又道:“還有一年多我才三歲,這樣就能去讀書了,那裡有好多小夥伴呢。”
“好,到時候娘給你縫一個書袋,咱們家靈姐兒可是要做才女的人,是不是?”舒氏笑道。
靈姐兒歡歡喜喜的笑了。
母女二人正說趣事的時候,正好舒大奶奶過來,她原本也是官宦人家的女子,後來公公去世,婆婆多病,家裡男人不爭氣。硬是把她一個以前靦腆的女子,到現在潑辣的渾然沒有任何顧忌了。
舒大奶奶一坐下來就道:“姑奶奶成日家錦衣玉食,還養著別人的女兒,也不管管你孃家,你弟弟和侄兒都要被人欺負死了。”
舒氏就知道她嫂子過來找茬要錢,故而先讓下人把靈姐兒抱下去,才道:“馨姐兒可是得了我們宗房一千兩銀子,那些銀子呢?還不是都在你們手上,如今你們倒是在我這裡哭窮。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什麼情況,我們大爺上京前,家裡派著老管家管賬,與我一文錢關係也沒有,我接濟你們都是我自己的月例銀子攢下來的。”
為了舒家的事情,她都差點死了一回了,怎麼還會管舒家的事?
舒大奶奶卻恨鐵不成鋼道:“還不是你侄兒,被你們宗房的大爺趕了出去,連書都沒的讀。我說姑奶奶,你也是鄭家七房的當家奶奶,還是原配夫人,我就沒見過你這麼窩囊的。”
“什麼?兆中被趕出來了?”舒氏一驚。
自己原本以為宗房和她的恩怨到此為止的,沒想到現在又橫生枝節,報復到了她侄兒身上。這未免也太狠了吧,純粹是置人於死地。
舒大奶奶見舒氏還不知曉,遂道:“不僅僅是被趕出來了,頭都破了,還被四仰八叉的摔出來,你說說這要我們怎麼辦啊?偏偏那麼多人都讀得,就他讀不得。姑奶奶,我也不是怪你,當初榕二太太的兒媳婦崔氏,雖說有個清河崔氏的大姓在那兒,但是家裡精窮了。可人家靠著宗房,他那侄兒就沒問題,論學問,你侄兒可比他強。”
“這……”舒氏是知道榕二太太介紹過的那位子弟,是她兒媳婦的外甥,不是什麼大族出身,和具二太太的侄兒楊瀾倒是關係不錯。
就因為人家關係好,即便才學一般,也被留下了,舒氏聽聞此事也覺得不服氣。
見小姑子還是這樣死頭死腦的,舒大奶奶忍不住抱怨道:“這麼多年你在鄭家一把年紀純粹是活到狗身上了。你生不出孩子來,總能抱個庶出的在膝下養著吧,偏偏你連這個本事都沒有。好了,如今連我們舒家也因為你被人欺負。”
舒氏想起這些年她過的日子,比黃連還苦,可她並不真傻。
鄭家這樣的人家,都是世代顯宦門庭,是不可能休妻的,她在鄭家活的好好地,做什麼要再次為了舒家又頭腦發熱。
所以這次她卻不能再莽夫了:“嫂子,你這般罵我,我也無法。我的確無能,好歹也給你們爭取了一千兩,這些銀錢也夠你們用一陣子了。你若信我,就自然信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意思,我想等水到渠成,我總會給你們一個交代。風水輪流轉,誰也不會一輩子在高位吧。”
舒大奶奶聽她這話卻總有些害怕,她只是想要個說法,想讓舒氏去替她說情,讓兒子重回鄭家族學讀書,可沒想過要怎麼要對付別人。
尤其是宗房那位太太可是出手闊氣極了,鄭家宗房時多麼至高無上的存在,怎麼能得罪。
也不知道舒大奶奶何時走的,舒氏一個人從天明坐到了天黑。
揮退這些子弟,當然會引起不少爭論和背後詛咒,麗姝知曉鄭灝為人清風朗月,很少受到任何負面評價。
她總怕他難過,所以特地在泡腳的時候開解他:“其實就像千百年來的改革派,在當時總會身負罵名,商鞅吳起都是如此,因為他們觸犯到了利益。可千百年來,大家都知道,秦國正是受益商鞅變法才統一六國,而楚國則因為任用吳起數年,卻又不能堅持下去,導致楚國並不如秦國。任何觸動別人利益的事情,都會遭到攻訐辱罵,你不要放在心上,只要咱們夫妻同心,就一定會其利斷金。”
鄭灝泡腳時正在冥想,沒想到麗姝同他說起這個,他有點詫異,這話是安慰他呢,怕他傷心難過。
所以,他在妻子眼裡是個嬌夫嗎?
儘管如此,鄭灝卻沒有反駁,反而一臉感動,如聞仙音似的,還道:“麗姝,你總是這樣變著方兒的讓我開心。”
“哪有啊,我說的都是實話嘛。”麗姝也不喜歡那種明明一身的才智,卻只顧自家撈錢,為了名聲歌舞昇平。
世人總覺得明哲保身,就什麼都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殊不知傾巢之下焉有完卵。
鄭夫人也的確是這麼和鄭灝說的,就在鄭灝次日早上去請安的時候,她就說起這些話:“六老太太好歹是長輩,她昨兒說你退了一個學生,害的他們要賠給人家兩百多兩,她們家哪裡有銀錢賠啊。其實兒子啊,水至清則無魚,你可麗姝年輕,總想幹一番大事,這我都能理解。但就像天下吏治腐敗一樣,即便你再如何清廉自持,也沒用,這個官場該糜爛還是得糜爛。”
若是以前,鄭灝很贊成這個道理,他有些做官的族人,實際上平日處理事情全部靠的是幕僚,不想做官就魚肉鄉里,在任上靠著當大官的族人庇護,居然考評還挺好。
這樣的官員還比比皆是,上下勾結,若有不合時宜者,即便能力再強,也無法出頭。
可就因為這樣,就不做了嗎?整日醉生夢死,卻不知將來又如何呢?
所以,鄭灝搖頭:“娘,自古無人為之,兒子就不能為了嗎?與其庸庸碌碌,行屍走肉,不如也鬧他一鬧,一味無為而治,未必就風平浪靜。”
見兒子主意已定,鄭夫人心想,大抵都是麗姝的主意,她爹劉承旭就是有名的犟骨頭,她也是如此。
別人在泥淖裡,只要能拿錢都能笑嘻嘻,她就不行,寧可不拿錢,也要跳出泥淖,堅決不同流合汙。
但鄭夫人想,她還是很有幾分手段的,至少現下動靜這麼大,居然名聲比具二太太好多了。
“罷了罷了,不撞南牆不回頭,我也管不到你們了。”鄭夫人如此道。
和鄭夫人不同,鄭老爺就一直支援兒子,他也是年少及第,也算是位極人臣,很知道所謂千里之堤毀於蟻穴,因此對鄭灝提及麗姝的功勞,不由得道:“如今你我父子二人在高位時,算得上是鮮花著錦,烈火烹油,一路為你祖母路祭之人多如牛毛?可若是我們稍有差池,恐怕就會被人抓著把柄。尤其是你——”
說到這裡,鄭老爺道:“我既為邊臣,就不可能入閣,但你和我不同。官員的名聲,就如同白壁一般,若不好好約束子弟,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可能是政敵將來威脅你的把柄。”
鄭灝頷首:“爹說的是,兒子何其有幸能得父親提點一二。”
他們父子的關係和一般父子不同,宗房子嗣艱難,鄭老爺是鄭宰相中年所出,鄭灝也是他爹很晚才有他,因為鄭夫人也在家守孝幾年才嫁過來。因此,鄭老爺對小時候的鄭灝就寵溺非常,非尋常嚴父的樣子。
平素都是鄭灝陪麗姝用飯,今日他索性就在鄭老爺這裡用飯,麗姝聽到了,雖然有些空落落的,但也吩咐廚房:“老爺愛吃炒臺菜,這炒臺菜的菜心最糯,用新鮮的蝦肉炒最好了,這道菜可一定要做。”
珠蘭聽了,對外吩咐一聲,麗姝則放下筆伸了個懶腰。
她自己吃,一個人倒是吃不完,就讓珠蘭和臘梅坐下陪她吃,這兩人是她最親近的左右手,日後她也會像對聽雪和絲雨一樣,替她們尋個良人,依舊在府裡做事,替她管家。
若她們要放出去,麗姝也願意放籍,就像她當年想放聽雪和絲雨放出去,她二人都不願意出去。出去了能嫁什麼好人,在府裡是副小姐,成親了也是管事娘子,在太太奶奶們面前得臉,也有下人服侍,更重要的是她們都願意跟著麗姝幹。
那邊鄭老爺見桌上都是自己愛吃的菜,不禁道:“你媳婦兒真是孝順,我回程時咳嗽了幾聲,就讓人尋了大夫過來,對我們兩老沒話說。我身上的鞋襪護膝都是她做的,尋常兒媳婦哪裡能這般啊。”
“那是,爹孃若不看重她,怎麼讓她嫁給我,兒子等了她許久呢。”提起麗姝,鄭灝就覺得很幸福。
吃完這頓飯,鄭灝也覺得心裡舒服許多了,覺得自己得到了父親的支援。
他則斟酌道:“兒子想清弟總不能一直閒養在家中,這大丈夫豈可一輩子無權,偏他年少時身子又有病,如今既有官員身份。我把那些刺兒頭驅除後,就讓他來管著族學,您看如何?”
鄭老爺皺眉:“他的身子好了嗎?”
此時,卻見鄭清大步流星的走進來:“爹,兒子身體俱好了,您就讓孩兒試試吧。”
看著小兒子期盼的眼神,鄭老爺思慮再三,最終還是點頭:“好。”
鄭清很是歡喜,和鄭灝相視一笑。
很快過了一個月,鄭清就走馬上任,這讓不少人出乎意料,大家都以為鄭灝會管族學,沒想到居然是鄭清來管,大家鬆了一口氣。
眾人對鄭清都沒有任何認識,只知道他身體孱弱,宗房用珍稀補品養著,身體差自然弱。所以很多人就開始對他輕視起來。
麗姝也是很擔心:“清弟一貫在家,和人打交道的少,那些少年不少頑童,他能不能管好呢?”
“大嫂您就別擔心了,您閉門看賬本一個月,可看出什麼門道來了?”譚氏一點兒也擔心自己的丈夫。
麗姝其實知曉鄭清恐怕也不是一般人,但這麼說只是怕到時候鄭清犯病了,譚氏和長輩們責怪,如今見譚氏都不說什麼,她也就放下心來。
而六老太太和鄭澤一家卻是對鄭灝怨念很大,之前六老太太還站在麗姝這邊去說過舒氏,轉眼,她就和具二太太還有舒氏混在一起了。
具二太太初時沒了管家權,就已經嚐到下面的人不把她當回事兒了,好在這些年她私下撈了不少銀錢,也在外接辦了鋪面,她又會持家,日子過的比舒氏和六老太太家裡要好太多了。
現下她這裡擺著幾碟時興的鮮果糕點,都沒怎麼動過,六老太太倒是滔滔不絕:“說起來還是宗房老夫人在的時候好,現在她一去,什麼牛鬼蛇神都跑出來了。南蠻子也想管起咱們家裡的宗務了,我們鄭家嫡支一貫都只和盧、李、崔三家聯姻。”
舒氏心想之前你可不是這麼說的,若非是因為你家裡出了血,你現在也不會和我們混。連舒氏都知道的事情,具二太太又怎能不知?
故而,具二太太道:“可荊湖劉家如今聲勢也是銳不可當,再者,那劉氏雖然年輕,卻自有氣度,六嬸您也是太過貶損了。”
六老太太不屑道:“我不是貶損太過,是當年她和灝哥兒剛成婚時,我就知道她這個人精於算計。明明回來守孝,卻非要攬事,還不是為了搶過管家權,生怕沒有自己的地位。這個人啊,年紀輕輕權欲太重,就似漢朝的張湯,唐朝的來俊臣一樣的人物,你看她對待你們盡顯她性子裡的詭譎奸詐、反覆無常、兇險邪惡的酷吏一樣的手段。不過,你們放心,來日她的下場肯定和來俊臣,來俊臣當年受到武則天重用,後來卻因得罪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被誅。”
具二太太和舒氏對視一眼,都覺得六老太太說的也太過狠了,雖說劉氏的確也有些手段,但是看的出她接受族務以來,並未追究具二太太不發放月例之事,已經網開一面了。說白了,就是爭權奪利,也沒誰對誰錯,看誰手段更高罷了。
但她們也不可能和六老太太因為此事鬧翻,這位六老太太可是族裡很有聲望的。
她們三人說的起勁,卻不知道麗姝不過一盞茶的功夫就已經知曉了。她初來鄭家,對各房不甚瞭解,訊息也不靈通,行事有掣肘。這幾個月卻開始安插人手,買通人做細作,沒辦法,這位具二太太兼併土地逼迫百姓的事情她必須知道始末,有沒有逼死人也該早知曉。而舒氏和六老太太都是和她們有私怨,不穩定的人,所以她必須監視好。
這個六老太太也是個惹禍之人,尤其是她為了自己享樂,幾乎是逼迫鄭澤收受賄賂,娶心術不正的王氏,甚至是到族學還貪錢,幾乎引狼入室。
現下還大肆說自己的壞話,這些話已經算得上是誹謗了。
具二太太說話做事非常謹慎,滑不溜丟的,但是六老太太這裡,她可不會姑息。
所謂的“敢言”就是六老太太的利器,她用一張嘴走遍族中,她兒媳婦懦弱不堪,孫媳婦王氏如今聽聞開始禮佛,當然,禮佛只是她不願意出來交際,也不願意再供給這位太婆婆,也不管家,反正就是不出錢,讓鄭澤想法子。
麗姝可以寓言,這位六老太太現在出來搞風搞雨,就是想給具二太太交投名狀,畢竟等自己走了,這個家指不定還得交給具二太太來。
畢竟榕二太太不行,她的兒媳婦也不行,其餘這一輩的也差不多死絕了。
六老太太還一無所覺,她在這裡罵了麗姝一頓,回到家還多吃了一碗飯,但因為鮑魚不新鮮,又把下人罵了一頓。
睡覺前,又嫌棄蠶絲被是去年的一股黴味,把下人又罵了一遍。
六房的下人一個月月例三百個錢都沒有,做的事情卻十分繁瑣,這六老太太還刁鑽古怪。今夜兩人還得守夜,隨時隨地半夜起身扶著她老人家出恭喝水,遲疑一會兒都被罰跪。
平日下人們敢怒不敢言,今日不知道怎麼一起守夜,一貫很是沉默的葉兒,對方才被罵的苗兒道:“你也是夠倒黴的,這些日子天氣不好,蠶絲被髮黴和你有什麼關係,還有鮑魚的事兒,那也是廚房的人存放不當,你真是太倒黴了。”
“葉兒姐姐,你今兒怎麼說起這些話來。可這有什麼法子呢,我們是奴婢,又不能改變。”
“你看看你年輕輕輕天天被罰跪,地上這麼涼,你都十七了,月事還沒來?怕都是這鬧的。我說這些還不是因為咱們同病相憐。”
二人絮絮叨叨的說了許多話,都壓低了聲音,六老太太卻有了尿意,正欲喊人,卻聽到說的激動的葉兒道:“那老虔婆天天苛待我們,遲早下阿鼻地獄,把她的眼珠子挖下來,舌頭拔下來。”
苗兒也是道:“真想一刀了結這個老東西,葉兒姐姐,現下就咱們倆守夜,不,就是咱們不守夜,別人守夜,也想結果了這個老虔婆。”
六老太太嚇的屁股尿流,原本一泡尿居然撒在了床上,眼見黑影靠攏,她暈厥了過去。
等到次日醒過來,六老太太見葉兒和苗兒還有其她丫鬟都心緒平常樣子,忍不住指著她們倆道:“是你們,就是你們兩個小蹄子要害我。”
“老太太,昨兒是彩蝶和我一起守夜的,葉兒和苗兒根本就沒來。”綵鳳笑道,她深知老太太昨夜尿失禁,老人愛面子,肯定又要責打責罵葉兒和苗兒,聽說苗兒因為長期被罰跪都十七了小日子都不來,她自然幫忙遮掩。
否則,再去哪裡的人牙子能買到一個月才三百錢的下人,常常受到虐待的。而且她倆打發出去了,以後就是她和彩蝶什麼都要做,還不如替葉兒的圓謊。
六老太太說胡話,天天嚷嚷著別人要殺她的訊息傳來,更不敢出門了,聽說身後一片葉子掉下來她都猶如驚弓之鳥。
具二太太聽聞這個訊息,直撇嘴對丈夫道:“這族裡也只有六老太太仗義執言,沒想到她居然得了驚恐之症,天天說別人說她壞話,要害她呢,嚇的不行。”
具二老爺就不喜歡六老太太,只道:“她是早年做虧心事,所以天天怕鬼敲門。”
可具二太太很是惋惜,這可是自己招的一員猛將,還沒開始呢,就已經摺了。
彼時,麗姝正和鄭灝對弈,她吃了鄭灝的白棋,笑眯眯的道:“看看,你這棋道高手也輸給我一子了。”
鄭灝則呷了一口茶,問起她來:“六老太太這是怎麼了?你去看了沒有。”
“不用看我就知道。”麗姝笑著,因為就是她乾的,以其人之道還之其人之身,只是沒想到她不經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