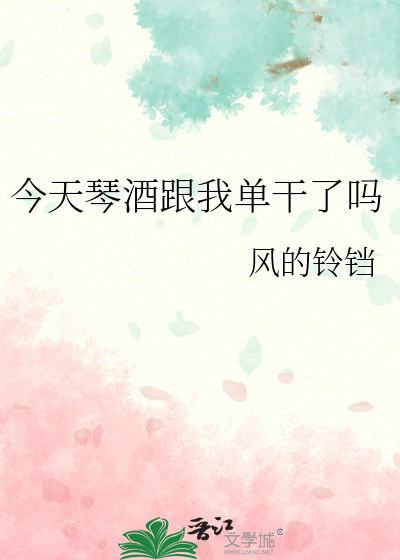第五本:後記,第一章:馬特
精甚細膩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當我醒來時,我年輕了七歲。
迷失方向根本無法形容我當時的心情。我的肺嘶嘶作響,急需空氣。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終於睜開眼睛,看到了漆黑的天花板。我坐起來,靠在牆上。柔軟的床單裹著我,一堆枕頭支撐著我。一切都感覺不對勁。
這些都不應該出現在這裡。我不該在這裡的。我感到頭暈目眩。我的大腦仍在努力整合,試圖將眼前的一切塑造成一幅連貫的畫面。
房間裡幾乎漆黑一片——我的房間,我提醒自己。這是我的房間。唯一的光源是房子附近的一盞路燈,從一扇掛著窗簾的窗戶裡透進來。長長的黑影延伸了地板的長度,把房間投射成一塊塊的顏色,突出了填充角落和縫隙的空隙。一切看起來都很熟悉,就像我剛從夢中跌跌撞撞地走出來一樣。
這一切都是一場夢嗎?
空氣中充滿了一種奇怪的感覺,我很久沒有這種感覺了。微弱的嗡嗡聲和電的噼啪聲。我的電腦。一臺真正的電子PC機。那天晚上我把它忘在那兒了。我們離開的時候,我正在和一個人聊天……她的臉掠過我的腦海,但那是一個模糊的輪廓,我無法形成一個完整的畫面。從我們上次說話到現在已經過去了一輩子。也許根本就沒有時間,我突然想到。
我下了床,急忙跑到電腦前。我坐下時,椅子轉了起來。我都忘了它還有輪子。我不耐煩地敲打著鍵盤上的空格鍵。那是一臺便宜的機器,是我從卡爾那裡買來的二手貨,而且總是要過一會兒才能醒過來。我甚至還沒有把它關掉,但我還是得等著裡面的碟片轟隆作響,風扇重新加速旋轉。顯示器發出一聲尖銳的裂縫,然後終於恢復了活力,隨著背光慢慢變暖,色彩褪去。
就在螢幕的角落裡,正是我想要的。時間是2010年10月6日凌晨1點32分。那是一個星期三。
現在我更困惑了。多年過去了,對吧?我小心翼翼地把手放在臉上。有些東西不見了。一切都感覺很順利,很陌生。那已經不是我的臉了,不是我記憶中的樣子了。突然間,我的胳膊和腿感到非常虛弱。
這一切都是一場夢嗎?我生命中令人作嘔、恐怖的近十年,完全是在一個晚上由我大腦的隨機怪癖想象出來的?所有那些生死相遇,冒險,背叛,浪漫?跨越多年的戰役和戰鬥?這可能嗎?
我開啟瀏覽器視窗。我還在努力回憶那天晚上我們到底在做什麼。我必須相信過去的我沒有清理自己的身後,沒有留下線索讓熟練的追蹤者可以追蹤。這次是電子線索,但基本思路是一樣的。這是我能想到的最接近多年前發生的事情的記錄。
不。就在前一天晚上。那只是幾個小時前的事。我現在需要記住這一點。
去塞拉維爾公園的地圖還開著。我記得很清楚。爸爸失蹤那天留給我的那輛卡車是我開車送我們去的。在我接了我們的朋友之後,我們把車停在了樹林的邊緣。我本來不想去,但布萊克的熱情很有感染力。他在外面看到了什麼,我們也必須看到。珍在樓下偷聽,勸我去。
然後,布萊克發現樹林裡有個影子閃過,我們跟著。
布萊克穿過樹林,我們緊緊地跟在後面。他不停地繞回來,喊著讓我們跟著他走一條只有他能看見的小路。就像我們一起打球的時候,布雷克總是衝在比賽的前面。他總是比他應該到達的地方快五步。
我們穿越的時候,他和以前一模一樣,只是他把它變成了一種優勢。他總是領先敵人五步,做別人不敢做的事。我利用他的瘋狂贏得了不少戰鬥。
這些實際發生了多少?有多少是真的?
更多的記憶充斥著我的腦海,伴隨著恐懼的毒害。我所做的事情的重量開始壓在我的腦海裡,威脅要把我完全壓垮。我會變成可怕的東西。我被迫在成百上千,成千上萬人的生命懸於旦夕的情況下做出決定。我犧牲了盟友,失去了朋友。我會走到失去一切的邊緣每一個人。我們好不容易才逃到對岸。我痛恨我所做的一切,痛恨我曾經的樣子。
有出路嗎?
答案來了。這是如此簡單和容易,我笑出聲來。我現在到家了。我在這裡很安全。沒人再追殺我了。幾乎沒人認識我。沒人會知道我做了什麼。如果真的是我乾的。
在我面前展現著一條美麗的金色小徑,我可以毫不拖延地走下去。沒有遺憾。我終於可以回到正常、簡單的生活。不要再打架了。就是正常的生活。我可以和朋友出去玩,打籃球,讓其他人來控制我。我要做的就是忘記。
就在我想這句話的時候,我感到肩上的重量減輕了。我把螢幕上的塞拉維爾地圖關上,象徵性地把它擦乾淨。瀏覽器在下一個標籤頁回到了我和一個女孩的對話。她有一張拘謹的臉,一種戒備的表情,好像她總是在她的微笑背後隱藏著什麼——但她的眼睛裡有一種友好的智慧,那種懇求你記住她說的每一個字的眼睛,即使它們可能很少而且相隔甚遠。她的聲音溫暖而充滿激情,是那種能激勵軍隊投入戰爭的聲音。
我們在幾天前她邀請我去的聊天室裡聊天。回顧這段對話,我是如此隨意和放鬆。我都忘了怎麼那樣說話了。這些天,所有的東西要麼是為法庭準備的,要麼是在激烈的戰鬥中即興發表的激動人心的演講。我已經不知道怎麼和別人單獨交談了。
我聳聳肩。我會想辦法的。我們只當面說過幾次話,而且通常是和她的朋友在一起。我可以把事情當作一個玩笑,或者讓她來說話。我可以繞過它。
我會繞開這一切。一切都會恢復原狀。畢竟昨晚什麼事也沒發生。我的生活非常正常。我只是個普通的高中生。僅此而已。
我讓電腦重新進入休眠狀態。我想我應該跟著它走;畢竟,我早上還要上學。在經歷了所有這些之後,這聽起來非常簡單。我幾乎在期待著平淡無奇的舊課堂。我剛要跳回床上,就聽到樓下有沙沙聲。有人在走動。我猜想是我母親又下班晚回家了。她遲到並不奇怪,但我突然想擁抱她。我很想念她。
我已經忘記了家裡有多冷,尤其是在十月的深夜。我翻遍了衣櫃找我的夾克。我最喜歡的夾克。我品嚐著它的柔軟和溫暖。這是我多年來想念的另一件事。
幾個小時,我提醒自己。才過了幾個小時。
我開啟門,門嘩啦嘩啦地響著以示抗議,我畏縮了一下。如果把手一直轉動,總是會這樣。我通常會記得在轉得太遠之前停下來。只是我需要記住的清單上的另一項。如果這樣下去,我就得把它們寫下來了。我隨手關上門,朝樓下走去,廚房裡的燈亮了。
走下樓梯,感覺像是過了好久。我每走一步都在想我該說什麼。如果我說什麼。如果我只是假裝下來喝一杯,如果我在上學的晚上這麼晚還沒睡需要一個藉口。我媽媽不是那種會因為我們熬夜而生氣的人。她盡了最大的努力養活我們,但這正是我為我們三個人做晚餐的那種晚上,把她的放在冰箱裡,不管她回家多晚。我以前討厭為她收拾剩飯剩菜,也討厭她不能在我們身邊做飯。
今晚,我更加感激她這些年來為我們所做的一切。她可能一週有五個晚上不在家吃晚飯,但當她每週做兩份全職工作來保證我和妹妹的健康和學業時,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我覺得我做不到。我在那邊學到了很多烹飪的知識。到了週末,我要請她吃一頓豐盛的晚餐,今晚,我要提醒她,她是多麼偉大。
我拐了個彎,看到的不是我媽媽,而是我妹妹詹妮弗的棕色長髮,從她正在翻找的食品儲藏室的門上露出來。我走進去時,她驚訝地抬起頭來。點心蛋糕的碎屑從她手中掉了下來,灑在地板上。其實我是設法偷偷接近她的。
“呃……嘿,珍,”我尷尬地說。
“嗨,珍嗎?她慢慢地重複著。“嗨,珍?“就這樣?”
“…你是想聽我講話嗎?”
Je
皺起了眉頭。“不,但是……經歷了這一切之後……”
“什麼全部?”
珍的嘴張大了,我發現她的牙齒上沾著一點同樣的點心蛋糕。我皺起眉頭。她的眼睛睜得像餐盤那麼大。“你……你不記得了?”
她的話是一把大錘。即使我匆忙建起的那堵牆開始崩塌,我仍然想否認這一切。哪怕再多幾分鐘,我也想留在那種幸福之中。“記得什麼?”
“上帝,馬特。去做每一個kapavas,visdu
alav。”
“Dou
a
akapavas,Je
。”艾託林從我嘴裡不請自來地蹦了出來。珍的侮辱需要得到某種回應。我無法釋懷。但當她的臉因滿意而扭曲時,我感到我匆忙建立起來的舒適的無知結構像一個搖搖欲墜的堡壘一樣在我周圍崩潰了。
如果珍還記得,如果她會說艾託林語,那就是真的。
塞拉維爾是真實存在的。
“我也是這麼想的,”珍得意地說。“順便說一句,你的發音還是很爛。”她從地板上撿起零食,跳上廚房櫃檯,仔細地檢查著。過了一會兒,她咬了一口。她的臉亮了起來。“這味道太棒了。馬特,我們得再買200個。現在。”
我靠在冰箱上,雙手捂著額頭。一陣頭痛開始襲來,就像太陽穴裡的鼓聲越來越響。
“頭痛?她問。
“是的。”
“你醒了多久了?”
“就幾分鐘。你呢?”
“大概半個小時吧?”別擔心,一切都會過去的。是的,它來了,”她補充道,一陣巨大的疼痛在我的大腦中傾瀉而下。
我的頭骨感覺就像有人用一把鈍斧反覆地把它切成兩半。我緊緊地抓著冰箱門的把手,感覺自己要崩潰了。我的視線消失了,廚房的燈光消失在一片黑暗的恐怖中。一個微弱的聲音跟著我下去,越走越遠,我被遺忘了。它在呼喚我,我拼命想回答,但我所能做的就是跌倒。幾英里外,我感到了一場可能是小地震的衝擊,使我的心臟顫抖。
我猛地活了過來。燈光又亮了。我坐在地板上,直直地盯著那隻蒼白的、嗡嗡作響的燈泡。我聞到了巧克力的味道。珍的零食。她的臉在幾英寸遠的地方,近距離凝視著。我一睜開眼睛,她就挪開給我空間。
“你沒事吧,馬特?”
我咳嗽了一下,想清一下突然又幹又痛的喉嚨。“是這樣認為的。我想喝一杯。”
“任何偏好?沒有sylva
di
e,但如果你想的話,我可以給你弄點更烈的。我想媽媽在車庫最上面的架子上放了一些東西。”
我坐了起來,感謝冰箱溫暖堅硬的外表。疼痛減輕了一些,邏輯和理性開始恢復。“珍,我們還未成年。”
“你25歲了,馬特。”
“不,我十八歲了。你十六歲。你沒注意到嗎?”
簡嘆了口氣。“是啊……就像我們從未離開過一樣。”
“是的。”
我們倆都沉默了一會兒。我站起來,在櫥櫃裡翻找著。我找到一小瓶布洛芬,拿出兩片藥片。很快喝了一杯水之後,我已經感覺好一點了。我在廚房的桌子旁坐下,把頭靠在牆上,等待著效果開始顯現。
“真希望我能想到這一點。”珍喃喃地說。
“嗯?”
“止痛藥”。她伸出手來,我把瓶子遞給她。“我差點忘了它們的存在。”
“現代醫學的奇蹟,”我喃喃地說。我閉上眼睛。那種痛苦仍然太真切了。我的大腦每一次劇烈的搏動都想從我的頭骨裡擠出來。我聽到外面有輛車啟動了,引擎的聲音就像從幾英寸遠的地方穿過我的耳膜。
當我意識到這一點時,我的眼睛又睜開了。
“珍,你不能——”
“不。我偏頭痛發作時就試過了。不行。”
她嘆了口氣,在我對面坐下,又端來了一雙水杯。她從桌子那邊遞給我一個,我感激地吞了下去。我的喉嚨仍然覺得又幹又幹,水的作用也就到此為止了。
“我猜這句話沒有傳達出去。”發現珍再也無法痊癒,有點讓人震驚。它是如此有用。如果珍不能治癒我們,也不能阻止布萊克在他那些瘋狂的特技表演中喪命……我只能圍繞這個限制來計劃了。
等待。不,我不會。我生命的那一部分結束了。如果我能做到,我就不會再陷入需要她能力的境地。我要過平靜、正常的生活——不管要付出什麼代價。
“我想現在開始停了,”她大聲說,又吞下了更多的水。“你是不是和我一樣渴得要命?”
儘管喝光了整杯,我的嘴巴和喉嚨仍然感覺像沙漠的表面。我點了點頭。
“水?”
“聽起來不錯”。我把椅子往後挪到角落裡,這樣我可以更舒服地靠在牆上,然後把外套捆起來,撐在肩上,臨時做了一個枕頭——就像我在競選中做過一千次的那樣。“你看起來還是比我好。”
珍聳了聳肩,又倒了水回來。“也許只是因為我睡得更久。我也有東西吃。”
“零食”。我皺起了眉頭。“你應該吃些更實質性的東西。”
“你知道我有多久沒吃巧克力了嗎?”
“是的。”
簡嘆了口氣。“別這麼沮喪,馬特。我們回家。我們又通電了。自來水!”就在這時,一輛重型卡車從外面開過。我們家鬆動的窗戶發出輕微的嘎嘎聲。“汽車,馬特。汽車!”她拉長了字兒,每個音節都充滿了興奮。“飛機、火車、吹風機。洗髮水。天啊,陣雨。馬特,我們又有淋浴了。”
“我明白,我明白。”我強顏歡笑。“回家真好。”
“給你。”珍笑了。她把剩下的水一飲而盡,心滿意足地呼了一口氣。“連水的味道都更好了。”
“他們又沒有水過濾器。”
“嗯,西爾弗一家是這麼做的。我們整件事,他們——”
我打斷了她。“是的,他們用魔法過濾了它。你告訴過我的。”除非萬不得已,我不想再聽了。我們越早恢復正常越好。我想暫時遷就她,但不可能長久。
“是的。真酷,”珍補充道,回到食品儲藏室去找另一份零食。我的頭痛在逐漸減輕,讓更多有意識的大腦騰出來處理問題。
我們可以這樣做。重新融入這個世界。在一段時間內,要準確地記住七年前的我們是誰,會很棘手。我們的旅行沒有明顯的痕跡,但有很多小事我們必須小心。據我所知,我的身體和我們離開的那天晚上一模一樣——平淡無奇。我感覺自己變得如此虛弱和渺小,我練就的肌肉一夜之間消失了。儘管如此,我仍然記得我所接受的所有訓練,記得我流血犧牲的每一場戰鬥。如果我一定要打架,我也能控制住自己。
不過我沒跟人打架。在我們離開之前,我從來沒有參加過搏擊俱樂部,而且我現在也絕對沒有打算開一個搏擊俱樂部。
“遞給我一些餅乾,好嗎?”我問。珍把盒子扔給我,我翻了翻。她是對的。我也同樣想念巧克力。那盒便宜的餅乾嚐起來像天堂。我吃了三分之一,每吃一口都覺得很餓。
珍倒了兩杯牛奶,沒人請她就端了過來。與她以自我為中心的喋喋不休的名聲相比,我認識的珍幾乎是相反的。她有驚人的洞察力,只是不總是付諸行動。我們默默地吃著,細細品嚐著零食。珍不停地環視著房間,好像她以前從未見過它一樣,注意著每一個細節。
“那麼,”她開始說,吃完了最後一塊餅乾。
我點了點頭。“你說得對,我們應該多買一些。”
“有更緊急的事要談,馬特。”
我嘆了口氣,聽天由命。現在說出來總比以後好,我想——但是珍腦子裡想的不是上週發生的事,而是別的事情。
“這是真的嗎?”
“是的。”
“你怎麼能肯定呢?”她問,眼睛斜視著他。“那我們在赫爾西瓦爾看到那些幻象的時候呢?”
“你還記得我的約定嗎?”
“Sel
ou。”
“那你和我一樣清楚,這是真的。”
珍點點頭。“好吧,是的。看來那個老女沒撒謊。”
“我肯定你想說的是女巫。”
“你不像我這麼瞭解她,”珍笑著回答。“那麼……我們到家了。”她臉上充滿了憂鬱的神情。“……永遠。”
我不敢反駁她。幸運的是,我沒有回答,因為珍從椅子上跳起來,衝到廚房的另一邊。我轉過身,迷惑不解,看到家裡的電話亮了起來,馬上就要響了。就在鈴聲即將打破寧靜的時候,珍拿起了手機。
“這是卡爾。”
這是另一個不受歡迎的發展。我鼓起勇氣準備對抗。“你能開擴音嗎?”
“好的,等一下。”珍擺弄著手機。“廢話。我不記得是怎麼回事了。”
“什麼?”
“有段時間沒見了,好嗎?”她把它舉到耳邊。“嘿。是的,卡爾,是我。堅持下去。閉嘴。我要怎麼開擴音?...按下……好的,是的。”她摸索著按了幾個按鈕,電話喇叭發出的微弱的白噪音充滿了廚房。珍把電話放在桌上。“馬特也在這裡。”
卡爾的聲音從揚聲器裡傳出來,非常低沉。他儘量避免發出太大的聲音,以免吵醒他喜怒無常的父親。“我們還活著。”
“不是吧,卡爾,”珍說。“想變得深刻嗎?”
“閉嘴。”透過電話,我幾乎可以聽到他的臉變紅了。“馬特,你在嗎?”
“我在這裡。”恐懼充滿了我的整個頭腦,就像一座大壩突然決口一樣。我很清楚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你們倆有布萊克的訊息嗎?”
珍看著我,表情嚴肅。她在等我回答。
我慢慢地搖了搖頭。“卡爾……”我開口了。
”等等。聽我說完。我們沒變,對吧?所以,“
一絲希望。我不敢考慮。我擔心它會長成什麼樣子,擔心它很快就會被撲滅。我必須儘快控制局面。
“你給他打電話了嗎?”
“他沒有手機。我給他家打過一次電話,但沒人接。我不想再試了。我不想吵醒任何人。”卡爾是對的。布萊克的父母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對夫妻,每次我去他們家玩的時候,我都很嫉妒他們家——但他爸爸絕對不會接受凌晨兩點被吵醒。
“那我們現在就只能這麼做了。”
“可是——”卡爾的聲音稍稍提高了一點,越來越響了。
“卡爾,”我尖銳地打斷他。“記住你在哪裡。你是十八歲。今天是上學的晚上,你爸爸在走廊那頭睡覺。”我儘量讓自己的聲音平靜下來。就像以前很多次一樣,它成功了。卡爾接著說話時,聲音低沉而壓抑。
“那我們該怎麼辦?”
“我們去上學。明天午餐時見,我們一直都是這樣。珍,你過來和我們坐在一起。”
珍點點頭。“好吧。薩拉一頓午餐沒有我也能活下去。”
“很好。卡爾?”
“是嗎?”
“Cy
aveil不存在。”
一陣沉默。我等待著,希望卡爾能理解並毫不猶豫地跟著我。只有一個辦法能讓我們度過難關而不被關進精神病院。我們必須重新融入,就好像我們從未離開過一樣。絕對不要告訴任何人。我能做到。在一些人的幫助下,珍可能也能做到這一點——但卡爾的變化比我大得多,而且方向相反。我已經準備好迎接這樣的挑戰了。新的卡爾?如果他的劍還在,我不確定。
他終於回答了。“明白了。”
我呼了一口氣,我沒有意識到我一直在憋著。珍注意到了,好奇地看著我。她什麼也沒說,把卡爾留在黑暗中。
“好吧。那我們明天見,卡爾。”
“明天。”卡爾承認。“嗨,珍。你還在嗎?”
“多夫?”珍俯身接聽電話。
“我知道,我應該得到所有的一切。”Syldaesevale
da,現在怎麼樣?”
“…當然,卡爾。”珍看起來有點尷尬,但很快就消失了。“會做”。
“好吧。晚上,夥計們。”電話咔噠一聲結束通話了。珍放下手機時,我仔細觀察她的反應。
“那是怎麼回事?”我問。我對卡爾說的話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我從來沒有像他那樣學過這種語言,只學了一些有用的短語(和一些侮辱),當然,我們兩個都沒有接近珍。
“什麼?一個男人就不能既友好又關心我嗎?”簡回答說。
“哦,好吧,忘了我的要求吧。”確實有些事,但珍說得很清楚,我不需要知道。只要不影響我們,那就是她的事。
“那麼……我們就回學校了,是嗎?”珍為我改變了話題,我感激地跳了起來。
“是的。正常點就好。你從來都不是。”
珍打了我的肩膀作為回應。“你可以做得更好。”
我笑了。“給我幾天時間。我會把所有的壞笑話都帶回來。”
Je
咧嘴一笑。我們已經感覺回到了正常。再多推幾下,也許我們就能完全滑向完美的世俗。“那麼,你明天晚餐想吃什麼?”
“我不知道。你想吃什麼?”
我聳了聳肩。“我們為什麼不放學後去雜貨店,見機行事呢?”你想要什麼我們都能買到。”
“哦。我可能會濫用它。”珍的臉變得調皮起來,但我說的是真心話。
“隨便你怎麼罵。這是一個特殊的場合。”
“壞笑話又回來的那一天?”
我又笑了。它讓人感到溫暖和安慰,就像太陽從黑暗中升起。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都沒有什麼可笑的了。“當然,就這麼辦吧。”
“你們兩個到底在幹什麼?”走廊裡傳來一個模糊的聲音,接著是前門咔噠一聲關上了。我們的母親終於走了進來,她的臉似乎因為疲憊而融化了。她的眼睛深陷,昏昏欲睡,身子靠在牆上。她把包掉在地板上。
“媽媽!”珍從座位上跳起來,衝了過來,緊緊地抱住她。我呆在原地,看著他們倆——但事實上,我和珍在那一刻感受到了同樣的快樂。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擁抱她,但現在一切都不同了。
“發生什麼事了?”
“沒什麼,媽媽,”珍回答道。她的臉縮了回去,我看到她眼中湧出了淚水。“我很高興見到你。”
“發生什麼事了嗎?”媽媽睜大了眼睛,變得警覺而熟練。儘管她很累,但只要想到女兒可能出了什麼問題,她就活了過來。這是我現在在我們三個人身上發現的一個特徵,腎上腺素激增和我們都掌握的高度意識狀態。媽媽,就像我們倆現在一樣,可以準備好面對任何事情,即使是在崩潰的邊緣。
“什麼也沒發生,媽媽,”我回答。“我們只是在等你回家。我睡不著。”
她皺起眉頭,但在我們倆的安慰下,她的疲勞開始被腎上腺素所取代。她的眼睛又垂了下來。“好吧,馬修。既然你這麼說。”
“我們很好。我想大家都該睡覺了。”
“來吧,媽媽,”珍補充道。“我扶你上樓。”
“謝謝你,珍妮。”我忘了,七年前珍還叫珍妮。她早就決定她討厭它了。當珍半抱著母親回到大廳時,她轉過身來,痛苦地看了我一眼。我咧嘴笑了笑。
“晚安,珍妮。”我喊道。她翻了個白眼,當他們開始爬樓梯時,她轉過身去。
吃完零食後,我收拾了一下,把牛奶收起來,把餅乾的空盒子扔了。
我其實很期待明天的學校生活,儘管在我們離開之前這聽起來很瘋狂。畢竟,有些朋友我已經近十年沒說過話了。重新上課會有點困難。我很難記住他們在哪個房間,或者我的儲物櫃在哪裡。我必須相信我的身體記憶會指引我找到正確的位置。
我能做到。我必須這麼做。唯一能讓我的生活重回正軌的方法就是沒人知道發生了什麼。塞拉維爾已經過去了,如果我能幫助它,它就會留在那裡。直到永遠。
當我關燈回到房間時,我看到珍的燈也熄滅了。我關上門,記住這次要避免咔噠聲,爬回床上。疲憊又來了。我幾乎立刻就開始迷迷糊糊地睡著了,但一段揮之不去的記憶又浮出水面,讓我一直醒著,回憶著後果。
在我們約定之後,女巫告訴了我一個秘密。一些我一直深藏在靈魂深處,不敢向任何人透露的東西。她告訴我怎麼回塞拉維爾。
我以我的生命發誓,如果我有辦法,我絕不讓我們任何人再看到那片悲慘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