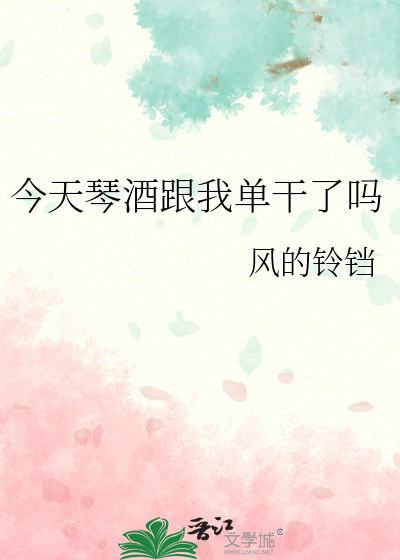第九章-珍
精甚細膩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喂?”
“波特曼,我是克拉克。可能會有所發現。”
“去吧。”
他和他最好的朋友之間還有一個聊天視窗。他們週二晚上在一起。”
“細節?”
“不多。只說他會在晚上9點左右被接走。”
“撿起來嗎?卡爾沒有駕照。或者一輛車。”
“所以這裡有第三方。”
“再和他媽媽談談。有車的朋友。”
“…我不確定你是否還會來,”薩拉尷尬地說,前門半開著。
“我當然來了,”我高興地說。“今天是星期四,不是嗎?”
“是的,但是——”
“但是什麼。”我給了她一個我能做到的最好的歪斜笑容。“你要讓我在外面站一整天嗎?”
我就在薩拉的門外,在一條石徑的盡頭,小徑兩旁掛滿了小燈籠和鮮花,還有——不是開玩笑的——草坪邊上的白色尖樁籬笆。可能是一幅畫。在樹林裡度過了一個漫長的下午後,我終於鼓起勇氣回到了文明世界。我很幸運那天是星期四;換做其他日子,我可能還在外面擔心得癱瘓。
但那是星期四。星期四在薩拉家吃晚飯。我從沒錯過週四在莎拉家的聚會。
我花了很長時間才從和卡爾的談話中恢復過來。我花了好幾個小時用一根棍子戳著地面,在埃託林語中找出關於雷尼爾·塞爾曼(Rey
i
Cellma
)的長篇大論和越來越難以理解的謾罵,以及對他的追隨者的難以置信的具體侮辱。真的是沒用的東西,因為我已經無能為力了,但這讓我感覺好多了。在泥土裡抓著艾託琳,是我回來後允許自己懷舊的感覺。我像一個溺水的女人一樣抓住了這些身份的線索,把自己從絕望中拉了出來。
該死,它起作用了。我在這裡,我還活著,我渴望和我最好的朋友一起出去玩。
薩拉終於完全開啟了門,但仍然很困惑。
“有人在家嗎?”我問,從她身邊走過,把我的鞋子踢到樓梯旁整潔的一堆裡。
“媽媽在後面。”薩拉輕輕地關上了門。我環顧四周,回憶起那所房子的樣子。
樓梯牆上掛滿了他們全家的照片——薩拉和她的父母。真正的,專業的東西,每一個。適當的照明和框架等等。她的父親在計算機行業工作,是一名無足輕重的工程師。這在我們這一帶很常見,但他太高階了。他們很有錢,但他們不怎麼炫耀。他開一輛普通的車,他妻子也是,他們的房子也不比我們的大多少。從外面看,這裡整潔整潔,但很中產階級。
在裡面?大量的小發明和小玩意。我不能告訴你他們房子裡一半的東西是做什麼的,但我知道它們都很貴。她爸爸很喜歡他的玩具。
一隻手碰了碰我的肩膀。
儘管發生了這一切,儘管我清楚地知道她是誰,她對我意味著什麼,我還是退縮了。我猛地舉起手,把她的手打飛了。
我轉過身,準備道歉,但她的表情是……滿意?
“你還在躲,”她提示道。
“薩拉,你看,”我正要開口,但她只是搖了搖頭。她拉著我的手,一步兩步把我拖上樓梯。
不一會兒,我們就進了薩拉的房間,門關得緊緊的。這個房間我記得很清楚。薩拉的床,我感覺過的最舒服的床,塞在角落裡。牆上貼滿了海報和圖畫(有些是我畫的,更好的是她畫的),還有一個裝滿衣服的衣櫥,比我以前有過的多得多。在另一個角落裡,靠近窗戶的地方,有一張寬桌子,上面有一排螢幕(三個,數一數),還有揚聲器、鍵盤,以及作為技術人員需要的一切東西。
她的電腦,可能比我擁有的所有東西加起來都貴(我從來沒有問過——我也不認為我真的想要答案……)坐在下面,電線從各個方向延伸開來。床邊的書架上擺滿了偉大的小說(我的私人借閱圖書館)。它的縫隙可能是我現在在家的書),“我的”膝上型電腦放在上面,可能是我上次來這裡時把它放在那裡的。
莎拉讓我用的。她說那是我的,並保證沒有我的允許,任何人都不能看或進入它。連她都沒有。即便如此,我也沒有把它帶回家。我想我不想讓媽媽因為沒錢給我買一個而感到內疚。
莎拉在我們身後關上了門,然後撲通一聲坐在她的椅子上。我在她對面的床上佔了我平時的位置。有那麼一會兒,我們倆都沉默不語。
我侷促不安,四處張望,避開她的目光。我不想先說。我不確定她會提出什麼,或者她聽到了什麼,或者發現了什麼。我想讓她主動,這樣我就能聰明點。馬特關於信任的話在我腦海中迴響。這一點,再加上我個人的背叛經歷,意味著我非常不願意向任何人敞開心扉。莎拉。
但她不會因此而放棄的。
“你知道,人們話很多……”薩拉非常正式地說。就像她要發表演講一樣。
“什麼?”我天真地問。
“去他的,”她厲聲說。“第二節課後到底發生了什麼?”
“你得說得更具體些……”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拖延。顯然她已經知道了。
“我聽說你輕而易舉地拿下了一名大學橄欖球隊隊員。把他直接扔進了儲物櫃。”
“哦。是的,我做到了。”
“珍,”薩拉說,她的聲音異常尖銳。“上次我記得,你害怕打一個過於激進的調情者。現在你打運動員是為了好玩?”
“不是為了好玩,”我趕緊說。“絕對不是為了好玩。”
“那又怎樣?”薩拉聽起來很擔心,這讓我感覺更糟了。“他對你做什麼了嗎?”
“沒有。什麼都沒有。這是個意外。”
“這不是意外,”她說,眼睛眯了起來。“天哪,珍,這是怎麼回事?”你這幾天都很瘋狂,而且不只是你一個人。馬特突然變得超級自信和外向,這很好,但仍然很奇怪。現在那個叫卡爾的傢伙,你突然跟他成了超級好朋友,儘管我以前從來沒聽說過他?”
我慢慢地點了點頭,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卡爾做了什麼?天啊!
這句話的意思是:“嗯,卡爾——一個非常安靜的傢伙,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在我們班——突然在APUSH的中途把老師罵了一頓。不停地說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薩拉惱怒地搖了搖頭。“珍,你們三個有點不對勁。很明顯。那麼……告訴我吧?”
“我不能,”我喃喃地說,我的目光迅速移開了。我說這話的時候不敢看她。
薩拉站起來,跪在我面前。她的手緊緊地抓住我的手,拼命地抓著。
“請珍。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只是想幫忙。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她的眼睛閃閃發光。她看起來好像要哭了。我只需要說話就能阻止她。
哦,星星,我想。我想讓她知道一切,不用我親自告訴她。跳過所有的麻煩,直接做回最好的朋友。
為什麼不呢?我腦海裡傳來一個小小的聲音。這是莎拉。如果這世上除了馬特還有一個人能知道我的秘密,那就是她了。
我能感覺到我的整個身體鋒利到一個點,好像我要起飛進入衝刺。當我轉身面對她時,感覺整個世界都在顫抖。空氣中充滿了期待,足以讓時間停止。
“我去了另一個世界。”
薩拉的眼睛眨了眨。他們又眨了眨眼睛。
我沒再說什麼。我只是看著。等待著。
她會認為我瘋了嗎?她會相信我嗎?
我想讓她覺得我瘋了嗎?也許我想發瘋。想象出這整個瘋狂的事情。
我不敢肯定。我只知道我想要我最好的朋友再次站在我這邊,與我同甘共苦,我們倆對抗整個宇宙。
“…再跟我說一遍。”她最後說。我不知道她是在諷刺還是認真。她的臉看起來很嚴肅。有點懷疑,但絕對不會生氣或被逗樂。我決定隨波逐流。我信任她。
“星期二晚上。我們,呃,我,馬特和卡爾,我們都……有主了。對另一個……哎呀,我想不出這個詞來。”
“地球?”莎拉猜。“維度?”
“維度,是的。”我點了點頭。“一個叫塞拉維爾的地方。”
“像森林一樣?”薩拉的聲音又有點遲疑了。她向後靠在地板上,靠在書桌上。她的水瓶就在旁邊,像往常一樣,她深深地喝了一口,仍然仔細地看著我。
“就是在那兒發生的。”我回答,又點了點頭。“那天晚上我們去了森林。我們四個人找到了一個——”
“等等,你們四個?”莎拉打斷。我情不自禁地嚥了一聲。“……珍?”
我不能把他排除在外,但我肯定還不能談論這件事。總有一天,我在腦海裡答應過她。我告訴你,我發誓。“我很抱歉。你認識布萊克·斯瓦瑟姆嗎?”
“不。”
“他是馬特和卡爾的朋友。不錯的小夥子。有點傻,但真的很好。”
“他也和你一起去了,”她總結道。
“……是的。”
“那麼他藏在哪兒呢?”我覺得我現在必須去見他,因為這有多瘋狂。”
我低頭看了看自己的腳,堅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腳趾上,一陣風吹進了我的耳朵。“他沒能回來。”我喃喃地說。違背了我的意志,違背了我身體裡的每一根神經對我叫喊著要我避開這場鬧劇,保持冷靜——我的眼淚湧了出來。
“哦……哦,上帝。”
薩拉立刻站了起來,來到我身邊。即使在我現在的狀態下,即使在這個地方,該死的,我仍然有一種本能,想要逃避突然出現的身體,但我抑制住了它。我不知道我是怎麼做到的,但我永遠感激那個決定在那一刻給予我精神勇氣的明星——讓莎拉照顧我一分鐘。
她伸出一隻胳膊摟住我的肩膀,我本能地把頭靠在她的肩膀上,淚如泉湧。這是我回來後的第一次——也是在那之前很長很長一段時間裡的第一次——有人真的看到我哭了。
是在說布萊克嗎?不,雖然那很令人心碎。
其實比這更簡單。薩拉——不管她現在在想什麼——看到了我的表情,毫不猶豫地跳了起來,試圖安慰我。
你知道有這樣一個朋友是什麼感覺嗎?一個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會站在你這邊的人?我不在的時候,我最想念她了。比淋浴、普通衣服、微波爐、巧克力蛋糕或其他任何東西更讓我想念:我想念我最好的朋友。
我又坐了起來,擦了擦眼睛。薩拉找到一個紙巾盒,遞給我一個。
“範南,”我哽咽著說。
“不用擔心,”她笑著說。“我猜這句話的意思是‘謝謝’。”
“班級第一名。”
“那麼你現在會說另一種語言了?”
我點了點頭。“Etoli
e。西爾凡達人的語言。”
“聽起來很魔幻。”
“好吧,是的,他們基本上是精靈。我的意思是,還有比這更多的東西,但是,是的,精靈。”
薩拉揚起眉毛。“精靈?”
“嗯,Sylves。叫他們精靈有點種族歧視。莎拉,那完全是幻想世界。精靈和矮人什麼的。不,我曾經遇到過一條龍。”
“…你到底是怎麼遇到龍的?”
“非常非常小心。”我笑了。“它們實際上並沒有那麼糟糕。不管怎麼說,那個不是。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它們早就滅絕了。”
“稍等。”薩拉把頭歪向一邊。“你說你星期二晚上走的。——“多長時間
“七年”。
說到一半,薩拉的嘴似乎張了起來。她花了一段時間才恢復過來,而我只是盯著角落裡籃子裡的一堆毛絨玩具。“…七年?她低聲說,不敢相信。
“我想是的。Likavsila
。”
“你看起來不像23歲,”她說,聲音裡又帶著懷疑。
“我確實覺得自己23歲了。”我抱怨道。“被強行塞回我16歲的身體真的,真的很糟糕,相信我。一個西拉內夫和一年不完全一樣,所以可能會有一點偏差。另外,當我到那裡的時候,我真的沒有任何方法來記錄時間。我真的不知道在特特瓦倫找到我之前,我在這個國家迷路了多久。”
“所以你回來了,沒有時間過去。納尼亞。你把自己的幻想世界混在一起了。”她笑了。
“別開玩笑了,”我辯解道。“我想認真一點。”
“我知道,”她說,又回到了沉思和放鬆的狀態。“只是……太多了,你知道嗎?”我正在迎頭趕上。”
“…你相信我,對吧?”我很緊張地說。我不知道如果她拒絕了我該怎麼辦。如果她不相信我,我想我活不下去了。但是,莎拉不是那種相信別人的話的人。她總是想要證據。這是家族遺傳,遺傳在她的血液裡。我不知道她對這一切會有什麼反應,因為這一切太……奇怪了。
“是這樣的,”薩拉故意說。“要麼你一夜之間突然有了豐富的想象力——”
“Vack鬥。”
-你在騙我,你從來沒騙過我。或者你瘋了,這很合理,但你看起來不像。主要是。”她聳聳肩。“所以,我差不多隻能相信你了。”她把頭髮向後甩開,然後直視著我。“聽起來不錯?”
我本可以吻她的。“謝謝你。”我說,一股溫暖的光芒傳遍了我全身的每根血管。
“好的,”薩拉興奮地說。“現在,你來解釋一下,一個連續兩年法語基本不及格的女孩,怎麼會突然掌握了另一門語言。”
我聳了聳肩。“我和西爾夫一家住了很多年。他們誰也不會說一句英語。再加上一點魔法,我很快就學會了Etoli
e。不得不這麼做。”
“…魔術?”薩拉的眼睛閃閃發光。現在她真的感興趣了。
我也是,我要向她,向我最親愛的朋友,解釋我的整個世界。我總是喜歡講故事,即使我不太擅長講故事。突然間,我有了一個偉大的、真實的故事要講,還有一個完美的傾訴物件。
“魔法。Etola。”
“細節。現在。”薩拉說得那麼激烈,我嚇了一跳。但我感覺到了,就像她一樣急切。渴望,渴望真正的幻想。一個我真正經歷過的。
“如果你……呃。”我皺起了眉頭。“我無法用這種語言來表達。”
薩拉顯得很同情。“你真的忘了英語嗎?”
“我沒有忘記,”我有點氣憤地說,“但是我很長時間都沒有說英語……我大約一年前才重新開始說英語。”當我開始——”我停頓了一下,尋找合適的詞。”解釋。為了條約。”
“…‘為條約作口譯’,”薩拉難以置信地重複道。“好吧,這不公平,你剛剛讓我多問了50個問題。”
“嗯,我是他們唯一會說英語的人。我是第一個與人類談判的陽光族成員。他們甚至還編了一個特別的標題來紀念它。”
“好吧,現在你只是在吹牛。”
“是的,”我笑著說。“不是開玩笑,他們用我的名字給這個職位命名。人類的大使被稱為西拉詹。即使是接替我的那個人,她也是新的希拉珍。”
莎拉咧嘴一笑。“所以你不朽了。幹得好。至少這解釋了你奇怪的口音。”
我突然感到很難為情。“這真的很奇怪嗎?”
“不。好吧,是的,但不是很奇怪。”薩拉試圖給我一個安慰的微笑。“我喜歡它。別弄丟了。”
“Sel
ou。”從那以後,我不再試圖糾正它,這讓我的喉嚨鬆了一口氣。
“等等,精靈——呃,是西爾弗斯——不是長生不老的嗎?”
我嘆了口氣。我知道這是遲早的事,儘管我討厭去想它。“不,但每個人都這麼認為。不過,多虧了etola,它們確實活了幾百年。”
莎拉太精明瞭,不可能不發現這種可能性。“所以如果這是魔法,你和他們住在一起,可以接觸到它……你也會活那麼久嗎?”
我猶豫了一下。“…我平靜地說。“每次我做這個儀式,我都能感覺到。你知道,治癒我。”
“但是,當你昨天試過的時候……”薩拉慢慢地說下去,把腦子裡的點點滴滴串聯起來。“哦。”
“是的。”
“我很抱歉,珍,”她喃喃地說。
“S'okay。”說實話,我還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感覺。我花了很長時間才適應這樣的想法:活得比正常年齡長一百多年,甚至更長,而且一直保持年輕和健康。突然被奪走是相當令人不安的。而且,我現在得更小心地照顧自己了。
我真的很討厭早上刷牙,或者看我吃什麼,或者處理月經。別讓我說其他的了。有時候,做人真的很糟糕。
“等等,那麼你會施魔法了?”我是說埃托拉?”薩拉急切的語氣又回來了。
當她說話的時候,她的貓從壁櫥裡探出頭來,它一直懶洋洋地躺在一堆塞在裡面的衣服上。這是他慣常的地方,也是薩拉唯一留在地板上的東西。除此之外,她的房間一塵不染。它慢吞吞地走過來,跳上了床,很快就爬到了我的腿上。我微笑著撫摸著它,得到的回報是一聲滿意的咕嚕聲。一會兒他又打起盹來了。
“不——不,”薩拉警告說,“他不會放過你的。”
“我可以,”我漫不經心地說。“至少有一點。”
“哦,有點。對的。”
我咧嘴笑了笑。“好吧,我表現得很好。Tethevalle
說我掌握的速度比他教過的任何人都快,甚至比一些正牌高手還好。在某些地方,他們說我是整個森林裡最好的。”
“而且很謙虛,”她揶揄道。
我笑了。“他們認為這是因為我是人類。我不曉得。他們比我堅持的時間要長得多。我比他們快多了。”她的貓在我腿上動來動去,促使我不停地撫摸。
“那你擅長什麼呢?”
我皺起眉頭,低頭看了看那隻貓。“他叫什麼名字來著?”
”標準。爸爸給他起的名字。用鍵盤的名字給貓命名真是太遜了,不過無所謂了。”我看得出來,我應該已經知道了,但薩拉儘可能友好地解釋了這一點。聽起來一點也不生氣。她只是又顯得憂心忡忡。“你沒事吧?”
“是的。”我清了清嗓子。當我繼續說下去時,我感到有點壓抑。“我最擅長射擊。這很有趣,把它扔來扔去,把它分開再組合,改變顏色,製造煙花和爆炸等等。一旦我學習、練習和冥想足夠多,我就能真正進入火的境界。我甚至可以白手起家。他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
“Etole
dei?”薩拉問。我故意對她的發音皺眉,儘管它真的很糟糕。她從桌上拿起一個壓力球朝我扔去。我笑著躲開了它。“但是當回事。”
“真的很難形容,”我誠實地說。“我猜,這就像是……對某件事的真正瞭解?”在你真正瞭解某樣東西之前,你不能對它或用它做任何事情。”
“嗯,”薩拉說,她的眼睛冷靜地分析著,就像每當她在解決一些程式設計問題時一樣。當然,冷靜的分析對魔法並沒有什麼幫助,所以過了一會兒,她又回來了,一副沮喪的樣子。“我希望看到更具體的東西。”
“對不起。我真的無法用英語很好地解釋。”
“該死的精靈。”薩拉語調凝重地說。我抓起球扔回給她,用釘子釘在她的胸口。“哎喲。”
“真的疼嗎?”我擔心地問。我沒有太注意我扔得有多用力。
“不,”她說,意識到我是認真的。她捏了一下球,想了一會兒。“…我忍不住覺得這裡有黑暗的一面。”
我又把目光移開。“是的,”我對著牆說。
“看,”她說。我看了看。她的眼睛顯得那麼友好和溫暖。自從我在坎迪爾外的球場上離開奈弗林後,我還沒見過那樣的眼睛,他滿身是血,但仍然準備給我一個擁抱,告訴我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如果你不想說——”
“我做的。”我必須這麼做。這是唯一能讓我擺脫內心痛苦的方法。“他們對我的火技如此滿意是有原因的。”
“…我敢打賭,這也與你幫助翻譯的那些條約有關,”她補充道。她的聲音變得單薄而緊張。“有一場戰爭,不是嗎?”
我點了點頭。
“你在裡面打過仗嗎?”
我又點了點頭。
薩拉沒有說話。她仔細地打量著我。沉默持續著,一刻比一刻更尷尬。
她會怎麼看我?我說不上來。即使作為我最好的朋友,對我做過的那些事?我做了為了生存必須做的事,對吧?這就是我每天晚上睡覺前對自己說的話,每次這些記憶浮現在我的腦海裡。
雖然我沒睡著。一個完整的晚上的睡眠是正常的人。我不正常,而且我肯定沒睡過整晚。白天斷斷續續的打盹,這就是我現在的生活。甚至在前一天的15個小時裡,我也充滿了恐慌的時刻,我醒來時,指關節發白,準備向一個機會主義的牢房同伴砍去,而這個同伴實際上並不在那裡。睡眠對我來說並不是放鬆,這是一種可怕的狀態,是我最脆弱的時候。
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請,莎拉。現在不要拋棄我。
我在腦海裡瘋狂地祈禱,向所有離我靈魂最近的星星祈禱,希望她能接受我變成的樣子。如果你在這個星球上還能聽到我的聲音,把我的智慧傳給莎拉。讓她知道該怎麼做,因為我顯然已經出局了。
“看,”她又開始說。我的目光與她的目光相望,絕望地希望著,但我強迫自己的臉恢復出一種被動的表情。我現在不能讓她看到我的情緒。“我不可能理解你經歷了什麼,但我可以試著傾聽。盡你所能。任何你想說的,隨時都可以。沒事吧?”
哦,莎拉。你怎麼可能存在。你怎麼會這麼完美,是什麼仁慈的命運把你送到我身邊的?我想哭,想笑,想笑。我想跳舞,我想唱歌,我想擁抱她,我想蜷縮在她房間的角落裡,在她擁抱我的時候哭得淚流滿面。我想為她傾吐我的靈魂,承認我所做過的每一件壞事,我殺死的男人和女人,我辜負的朋友,我違反的法律,我愛過卻失去的人,以及我所接受的全部孤獨的生活。我想讓她看到我,告訴我一切都好。
那些話我都沒說。這些事我都沒做。
我只是等著,盯著薩拉,那警惕而孤獨的眼睛永遠地盯著我的臉。
“謝謝你。”我微笑著說。她也笑了,但她也帶著一種悲傷,這是我從未在她的表情中看到過的。還是它一直都在那裡,而我卻從來沒有理解過?從未意識到它的本質?
我不知道,但那一刻我能看出來。我不是房間裡唯一一個有秘密的人。
***
薩拉的媽媽叫我們去吃晚飯。我們又開始交談了,謝天謝地,我們回到了更快樂、更輕鬆的話題上。我試著如實而徹底地回答。薩拉喜歡奇幻小說,但即便如此,我還是低估了她對我所有冒險經歷的渴望。
事實上,告訴她一切真的很有趣。她太著迷了。我本可以談論天氣,她可能還是會津津有味。她想知道每一個細節,我很樂意分享。主要是關於西爾弗一家和他們如何收養我的故事,但也有關於整個世界的故事,關於不同的人和他們的文化(不管怎麼說,就我所知,西爾弗斯並沒有真正出去),當然,還有關於埃托拉和埃託林的故事。
儘管名字不同,但它們之間並沒有真正的聯絡。我的意思是,說出與你想要演奏的任何一種etola相關的短語可能會幫助你集中注意力,但在真正的精通程度上,大聲說出它被認為是業餘的。只要你清楚地知道你要做什麼,在世界的任何意義上,你都不需要說什麼。
不過,手勢是非常必要的。正如薩拉注意到的那樣,在過去的幾天裡,無論是中午的儀式還是吃飯的儀式,我都表現得像一個非常困惑的啞劇演員。雖然有些etolev不需要手工,但大多數都需要,尤其是外部的東西。我不知道這是否只是另一種幫助集中注意力的方法,但如果沒有手勢或動作來引導etola,我從來沒有得到過任何好事。我的努力都以失敗告終。
我的手指被燒焦了很多很多次,直到我學會了如何精確地移動火焰。
對不起,我又走神了。這裡有一個更重要的故事要講,而不是我在玩弄火。
薩拉和我走下樓,像往常一樣談笑風生。她母親正在擺盤子準備晚飯。我聞到了披薩的味道,我很興奮。我還沒吃過披薩——好吧,現在你應該明白了。但當回事。披薩。有沒有比披薩更真實的東西?
“Shasii,selaval,”我們走進廚房時,Sa
a漫不經心地喊道。我咯咯地笑著用胳膊肘碰了碰她。
“那是什麼?”媽媽問,從烤箱裡抬起頭來。
“哦,沒什麼,”她非常嚴肅地說,和我一起忍住了笑。
我在她耳邊輕聲說:“我的女兒,我的女兒,我的女兒,卡爾。”不完全是這樣,她和卡爾都很糟糕。但我剛剛教了她臺詞;一分鐘後,她還是弄錯了。
“嗯?她大聲問道,但我只是天真地笑了笑作為回答。“哦,這種遊戲兩個人玩。你看êtes,你看我的臉,我的臉,我的臉。
“好好表現,薩拉,”她媽媽一邊抽出披薩一邊心不在焉地插嘴說。它是自制的,看起來絕對完美。這倒不是說我有什麼可以和最近的披薩相比的,但說真的,我對這個披薩垂涎不已。
她媽媽開始把它切成薄片,而我們則坐在餐桌上慣常的位置上。就在她給我們每人拿了一塊的時候,我聽到車庫的門開始滑開了。
這很不尋常,但也不是沒聽說過。我們吃飯的時候,她父親通常還沒有下班回家。他往往工作到很晚。當他在那裡的時候,我們的談話稍微平靜了一些,但他總是很有禮貌,問候我的家人,問我過得怎麼樣。他看起來是個不錯的人。是的,他有時有點冷,但他也非常疲憊,工作壓力很大。我不能責怪他一到家就不願意容忍兩個高中生,即便如此,他也總是表現得像個稱職的主人。
這一次,有點不對勁。我說不出是什麼。一些細節發生了變化。除了…我上週四來過,週一也來過莎拉媽媽的生日。就在三天前,感覺有些不一樣。當然除了我。
我環顧了一下房間。薩拉還在說今天在學校發生的事。她媽媽一邊點頭,一邊像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繼續著我們的談話……但我能看到。她開始小心翼翼地移動。她衡量著自己走的每一步,精心設計著每一個動作,既慎重又謹慎。
薩拉似乎也突然警惕起來。她非常專注地盯著她的盤子——她的空盤子,我應該指出來。她的手擺弄著叉子。當我的眼睛掃過去時,我可以看到她抱得有多緊。這很微妙,來了又去,但意圖很明顯。
就像箭射進了我的肚子。我是個白痴。我怎麼會錯過這一點呢?
他們一點也沒變。我終於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他們很害怕。
當通往車庫的門開啟時,一切變得更加清晰。
“歡迎回家,親愛的。”薩拉的媽媽喊道。很正常的。
她父親朝走廊那邊望去,看見我坐在桌子旁。他微笑著揮了揮手,把外套收起來。“晚上。聞起來真香,親愛的。”
“工作怎麼樣?”
“讓人筋疲力盡。我很高興回家了。”
“要喝點什麼嗎?”薩拉問,仍然盯著盤子。她的聲音非常隨意。
“謝謝你,薩拉,但我能拿到。你要什麼嗎?”
“可樂聽起來不錯。珍?”
明星們,他們都在演戲嗎?一直以來?當我意識到薩拉和她爸爸都在期待地看著我時,我喘不過氣來。我嚥了口氣,想清清嗓子。
“呃,我要根汁汽水嗎?”我尷尬地問。我應該按照劇本演嗎?我是個糟糕的演員。如果需要的話,我可以隱瞞,但我不擅長假裝正常。我都不知道什麼是正常了。
“哦,現在是珍了嗎?”她媽媽一邊問,一邊把一片披薩塞進我的盤子裡。她的手仍然緊握著披薩卷,那鋒利的銀色邊緣在陽光的照射下閃閃發光。
“是的。是時候做出改變了。”薩拉在桌子底下推了推我,試圖讓我集中注意力,但我仍然目不轉睛地盯著她握著叉子的手,就像一把匕首。“不再是珍妮了。”
“那太糟糕了。我喜歡珍妮這個名字。”
“好了,親愛的,這是她的名字。她可以用它做她喜歡做的事,”她的父親說。他對我眨了眨眼睛。“不再是街區裡的珍妮了。”
“上帝啊,爸爸。”薩拉翻了個白眼。“請不要試圖引用流行文化。過了。”
我對發生的事情感到非常困惑。我無法處理正在進行的荒謬矛盾的談話,以及房間裡每個人的身體反應。父親一開口,薩拉就又抓住了叉子。當他看向她的母親時,她似乎有點退縮——但當他看向我時,她的指關節變得蒼白,因為她抓住了披薩卷。
如果我沒有在幾乎完全相同的情況下,在他們的廚房裡吃過一百次這樣的晚餐,我會認為我們快要完蛋了。
只不過這裡是俄勒岡州的郊區,而不是小巷裡的酒館或破舊的地牢。在這裡打架就像一個傳送門開啟把我們都扔進另一個宇宙。
抱歉,不好意思。
整個晚餐過程都是這樣。就像他們在為我表演一樣。正常、幸福的家庭。他們會取笑對方的舊習慣,爭論政治,討論電影和電視節目。這一切是如此完美,如此普通,我發現自己伸手去拿刀,刀還藏在我背後的襯衫下襬下面,這是我唯一沒有告訴薩拉的一件事。
幕布什麼時候落下?
***
從來沒有。晚飯結束後,薩拉的媽媽收拾了一下,我徑直從後門走到院子裡去透透氣。薩拉離開了她的位置,過了一會兒也跟了上來。直到門關上了,我們走到拐角處,光線消失了,我才轉過身來面對她。
“那是多夫奈良瓦克嗎?”我問道,既困惑又生氣。
薩拉看上去也真的很困惑。“嗯?”
”。整個晚餐。你們所有人。”我很緊張。非常緊張。莎拉很幸運,我現在不能變出火來,否則鄰居們可能會叫消防員來。
“你在說什麼?”
我猜她決心要把戲演下去。我不知道該如何反應,該做什麼,該如何回應。我很想生她的氣,因為她對我隱瞞了這件事,但我怎麼能這麼做呢?在過去的幾天裡我一直瞞著她,這不會讓我成為一個超級偽君子嗎?
這次不一樣,我說服自己。這就是控制和恐懼。這種情況正在積極發生,而且顯然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
毫無徵兆地,我抓住莎拉襯衫的下襬,把它掀起來。不,我沒在想那些事。把你的思想從陰溝裡解放出來。我在找瘀傷。任何型別的標記。證據。
“嗯……”薩拉環顧四周,確保沒人看見我們。“嗯,這太奇怪了。”
在精神上,我同意了。她身上沒有受過虐待的痕跡。這一切都是我的想象嗎?那真的是非常正常的晚餐嗎?
我是不是完全瘋了?
“對不起,”我咕噥著說。我鬆手,退到房子的牆上。
“不用擔心。下次提醒我一聲好嗎?”薩拉看起來對整個情況出奇地坦然。
“對不起,”我重複了一遍,轉身要離開。
我還沒來得及走,薩拉就伸出手抓住了我的手。“嘿,沒事的,”她平靜地說。
我感到我的眼睛又溼潤了。我甚至不能和我最好的朋友的家人共度一個晚上,我的過去就會突然出現在我的腦海裡。我的本能幾乎讓我去攻擊莎拉的父親,在他自己的家裡,當著他家人的面。
我真的能像以前那樣住在這裡嗎?
那天晚上,我第二次哭了,但再也沒有任何快樂了。快樂是留給那些沒有主動失去理智的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