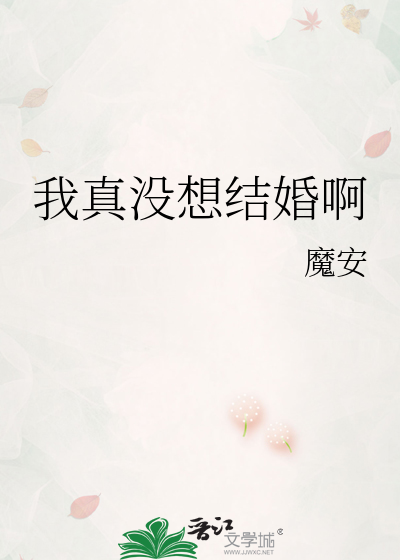酒釀番茄番茄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是,想來也快了。”
呂雉頷首,卻不見一絲喜色。
儘管老趙王張耳新逝不久,但子女為父母服喪三年、以及三日不食之類的喪禮,此時非但未入漢律,而且只有極少一批儒生在嚴格踐行。
先秦時期,社會上普遍實行的是“既葬,除服”的短喪,不是儒家推崇的事死如生,而是有些黃老意味的“生事死止”,以逝者下葬作為終點,讓生者繼續好好生活。
因此,漢初的“沒而喪”律法也順應民意,一切從簡,子女為父母、妻為夫居喪,只需服滿三十六日,即可除去喪服,恢復自己的日常生活。
為此,叔孫通曾好幾次藉故找過呂雉,吞吞吐吐地說自己打算向皇帝獻策,想將儒家經典《禮記》中所倡導的關於奔喪、居喪的行為規範納入法律,最起碼,在道德方面予以大力褒獎。
而皇后總是斬釘截鐵地勸他死了這條心,
“奉常啊,朝廷絕無推廣嚴苛喪法的道理,也斷不會將其立為儀表的,我勸你不要白白浪費時間。
儒家那一套喪儀我都知道,很是鄭重,可你們一會兒讓大家三兩日不許飲食,一會兒三年不許嫁娶,是不是見不得天下人過些舒服日子?
好不容易止了干戈,咱們先別折騰了,好嗎?”
說實話,戰亂近十年,滿目瘡痍,全國哪一戶人家沒有死傷?
值此百廢待興之際,若家家戶戶嚴守繁瑣的道德之禮,凡遇喪事,便動輒幾天不飲不食、幾年不嫁不娶的話,那心心念念盼著社會人口增殖的朝廷,簡直如同白日做夢了。
叔孫通是善於變通的大儒,想通了這一節,便也不再繼續於此事上糾纏。
“算下來,先景王張耳早已大殮,卻仍在停靈,尚未下葬。
依照皇帝的意思,是要擇個吉日出殯,其實也是在等朝中人事安排妥當,再大辦葬儀。”
“是,張蒼回來了,對匈奴的策略有個頭緒了,再加上燕王那邊……也快了,他的這一手棋,也到了不得不下的時候。”
呂雉嘆道,魯元與張敖的婚事,將作為劉季拉攏趙地的手段,與新趙王的冊封一併辦妥。
並且,對多疑的劉季而言,僅在趙國安插一個丞相張蒼,是遠遠不夠的。
***
幾日後,張敖奉詔入禁中覲見。
待踏入殿內才發覺,此次覲見,除他與皇帝、皇后之外,便只多了一個陳平坐在旁側。
張敖猜測,這是要商定自己尚公主的親事了,便搶先一步,伏地叩首,
“前幾日,陛下問與匈奴和親之事,臣心內彷徨,卻於倉促之間無言以對。
臣自歸去,寤寐思服,忐忑不安,只恨自己沒有為了魯元而與那劉敬力爭。
奪妻之仇,不共戴天,臣願替陛下出兵,蕩平匈奴。”
“和親只是劉敬的提議,我們並沒有應允,何來奪妻之仇?
你這孩子,快起來入座吧。”
劉季彷彿被張敖驟然之間所行的大禮嚇了一跳,不由笑道,
“今日找你前來,一來為私事,一來為國事。”
張敖只應聲是,上身微微前傾,姿態極為恭敬。
“先說私事吧。
你與魯元的親事,是我和張耳大哥定下來的,天子所諾,自是一言九鼎。
但當時我倆只有口頭之約,六禮中什麼納采、問名、納徵之步驟,一概都無,呵呵。”
劉季乾笑一聲,似乎對草創階段自己行事的不拘小節,甚為洋洋得意,
“眼下趁你人在洛陽,乾脆把請期與親迎一併做了,帶著新婦一道回邯鄲去罷。”
“臣自是無所不從,只是......若太過簡陋,怕委屈了公主。”張敖忙答。
“你有這份疼惜公主的心,自是好的。
你去請教請教叔孫通,儘管時間倉促,但由他來辦,相信也能符合體統。”
呂雉溫言對他說。
“對對,去問叔孫通,去問叔孫通。
接下來,咱們說國事。”
劉季擺擺手,實在懶得為家長裡短的瑣事操心似的。
他清清嗓子,飛速看了陳平一眼,又目光陰沉地盯著張敖,
“都說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可咱們對匈奴知之甚少,這一點極是不利。”
我們需在匈奴,在冒頓單于身邊,插進一些諜者。”
***
兵不厭詐,無論是作為緊鄰的龐大陌生帝國,還是最終難免決戰的宿敵對手,漢廷對於匈奴的瞭解和認知,永遠不嫌多:
大到他們的官僚架構、權力層級、兵力部署,小到每一帳的人口構成、五畜的每年產出;
還有他們王庭移動的方位,與放牧路線的規律,都需做到了如指掌,方能有的放矢地制定戰和策略。
因此,派去的諜者,不能是走馬觀花的巡遊商旅,而需要實實在在紮根大漠,與匈奴人同吃同住同牧,像一枚枚產自漢地的楔子,牢牢地釘死在草原。
更理想的情況下,這其中的一人或幾人,能成功打入匈奴的最高決策層,即匈奴王庭,洞悉他們的所想所為,以便向中土源源不絕地輸送情報。
顯而易見,這將是一項兇險無比的任務,而諜者的出路也只有三種:
或因暴露而被匈奴人用酷刑殘殺,或在草原捱到老死而等不到被啟用的那日;
抑或,在大決戰前發揮出他們潛伏的作用,並在最後一刻逃出生天。
對於使用間諜,劉季並不陌生,想當年,彭越的身邊、韓信的身邊,以至項羽的帳下,都不曾少了他的細作的幽暗身影。
此刻,已高居皇座的他,面無表情,在斑白頭髮的映襯下,像只已過壯時卻敏銳不減的獵鷹。
劉季語不遲疑,
“陳平,此事交由你負責。
你去選一批機敏善辯的熟手,有些武功底子的更好,把他們悄悄送到趙國,由張敖安排吧。”
他想了想,又道,
“這批人不必太多,至多三、四十名吧,練好後,儘快從趙國邊境,放到草原去。”
“要以什麼理由派去呢?”張敖領命,恭敬地問。
“這很簡單,你給他們隨便安插些罪名,偷盜、逃役什麼的,然後疏於看守,讓他們伺機越獄。
你們趙地與匈奴的邊境綿長,囚犯們鑽個空子,向北逃竄到草原去,也屬人之常情。”
劉季格外耐心,語重心長,似乎在對親生兒子諄諄教導。
坐在旁邊的呂雉,深情凝重地用心聆聽,然而她盯著屋頂藻井蓮花出神的眼神,卻暴露出心不在焉來。
劉季才不會如此大張旗鼓地派出密探,看來,重頭戲還在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