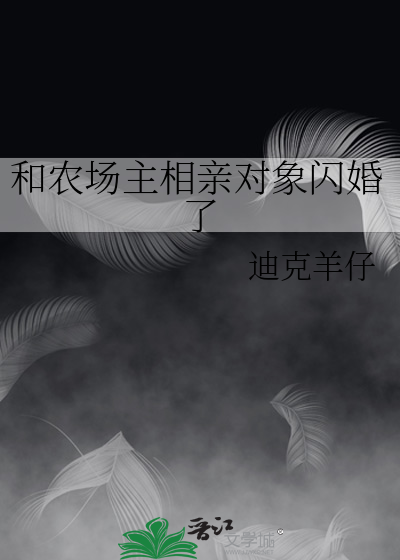梁躍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一》:初遇,悲情兒時
秋月春風,寒來暑往,他——姚林的兒子姚建,從小就沒有父母,與爺爺奶奶生活在溪澗崖畔,碧水青山,竹籬茅舍,每天在“雲端晚霞如醉,水邊蘆花若雪”的“清幽鎮”過著月輪浮沉,星影盪漾,蝶舞山崗,平靜而清幽的孤寂日子。
一個小孩,一個人玩,這種孤寂有誰能知?
他,在小鎮上與別的孩子一起玩,總會受欺負,每次看別的孩子有新玩具時,自己則會站在遠處看上幾眼,就獨自低頭走開。小鎮上有什麼活動時,他就一人流浪在溪澗,對著天空訴說心中無法向別人言出的“痛”。
小小年紀,這種痛有誰能知?
天地蕭索,寒風冷烈,在他十四歲那年,他為重病的奶奶上山採藥時,撿了一把木製的玩具劍,帶回家,不敢讓爺爺奶奶看見就隱藏起來,等到無人時再拿出來玩。
他隱藏木劍是因為在這“清幽鎮”,他們一家的名譽不好,鎮上的其他人都疏遠他們,還用一些不堪入耳的流言蜚語來低毀他們的名譽。他怕這劍讓人看見,小鎮其他人又會用一些“言語”來刺激他爺爺奶奶。
這一切為什麼?他不知道,只聽別人說與他父親有關。
可這天,玩劍時恰恰被幾個小夥伴看見。
“劍不是你的,拿來,你個小偷。”
聽到“小偷”一詞,不知是天生就對這種辱罵厭惡,還是對於這個詞的敏感,他放下劍,快步衝到罵他的小孩身邊,用手揪住這小孩的衣領,把對方按倒在地,帶著恨的拳頭隨之朝這小孩臉上打去。
“你才是小偷,你才是小偷,你……”他已被恨吞噬了自己,只知道把自己壓抑了好久的怨與恨全發洩在這拳頭上,那小孩臉上。
旁邊站著的另外兩個小孩被他的舉動嚇傻了眼,一溜煙,已不見身影此。
這一刻,他的眼裡只有火,而且越燒越旺,心裡充滿了前所未有的快感,拳頭盡情的揮灑。
他的命運隨之改寫,可他不後悔。
“喂,放手。”一個身材魁梧龐大,身穿肥大長衫的中年男子走近,抓著他的一支胳膊,用力一摔,他便到了兩三米以外的地方。
被這男子這麼用力一摔,他的胳膊已失去了知覺,無法再自如使喚,可他並沒有感覺到痛,只是兩眼呆看著中年男子搖晃著地上被他打暈過去的孩子。
“爸……”那孩子睜開眼,想用手站起來,可無力,他越想站起兩隻手越不聽話。中年男子見那孩子無力站起,慌了,抱著孩子朝小路盡頭飛奔去。
此時周圍已圍了很大一群人,但沒有一人過來扶他,他無力再站起,只能聽著這些人幸災樂禍地指著他談論道:
“這小孩怎麼這樣,他爸不檢點,他也這樣。”
“有其父必有其子,沒什麼奇怪的。”
“真是天意弄人,他也變成這樣,真是我們鎮的不幸。”
……
他看著周圍的人用著看怪物的眼神看著他,用手對他指指點點,還七嘴八舌的評論著他和他的父母,他此時心中除了恨什麼也不再有。
恨這些人,恨這個世界,恨他自己。
可再恨也無用,他知道自己的痛苦與快樂只有自己承擔,別人只會看著你哭,嫉妒你笑,不會因為你的痛而痛快樂而快樂。
他此時好想讓所有人能閉嘴,好想自己能站起來說明這一切,好想有自己的父母在身邊保護著自己。但這已不可能,他轉過頭,把所有人的嘴臉都看了一遍,他要記住這些人,記住這些看不起他的人的嘴臉。
他用右手捧著自己失去知覺的左手,端坐在地上,望著陰霾的天空中冷淡的白雲,眼球裡盡是血絲,眼淚欲奪眶而出,他呻吟著嚥了一口泡沫,仰著頭儘量不讓眼淚流下來。因為他知道這眼淚不能洗刷任何東西,自己有未來,還有夢,還有爺爺奶奶,還有爸爸媽媽的事……。
他不再想了,也無力再想了,他倒在了冰冷寒青的地上。
“你醒了,你看你一個人躺在那冰冷的地上,怎麼也沒人照顧你啊!要不是我爺爺,你……。”
“韻兒,說什麼啦!”端著藥問他走近的老人打斷了坐在他身旁並用兩隻水靈靈的大眼睛看著他的十一二歲的小姑娘的話。
“這是我爺爺,你就是他救回來的”,韻兒說看就朝老人跑去,向老人要他手中的藥碗。
“乖!這藥救是他的。”老人用手拍了一下這小女孩的頭,走到姚建身邊,坐在床頭,揭開他身上的被子,把藥碗放在旁邊的桌上,用左手摟起他的腰,將他扶起,右手伸到桌上,端起藥碗,湊到他嘴邊,說:“快把藥喝了,喝了身子就會好的,也不再痛了。”
“別怕,我們是好人。”見他不喝,鼓著圓圓的眼睛看著自己,老人再次放下手中的藥碗,摸著他的頭說:“你把藥喝了,你爺爺奶奶就會來看你,我認識你,也認識你爺爺奶奶,那日你倒在了地上,我採藥路過看見無人管你,就把你帶了回來,來快把藥喝了。”說完老人又伸手端起放在桌上的碗。
“你認識我爺爺奶奶,真的?”他注視著老人和韻兒,一幅不太相信的表情。
“你姓姚,小名建兒,你爺爺姚鎮中,你奶奶鍾彩雲,你……。”
“那麼,你知道我爸爸媽媽對嗎?他們叫什麼?他們現在在哪兒?”他急促的打斷了老人的話,充滿血絲的眼球露出一絲絲光亮,就像一盞枯燈遇到了燈油一樣。
從小到大,他爺爺奶奶從不告訴他父母的事,也不允許他問別人。他增試著問過,可每次爺爺奶奶總是轉移話題,有意瞞他一樣,而他在小鎮其他人的談論中,得知他父親是一個萬人厭惡的壞人。他不相信他父親是這些人言語中的壞人,他從小就想弄清他父親的事。這件事,是他心裡的一個結,一個改變了他一生一世的結。
老人看著他閃著淚光,無法讓人讀懂的眼神,不再說什麼,只是催促他趕快把藥喝下。
他接過老人手中的碗,猛灌而下,隨後把碗交給老人,用手一抹嘴巴,便央求老人:“我爸爸媽媽究竟是怎麼樣的人?他們現在在哪兒?我每次問爺爺奶奶他們都不說,你認識他們,你一定知道,你快告訴我呀!”
“你爸媽是好人,你身子弱,快躺下休息,我還要去為你準備治手的草藥。”老人說完,把他放倒在床上,鋪好被子,拿著碗轉身帶門走了出去。
“你告訴我,我爸媽究竟是怎麼樣的人啊?”他準備用手撐起身子,去追問老人,可此時門已關,老人的腳步聲也漸漸遠去,他只能躺在床上聽窗外寒風呼嘯,獨自忍受內心無法言語的痛。
“爺爺不告訴你,你就不要再問了。”小女孩看著他一幅急切和無奈的樣子,邊說邊幫他蓋好被子。
“你叫韻兒!”他看著讓人一看就喜歡上的韻兒,敷衍著。
“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我聽你爺爺叫你韻兒。”
“對,那是我的小名。”
“是你爸媽取的?”
“我叫姚建,爺爺奶奶叫我建兒!”想起爺爺奶奶,他自言自語道:“不知道爺爺奶奶現在怎麼樣了!他們不見我一定很著急。”
“你爺爺來看過你,見你沒什麼大礙,就把你交給我爺爺照看,並讓你在這養傷,不要回去。”
“不讓我回去!為什麼?”姚建不明白,眼神中全是疑問。
“你爺爺說你把一個孩子打了,而且很重,現在醫院住著啦!你要是回去了,他們定會讓你進什麼少管所。”韻兒轉過頭看了門外,確定沒人時,便小聲問他,“聽說那裡是犯錯的小孩去的地方,你這麼小就打人,而且還很重,你說因為什麼啊?”
姚建沒有反應,只是望著屋頂發呆,回想著打人的那一幕,心中竟有言不出的快感,頓時渾身好象有使不完的勁,手不自覺的握成了拳頭。
韻兒見他不搭理自己,便拉著他的手撒嬌,“說說嘛!快說說。”。
韻兒嚇了一跳,鬆開姚建的手,一幅受了氣的樣子,邊朝外面走邊嘟嚕:“那麼大聲幹嘛!我又沒有說你什麼。”
韻兒的身影在姚建眼中越來越遠,他心中一陣冰涼。他也不知道心中為什麼會有那麼大氣,眼睛只是冷冷地看著外面樹上飄下的落葉,久久地。
日升月落,姚建一天天受鍾親新和韻兒的精心照顧,身子漸漸痊癒了。可他的爺爺自從他出事後,每天都要到被打的小孩家做苦力事償還那小孩的醫藥費,否則那小孩的爸爸就要讓姚建進“少管所”。而他奶奶每天不見他爺爺和他,心中難免不會亂想,精神越來越差。可他爺爺白天要給人家做苦力,晚上還要回家照顧他重病的奶奶,身體也一日不如一日。最終他奶奶終於忍不住心中的猜忌,找到鄰居的張大嫂問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張大嫂性情溫和,內向不善言語,忍不住追問,一口氣全說了出來。他奶奶聽後,經不住打擊,當場吐血暈了過去。
張大嫂嚇壞了,慌忙跑到姚鎮中做苦力的地方,叫他趕快回去。可看著姚鎮中做苦力的中年男子(也就是被打小孩的父母)卻不讓他走,還說:“今日時間未到就想走,沒門。你如果走了,我會讓你孫子進‘少管所’的。”
中年男子的話令姚鎮中再三思索,放下手中的活。最後,終於忍不住內心的煎熬,他丟下手中的鏟子,與張大嫂飛奔回家。可已經晚了,鍾彩雲氣血攻心,再加以前的重病,她已經快奄奄一息了。
姚鎮中抱著鍾彩雲大聲哭喊,而在一旁的張大嫂急忙跑到韻兒家,告訴了韻兒爺爺這一切。不料,這些被韻兒知道,他們說的話全被韻兒無意聽見。
鍾親新與張大嫂來到姚鎮中家,推開門,見奄奄一息的鐘彩雲在姚鎮中懷裡不知說些什麼,他們便靜靜地站在旁邊,鍾親新放下手中的藥箱,準備給鍾彩雲把脈,誰知她卻推開了,不讓他治。姚鎮中看著鍾彩雲那傷心的眼神,朝他們揮了揮手,視意讓他們出去。
帶上門出去後,他們就站在外面,看著秋風席捲著落葉,心中的悲傷淒涼迎著秋風,伴著落葉,靜靜地等著。
屋裡靜悄悄的,只聽得見姚鎮中的哭聲和鍾採雲在他懷裡用盡所有力氣,一字一句的說:“我們命苦,不怪誰,老天看不下去,讓我先走,我還……還放心不下你……你和建兒。”
姚鎮中握著她的手,哭泣著,“建兒沒事,有你弟弟照看著。我也時日不多了,很快,我們就可以見面。到了陰間,這塵世的一切,就再與我們無關,你也再不用受苦。唉!只希望在下面‘閻王’能讓我們再在一起,你到下面等我。”
“我等……等你,如果……你……你不來,我就不喝孟婆湯。”鍾彩雲的眼中此時盡是一幅幅被歲月帶走的人生畫卷,一幕幕熟悉的畫面,一陣陣沉痛的記憶,從出世到此時,那麼清晰,那麼沉重,那麼不捨。
時間,從不停留,畫面隨時間而蒼老。也許,人生就是這樣!從不停留,從不給人任何想挽回的機會。
“建兒他爺爺,你……你說……到……到了陰間,我……我們真的能見面嗎?”她眼中正出現過世的父母和親人在向她招手,呼喚著她,迎接她到另一個國度,讓她忘了塵世所有的不幸。她想著鍾親新和建兒,此時竟有點不捨,手緊緊讓鍾親心握著,怕一鬆,從此就陰陽永相隔。
“會的”。鍾親新的眼淚溼了衣衫,溼了他的心。
“我……等……等你。”話語一落,鍾彩雲嘴角含著笑躺在了姚鎮中的懷裡,靜靜地,似沉睡著。
從此,她於塵世再無牽聯,她的世界又將是一片天地,是喜是憂,是悲是愁,塵世再無人知曉。她痛苦一生,臨死之前卻能想開,含笑而去,這也許是因為塵世她真的活的很痛苦,死倒是一種解脫,讓她可以遠離塵世的一切,永不再理會塵世的情仇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