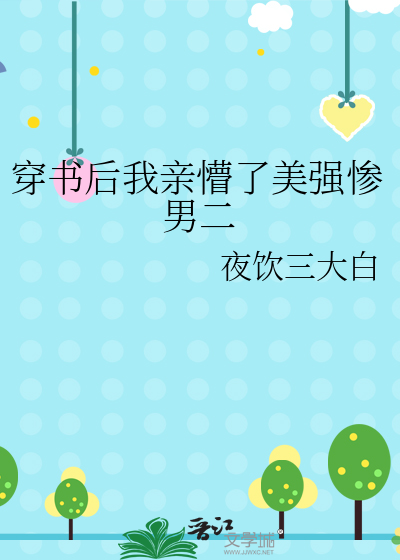林悅南兮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李紈不知賈珩心中所想,見其自有主見,也就不再多作言語,她本就是一味守愚藏拙的性子,別人之事都是很難過問幾句。
又隨意寒暄了幾句,正要告辭離去。
賈珩行至廊簷之下,目送李紈離去,搖了搖頭,如何對待賈家這條破船,他一時間也有些舉棋不定。
“唯一所慮者,若我科舉入仕,或會被視為賈家之人。”
這或許就是悲哀之處,政治鬥爭向來殘酷無比,除非他如廊上二爺賈芸一樣,安心做個升斗小民,賈家倒臺後,或能獨善其身。
否則,一旦科舉入仕,哪怕再不願,也難免會被視為賈家的旗幟人物。
當然,歷史上也不乏多線下注的例子。
“好在……還有時間慢慢佈置。”
賈珩思索了下,他心中已有一些謀劃。
卻說李紈帶著書冊,出了賈珩所居宅院,登上馬車,一路回到榮國府,正要往居所而去,走不大遠,就見垂花門下,俏生生站著二人,不由就是頓住步子。
只見為首之人是一個著杏黃色外裳的女人,其彎彎柳葉眉下,一雙丹鳳眼,隱見精明、凌厲之芒,旁邊站著一個對襟水綠色襖裙的女子,彎彎秀眉之下,瓊鼻檀口,肌膚白膩。
“大嫂子,這是從哪裡回來的?”王熙鳳開口問道,聲音清脆悅耳,如碎玉清音,說話間,就將一雙似笑非笑的眸子,落在李紈手中的書冊之上。
嗯,她不識幾個字,原也認不得什麼書。
“鳳丫頭,怎麼不在老太太跟前伺候著。”李紈笑著迎上前去,見王熙鳳目光疑惑,解釋道:“這是從前門街柳條衚衕,賈四兒哪兒取來的。”
賈珩之父在族中排行老四,故有此說。
王熙鳳俏麗的丹鳳眼中閃過一抹思索,恍然道:“原來是他家,賈四兒去得早,留下孤兒寡母,聽說董氏也是個心氣兒高的,見天兒攆著她孩子讀書,偏偏那賈珩是個喜舞刀弄槍的,可把他娘氣的不行。”
身為榮國府的管家媳婦,代王夫人處置府中大事小情,縱然賈珩之先父,賈四兒早已出了賈府五服之親,可對於這種族中趣事也並非全然不知。
在這個娛樂匱乏的時代,街坊四鄰之中的家事八卦,原就是談資趣事兒。
李紈頓了下,道:“哦,這倒是我不知了,從他家出來,倒是沒見那董氏。”
一聽王熙鳳之言,李紈心頭也不由生出幾分感同身受來。
想來自賈珠去後,她在家拉扯著一個孩子,這情景何嘗不類賈四兒?
再想到那少年不大孩子,動靜舉止,就已如小大人般,卻是不由想起了蘭兒,也不知長大後能否為她支撐起一片天地。
王熙鳳道:“年前才沒了老子娘,命苦的緊,她娘一心想讓進學,但這賈珩最喜舞刀弄槍,現在和蓉哥兒身旁充作常隨使喚,混口飯吃。”
因為,蓉大爺常和賈璉在一起廝混,又常往王熙鳳屋中串兒門,王熙風對賈蓉的身邊人也有幾分熟悉。
李紈心頭泛起一抹疑惑,不愛讀書,可臨得那一手好字,這就讓人稱奇了。
不過少婦原也不是憂切旁人,攀藤纏幔的性子,笑道:“若無他事,我就先回去了,這會子,蘭兒該下學了呢。”
王熙風笑了笑,目送李紈離去。
……
……
“珩大爺在家嗎?”
賈珩正要回屋,忽地聽到外間一聲呼喚,抬眸看去,就見來人穿著常隨短打綢衫,身量不高,斜眼看人,低眉順眼模樣。
“蓉大爺聽說你大好了,今日去戲園子吃酒聽曲,跟前缺個人伺候著,點名讓你過去呢。”那小廝開口說道。
賈珩擰了擰眉,回憶起前身和賈蓉的交集。
賈蓉年方十六,往日最喜飛鷹走狗,尋花問柳,有時與京都權貴子弟發生口角衝突,常有毆鬥之事發生。
而他因少時與表兄廝混,習些拳腳功夫,在賈蓉身旁,常有照應之舉。
再加上,前身自從母親去後,家中錢糧拮据,想入寧國府謀個差事,所以才在賈蓉身前大獻殷勤。
說來,前身之所以魂歸幽冥,為他所奪,也是因為此情。
如果按《紅樓夢》原著的歷史脈絡,他最後是要在賈府謀了個二等差事的,在賈蓉之妻秦氏亡故時,露過一臉的。
不過,此刻賈蓉還未娶親,其與營膳司郎中秦業之家的婚事還未定下。
“秦可卿……漫言不孝皆榮出,造釁開端始在寧,秦可卿這等絕世尤物,一入賈府,未來賈府之敗亡就進入了倒計時。”
《紅樓夢》原書記載,秦可卿死時,賈蓉二十歲,而冷子興——這位周瑞家的姑爺,在演說榮國府時,賈蓉才十六歲。
“珩大爺……”小廝見賈珩出神,就是喚道。
賈珩就有些不想去,他受傷躺在床上這十來天,賈蓉連探望都沒探望,卻是見他前即日大好了,在寧榮街溜達,這才想起來使喚人。
念及此處,就道:“我二日,身子還有些不大爽利,大夫說不能飲酒,等過幾日再過去。”
那小廝道:“那既是這般,我就先回話了。”
賈珩點了點頭,目送小廝遠去。
慶芳園
賈蓉、賈璉圍坐在廂房一方圓形桌子前中,時已入秋,有道是一場秋雨一場寒,二人皆著了棉衫,風流倜儻,一派儒雅風流模樣。
賈璉一身藍白色綢衫,面如傅粉,濃眉之下,一雙桃花眼眸自有多情流轉,掌中拿了一個酒盅,抿了一口,笑道:“蓉哥兒,親事說的如何了?”
賈蓉拿起一個果子往嘴裡塞著,心不在焉道:“現在敲定了幾家,還在說著呢。”
“你啊,怎麼怏怏不樂的,怎麼,怕成親之後,被管束著,不能出來玩兒?”賈璉猜到賈蓉的心思,笑道:“你看你二叔我,成了親又如何?還不是想去哪兒就去哪兒?”
賈蓉不好揭破賈璉的底細,憋著笑道:“二叔所言是理。”
“怎麼不信?我在家中可是說一不二。”賈璉見賈蓉表情古怪,臉色也有些掛不住,板起面孔,以長輩的口吻教訓,道:“早些成親也是好事,你也不小了,天天在都中廝混也不像樣,前日怎麼回事兒,怎麼聽說你族中賈老四家中的獨苗兒,被人開了瓢。”
“哎,就是和禮部侍郎家的粱公子,爭一個花魁,那幫狗娘肏的,從後面偷襲我,賈珩在一旁拉了下,就捱了一記。”賈蓉提及此事,仍有些憤憤不平。
“那花魁模樣俊不?”賈璉似笑非笑問道,對賈蓉也好,賈珩也罷,顯然並不怎麼關注。
“二叔,我哪見得著?還不是被那禮部侍郎粱元招了入幕之賓。”賈蓉臉一下子垮下來。
“得罪了禮部侍郎家的公子,珍大哥還不將你腿打斷。”賈璉打趣道。
賈蓉臉頓時苦了起來。
“好了,不說這些,待珍大哥打你,你到時只管過來尋我就是。”賈璉見賈蓉這副苦澀樣,心頭方愜意了一些,轉而又溫言寬慰。
賈蓉方轉憂為喜,笑道:“二叔,馮紫英約了明天一起秋獵,二叔去不去?”
賈璉擺了擺手,笑罵道:“我才不玩兒這些,我看你是存心拿二叔我取笑。”
開國勳親一輩,四王八公,歷經近百年,其後輩子弟多不稱器,疏於戰陣,幾為紈絝膏粱。
“不過,我倒是聽前個大老爺說,聽說舅老爺,將要大用了呢。”賈璉笑了笑,說道。
王子騰是他妻子王熙鳳的孃家,賈史王薛四家同氣連枝,如舅老爺大用,他在京都之中,也能多個依仗。
此刻賈璉和鳳姐成婚不久,正是如膠似漆,恩愛兩不疑的蜜月之期。
叔侄兩個說笑著,不多時,一個僕人抽空插話,說道:“蓉大爺,馮家大爺來了。”
“二叔,馮紫英過來了,我去迎迎。”說著,賈蓉就是起身,向著外間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