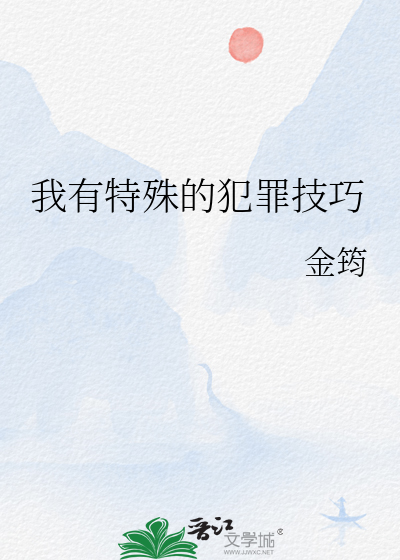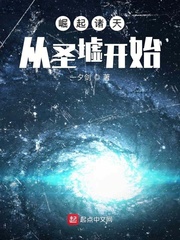狼家二萌神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冒煙了。
其實這甚至能算一個藝術兼哲學的深奧問題。沈穗看過許多戰前的,他發現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前半期的某些作品裡,經常會有「igotsoke」這樣的語段出現。一開始他以為這是某種時代流行語,於是便自然而然將其代入理解為「我有一支菸。」但顯然,這樣的理解是極其膚淺且片面的,也必定做夢也想不到其中已經深埋了很久的雋永含義。
而外頭的李欣乍聽冒煙了,他面上出現片刻的慌亂,畢竟這裡頭是雜物間,搞得不好一個火勢上來,他能見到鐵板沈穗。不過慌亂的時間肯定不會超過「got」soke噴出一口煙霧來的更久。因為,鐵門邊的牆上就掛著鑰匙。
於是,李欣露出了非常純真的笑容。
沈穗背上沒長眼,在逐漸濃重的煙霧裡不停踩著可能得著火點,然而他沒有外套二沒有一泡尿,只能徒勞地咳嗽起來,奔到鐵門邊,搖著欄杆叫道放我出去。
「叮叮叮。」鑰匙敲在鐵皮上發出異常清脆的響聲,李欣指頭又敲敲門,悠哉道:「咳,哎呀,老子曾曰過,寧靜致遠。」
沈穗不顧煙嗆得鼻涕眼淚橫流且屁股要滾燙起來,大怒道:「是諸葛亮說的。」
誰說的當然不重要,重要的是解釋權目前在誰手裡。李欣收起鑰匙,說道:「偷老子煙抽的下場,燒死在裡頭吧你。」
沈穗心說這火是他的破誓引來的滅世之火?媽的,果然是前幾天修真看得多,英雄氣學來了,天火氣也搞來了。他一腳猛踹上鐵門,可惜這鐵門並不領俠客的情,巋然不動。
「啊喂,你做個人吧,快放我出去啊!放我出去!」
李欣搖搖頭,表示你此前喊了太多次放我出去,這會兒喊破喉嚨還真不見得有人來救。頗為賴皮蛇道:「現世報了吧,你說這事應該怎麼了了吧。」
有道是人在屋簷下,必須要低頭。平時犯錯誤了,寫個檢討最多吃幾記巴掌就是了,哪怕是真的把年級主任那撮頭髮給拔了,把菜刀扔委員辦公室裡,也是關幾天,性命無礙。而現在是真·火燒眉毛,後頭的綵帶堆燒地很快,幾分鐘裡就把半片地兒給點上了。這周圍都是雜物箱子,弄不好真要交代在裡頭。
然而沈穗偏生就是個吃軟不吃硬的主兒,他篤信李欣不可能真坐視自己燒死在裡頭,光棍脾氣犯了,搖著門就是不肯鬆口。
「熬!看誰能熬!」李欣也毛了,能和沈穗這種內心混不吝的屑人混在一起做哥們,又能不是頑主麼?
兩人便大眼瞪小眼,煙霧出來大了,便閉上眼,等李欣摸著欄杆覺著微微發燙,而煙霧濃到模糊視線,他倒是率先慌了,叫道:「穗子,***作死呢!」
沒吱聲。
閉眼功夫,沈穗竟然從門邊消失了,李欣眼裡盡是火色,他真著急了,抖著手要把鑰匙***孔裡,手哆嗦一下鑰匙還掉地上了。
「***,真要燒死我啊!」
李欣顧不上許多,「噹啷」一下開啟門,旋即撲面而來就是捱了一拳,被當頭打翻在地。灰頭土臉,臉給燎了兩個炮的沈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又踹了李欣一腳,馬上拖著他連滾帶爬出了地下室。
待到地上的人覺察到不對,過來救火時,這兩個燻成泥的人倒是躲一邊去了。
「你這個狗東西,是真不把自己命當命啊。」李欣一拳搗了回去。沈穗沒躲,顯然他的注意力不在這上面,他怔怔地望著廣場上的人影,某個頭上彩飄帶還沒落盡的姑娘在飛也似得提桶跑路倒水,竟是還踩滑了一跤,一瘸一拐哭著提著小半桶水又往火場裡鑽。
「幹。」沈穗罵了一句,臉也不抹,手狠狠拍過膝頭跳起來衝過去,然而跑了不到一半路便洩了氣又匆匆
回來。惹得李欣又罵了一頓。
「你怎麼回來了!這不是正是時候嗎!」
「不合適。」沈穗悶悶吭了一句,隨手往路上某個水潭擦了把手,把臉給抹了把,才把後背給了出去,腳步卻又停住,他甚至不知道該去哪裡。
去哪裡?闖了這麼大的禍,還回家麼?臉皮多厚哇,回學校麼?靠不如讓他鑽陰溝,黑山防護所就這麼大,能去哪裡?
見哥們愣在原地,李欣如何不清楚沈穗的處境,他正想動身說先來哥們這兒待幾天,但就是眨眼的功夫,沈穗竟是不見了,任憑李欣如何去找,這周圍,居然不見一點蹤影,於是他也加入到大喊沈穗名字的隊伍中去。
廣場的火勢很大。
樸海珍的心很碎。
做慣了班主任,是全黑山不良少年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做慣了委員,是全黑山人民心裡標準意義上的官。樸海珍在外頭,人人見了她,須先打招呼,尊稱一句「樸老師。」若是在家裡,訓起了一兒一女,就是操扳手身材結實無比的丈夫也沒的插嘴,否則樸海珍嘴巴里吐出來的鋼水能把他也給熔進去。
有道是烈火出真金,當樸海珍衝到上午讓她心碎過一次的廣場時,她左顧右盼沒有發現人群有她兒子的跡象,當時一股血氣便衝了腦子,她慌忙拽住沈玉德的胳膊,仰臉喊道:「沈玉德,我兒子呢!我兒子呢!我兒子呢!!!」
沈玉德一把甩開了老婆,拽住了從火場裡跑出來的人,吼道:「沈穗呢!我兒子呢!」
「咳咳,咳,沒找見……沒找見……」
這話樸海珍聽得分明,這火,這煙,在地上就燙腳板,要是沈穗困住的地下呢,當場一口氣沒接上,便昏了過去。引得周圍人更加忙亂起來,直叫拆門板把人送衛生所裡去。
對,防護所裡可沒有什麼車,屁大的地方,一把火靠兩桶水就能澆滅了,是的,消防栓一開,火沒有幾個,剩下的,都是煙。
這把火燒的很大,不出半小時,整個黑山防護所便都知道樸老師的兒子給燒死在裡頭了。紛紛扼腕嘆息的同時又帶了些微不可查的幸災樂禍,畢竟大家都知道,老師這個位置,蠻多人相當了,摸書不比摸扳手來的強?
辛成功掄起扳手擰開了地表偵察車的輪胎螺絲,這臺「野兔」式全地形車的年頭有點老,輻條和軸承都得經常看顧看顧。他一邊聽著勘測隊的同事講今天廣場發生的事,一邊利索地把螺絲重新上了回去,跳下車,哐噹一聲實心的砸到地上,膝蓋不帶彎一分。
「怎麼搞得,好好的人,死不見屍呢?」辛成功說道。
同事遞給他棉絲,擦拭起油汙,嘆道:「找了小半天,啥都沒有,人也不見,確實奇怪。」
「這沈穗我知道,前陣子不就來咱們單位,嚷嚷著畢業分配過來做隊員麼,今天上午典禮***還要來咱們這裡,下午人就沒了。」
勘探隊的人都偏瘦小,嗓門有大有細。靠軍械庫安全門的寸頭攤手道:「咱們這兒是毛頭小子來的地方麼?想來就來?上去了也是累贅,盔鼠一爪子就能撓死他,防毒面具恐怕都不會帶。」
「咱們頭頂是黑山廢墟,也就是這幫子沒見過世面的小年輕喜歡上去,寧願他和我換換位置。」
辛成功鼻子有點漏氣,鼻孔那兒豁了道口,說話跟著嗤嗤響,他嘲諷寸頭道:「你要是讀書的料子,哪能來我手底下幹活?」
寸頭屁股一撞門,人彈了起來,不樂意道:「頭兒,我怎麼就不是個讀書的料呢?上次去黑山大學圖書館,可是我給你揀的黃***。」
眾人鬨堂大笑。
辛成功黢黑的臉當即變得通紅,反唇相譏道:「你揀的那些光碟去哪兒?給大家借一步說說?」
眾人又發出「籲」的鄙夷聲。
並沒幾個人格外關心廣場下燒死的那個是誰,這群四個月就要上地表一次的勘測隊員沒有什麼格外心情關注防護所發生了什麼,只要別欠了他們的特別補給就行。眾人旋即又日常搬弄起了健身器材,槓鈴和扳手起飛。辛成功坐進了野兔車裡,從儀表盤下面摸了支菸出來,抽了口,說道:「下個月小陳請假不上,誰頂他?」
眾人立刻熄了聲。沉默的槓鈴卻是呼啦啦和風車似的轉。
辛成功知道沒誰願意頂人班多去了一次地表,他也沒這興趣。這純是個運氣活,如果找對了地方,能拉一車戰前物資回來,要是倒黴了,被變異獸攆著跑,掛外面也不是很稀奇的事。沒人喜歡來勘測隊,防護所居民平均壽命六十多,這幫人壽命才四十多,一個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一個是身在輻中不知輻。
「無非開條件嘛!說,想要什麼,老子能辦的,都許上!」
討價還價是頂班的必須前提,辛成功開價兩條煙兩瓶酒,而有意頂班的寸頭王卻要求算兩次出勤。
「***別不知好歹,這地表出勤又不是我能作假的,大頭兒在外邊沒回來呢,我給你記賬簡單,回來頭兒給我錘死。」
「那沒得談,我不去。」寸頭王光棍道。
正當辛成功準備上手教育一下時,勘測隊門外傳來一道聲。
「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