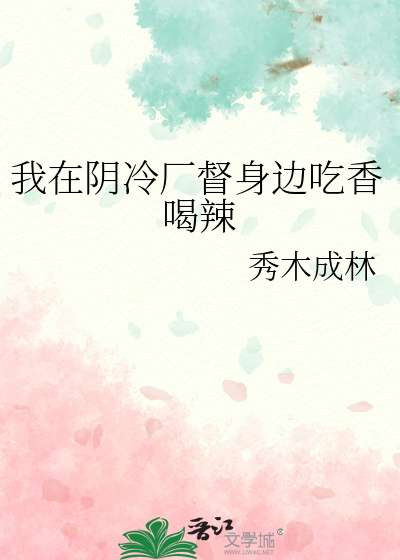天如玉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話剛說完,帳門厚簾被掀開,穆長洲走了回來。
舜音瞥他一眼,他先前離去,現在回來已卸了玄甲,臉上和手上都帶著層溼氣,大概是去清洗了一番。
勝雨見他回來,立即垂首退了出去。
穆長洲走近,手指直接伸入她外衫,挑起她中衣領口,去看她左肩。
舜音想起那裡之前被他揉撫了許久,藥膏都似全被揉了進去,抬手攏一下:“不必看,沒那麼痛了。”
穆長洲不知她是不是逞強,但見瘀血確實散了一些,才收回手,目光掃過她仍紅著的唇,又轉過她頸邊,看她眼下青灰在燈火裡像是更深了,俯下身,手在她身下的行軍榻上拍一下:“睡吧,就睡這裡。”
舜音轉眼掃視四下,這裡只一張行軍榻可以睡,就是她現在坐著的地方,偏偏又窄小,看著也僅能睡下一人。
穆長洲像是看穿了她眼神,薄唇輕輕一扯:“你現在的肩膀碰不得,自己睡這裡,我還要去交代軍情。”
說完頓一下,他身俯著,頭一偏就離近她臉,壓低了聲:“吉日都要定了,我還會急在這一時半刻不成?”
舜音下意識去看他,正對上他似笑非笑的臉,看著他直起身,在眼前轉身出去了。
頓時又想起先前他那句問話,當時她已忘了該說什麼,只顧著換氣。
直到他貼著她右耳,又說一句:“不說話便當你答應了。”
她抿了抿唇,沒說話,也說不出什麼話了……
外面隱隱傳來胡孛兒的嚷嚷:“軍司可算有笑了,得了首勝本就該高興!”
舜音側身躺去行軍榻上,小心避開左肩,剛好右耳被硬枕遮住,動靜也聽不見了。
她暗自舒一口氣,定定心,在心底說一句:沒什麼,本就是夫妻間該做的事。
當初是認定他娶自己並不情願,要識趣,才避開了圓房吉日,如今他既然想……那也是應該的。
只是心跳莫名的有點快,她按一下心口,閉上眼,不想了。
天亮得很早,大概是因為軍營裡時刻都有人走動,顯得很早。
舜音睜開眼時,營帳中還昏暗著,一片茫茫青白色,外面卻像是已在忙碌,時不時就有一些響動。
她坐起身,聽見外面隱約有兵卒在稟報什麼。
穆長洲在帳外接了一句:“嗯,稍後再報。”他已早起了。
舜音忽然看見身側多了一張行軍榻,不知是何時搬來的,但一看就知道是誰睡的,轉眼去看帳門,門簾掀開,穆長洲走了回來。
他身上已穿好了玄甲,走近時有微微鐵甲擊撞輕響,一步一聲,眼睛看著她,又掃了眼她左肩:“你起早了。”在外奔波三日肯定辛苦,本是想讓她多睡片刻才早早出去,沒想到她還是早醒了。
舜音睡了一覺也不覺疲憊了,問:“要行動了?”
穆長洲點頭:“先機已有,不盡早行動,豈不浪費你這三日了。”
舜音沒說什麼,心裡卻也是這麼想的,手指攏了攏身上外衫。
穆長洲走近,站在她身前,俯身拉起她外衫左袖,一手握住她左臂,說:“伸進來。”
舜音怔一下,才察覺他這是在給自己穿衣,一時都沒顧上動。
他已直接握著她左臂送入袖中:“眼下也就只有我知道你此處受傷,總不能讓旁人來。”
舜音的左臂抬起,連到左肩還有點痛,但他說話的功夫就已替她套好了衣袖,手指握著她的手臂,眼神似還在看她反應。她右手握住領口,輕聲說:“好了,後面我自己可以了。”
外面已有兵卒來請:“軍司,準備好了!”
穆長洲仍看著她臉,沒見她露出痛色,才鬆開手站直,轉身去取了木架上懸著的輿圖,在手中一卷,往外走。
舜音抬眼看去,他停在帳門邊招了下手。
勝雨緊跟著就進來伺候,他又回頭看她一眼,才放下門簾走了。
營中一支一支隊伍正牽馬往外,到營地外列陣上馬,皆是騎兵。
並非昨日的騎兵,這支兵馬由穆長洲親手挑選,有涼州精銳,也有自鄯州精銳中擇選出的一部分,整合之後訓練至今,今日方要派上用場,一共也不過才兩千人。
胡孛兒打馬從營中匆匆奔出,絡腮鬍須上都掛著沒幹的水珠:“軍司這是打算一戰斃敵?”
兵卒牽馬送至,穆長洲將輿圖納入懷中,接過韁繩,翻身而上,知道他還不清楚自己已掌握先機,舜音的能力也不能暴露,否則便會連帶牽扯出她先前為中原做的事,沉聲說:“能一戰斃敵,自然最好。”
胡孛兒抹一下鬍鬚,先前連敗,他覺得憋屈,昨日才揚眉吐氣:“昨日那個報信的弓衛當賞,也不知跟著夫人做什麼去了,還能帶回訊息,今日再來些敵方的訊息就好了!”話到此處一停,他瞅瞅穆長洲,只因知曉他脾氣,不該多嘴的不要多問。
穆長洲一笑:“該賞誰我自然會賞。”
胡孛兒見他有笑才放心,仔細想想,自打昨日夫人返回,他笑容就多了。
穆長洲打馬在前,掃視過一遍隊伍,回頭問:“都按我昨晚吩咐安排好了?”
胡孛兒回:“都好了!佐史那裡也已安排過了。”
穆長洲點頭,看一眼天色。
舜音由勝雨伺候著穿好了下裙,梳洗完畢,走出中軍大帳時,天上尚未露出朝陽蹤跡。
營外騎兵卻已整肅待發了。
她轉頭找了找,剛看到穆長洲在馬上的身影,他已先一步看到她,打馬返回營內,到了帳門邊,擺一下手。
左右退開,他自馬上稍稍俯身:“料想你還有話說。”
舜音就是出來再說詳細的,掃視過左右,放低聲:“處木昆部慣來陰險,常於四周分佈兵馬,要直搗其大營,還是要留意。”
穆長洲看著她冷淡的眉眼,想起她昨日說起這一部落時語氣也冷,靠直覺判斷,低聲問:“你對他們熟悉?”
舜音說:“不算熟悉,但知道一些。”
穆長洲覺得她臉色更淡了,卻也看不出什麼,在馬背上坐直。
日未升,風已更烈,正是出發的好時候。
胡孛兒已自營外看來。
穆長洲面色冷肅,一思既定,低頭說:“若有不對,及時後撤,但要迂迴繞至關口,不要直行。”
舜音點頭,目光上下打量他,雖然早已接受他是涼州行軍司馬的事實,昨日也親眼見了他身披玄甲,但今日見他直接領軍,似才徹底剝離了年少時他那文人模樣。
穆長洲與她對視一眼,一扯韁繩,打馬出營,帶軍往前。
舜音看著他背影遠去,直到被風吹過的塵煙瀰漫遮住,才收回目光,低頭握住袖中手指。
能不能一舉而成,就看今日了……
天陰風大,日頭始終沒有升起,四野之中蒼茫一片。
一片白色圓頂的氈房在視野裡顯露,離得太遠,猶如原中一叢一叢人畜無害的白野花。
胡孛兒扒著塊大石朝那裡遠遠看了一陣,扭頭急匆匆上馬趕回後方隊伍:“軍司,神了!真在此處!”他兩眼都要放光。
穆長洲收起輿圖:“領你營中騎兵在後壓陣,待我先鋒過後再入。”
“是。”胡孛兒搓手,已急不可耐要去立功了。
穆長洲一言不發地看著天,一手持弓,一手抓住韁繩,如在等天時突降。
胡孛兒連同身後隊伍已不自覺靜默,連馬都未發出一聲嘶鳴。
驀然又是一陣東南大風吹來,呼嘯席捲著自身後往北面漫卷。
穆長洲揚手一揮,韁繩一振,策馬而出。
身後騎兵隊伍頃刻跟上,順風出動,攜沙帶塵,直衝往前。
陰沉沉的天際似與遠處的山嶺相接,近處的曠野卻在震動,玄甲如潮水奔襲而來,快過疾風,割裂天際,直指敵營。
那片白色氈房裡頓時動靜四起,似有無數人在奔走,匆忙應對。
當先一陣箭雨,隨風送入敵營大帳,披頭散髮的敵兵們來不及準備,有的甲冑不全就已持兵至營門處抵擋。
迎接他們的是迎頭一箭,力透穿心,中間一名敵兵被穿胸而過,倒地不起,頓現缺口。
其餘敵兵震驚前視,看到為首而至的人玄甲策馬、手握長弓的一道身影,就已大駭出聲。
但已晚了,穆長洲收弓,身後騎兵隨他自缺口踏馬破入,手中馬槊亮出,尖刃反射冽冽寒光……
營地被踏破,胡孛兒率自己營中騎兵衝掃而來,跨馬直奔敵方大帳,揮刀劈帳而入,很快又氣急敗壞地出來:“不見狼頭纛!狗賊頭子跑了!”
穆長洲策馬至營地後方,看見一片缺口,快馬踏過的痕跡明顯,往缺口後方看,雖有路卻狹窄,不是逃生的好去處,反而留了如此明顯的痕跡,像是生怕別人不知道他們是從這裡逃了。
他持弓環視四周,在嘈雜中分辨著動靜,忽而下令:“撤出嚴戒。”
胡孛兒聞言一愣,當即高呼,傳令四周:“快撤!嚴戒!”
兩邊忽來陣陣馬蹄聲響,有兵馬在往此處合攏而來。
穆長洲縱馬出了敵營,左右各望一眼,掃到了左側豎起的狼頭纛,原來往後逃是假,往側面逃再回擊是真。
確實如舜音所言,陰險,且常於四周分佈兵馬……
已是午後,天依舊陰沉。
舜音坐在營中,隱約聽見了有快馬返回。
剛抬頭去看,勝雨快步自帳門外走入,到她右側,湊近小聲耳語了幾句。
快馬返回的是斥候,營中留了兩名副將鎮守,大概是提前得了軍司吩咐,副將吩咐將斥候帶回的訊息也送至夫人知曉,說是發現一支敵兵天亮時就往關口方向去騷擾,眼下正往南向而來。
舜音擰眉思索,昨日敵方兩隊兵馬折損,應該沒有活口傳回穆長洲已領兵的訊息,所以這支兵馬一早出動,先往關口,又往附近而來,多半是有意騷擾,以探虛實。
只是他們不知眼下涼州的騎兵精銳已直往其大本營而去了。
她又想了想,當機立斷起身:“即刻就走。”
勝雨忙去為她備馬。
營中定是早有準備,舜音出去時,發現那兩名副將已在指揮兵卒拔營。
弓衛們很快朝她身邊聚集過來,牽著馬,攜弓帶刀,料想也是一早安排好的。
勝雨牽了匹白馬送來。
舜音看了一眼,她的騮馬經那一摔也受了傷,暫時騎不得了,抓住韁繩坐上馬背,扶一下隱隱作痛的左肩,當先打馬出營。
按照穆長洲的話,迂迴繞行往關口而去,沒有直行。
他將營帳故意紮在此處,避開了關口方向,也是有意避開敵方一股一股的騷擾,此時剛好有時間繞路。
還沒多遠,竟聽見了隱隱而來的馬蹄聲。
一名弓衛快馬奔去觀望,又迅速折返,跟上舜音的馬,急聲報:“夫人,是敵兵,已尋到附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