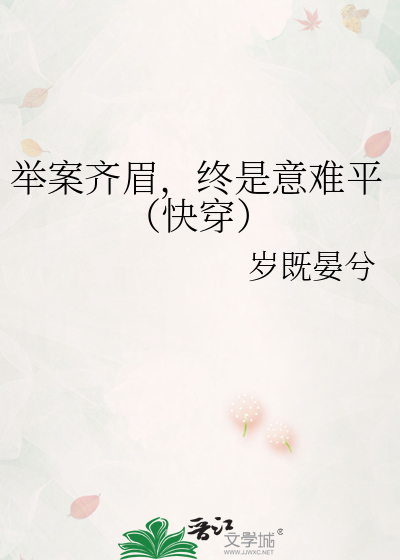9 呂玄
菌行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呂曉璇想了許久,做出一個決定,土匪留著也是禍害老百姓,不管他們到底是本地武林門派養寇自重也好,有什麼苦衷才落草為寇也罷,老百姓因他們吃了苦,那就該殺。
剿匪!
別看呂曉璇在刑部做官,喊剿匪多少有點狗拿耗子多管閒事,但呂曉璇這些年不是白混的。
打定主意,呂曉璇行動起來,她進城遞交令牌,尋到本地衛所的羅千戶,羅大虎。
那羅大虎自退下戰場,在地方衛所待了一陣,便有些心灰意懶,自覺該吃的苦早在戰場上吃完,往後只需躺功勞簿便可。
這天,他照常拖到日上三竿才到衛所,卻見衛所氛圍緊繃,軍士們精氣神與往日大不一樣,尤其是與他一同從戰場上回來的老兵,各個都站姿筆挺,只看模樣,便知道是難得的好兵。
羅大虎疑惑:“怎麼了這是?”
路過的龐副千戶對他擠眉弄眼,卻沒敢張嘴,直到屋內傳來一聲輕笑。
“大虎,幾月不見,你就懈怠了啊。”
羅大虎聽到這聲音,當即面色一變,連滾帶爬衝進去,看見來人的一刻,他心中激動,雙膝重重跪地:“呂將軍!”
衡州府衛所的羅千戶,正是呂曉璇打北孟時帶過的兵,她便是羅大虎的老上官!
呂曉璇端坐首位,龍盤虎踞,氣勢威嚴,她淡淡道:“我已不是什麼將軍了,如今不過一小小員外郎爾,難怪羅千戶要這麼久,才屈尊到衛所來見我。”
羅大虎看著這令他無比敬畏愛戴的長官,又聽呂玄語調頗冷,又是激動又是委屈,鐵塔般黑黝黝的漢子,眼中已有了水光。
“將軍,屬下也不想如此,可衡州府沒戰打,兄弟們窮啊,別說習武操練,能按時拿餉銀便不錯了,屬下若不縱容衛所內懶散之風,底下的兄弟也不敢離職去為家裡耕田,日子可怎麼過呢?”
呂曉璇呵斥一聲:“你還有理了!”
見羅大虎畏縮一下,她也不深究,揮手道:“我這次找你,卻是有筆大買賣,卻不知道你羅老虎那口牙還在不在,啃不啃得動硬骨頭。”
買賣?
羅大虎眼前一亮,上次呂大人和他們說有買賣做,隔天就領著他們一幫兄弟突襲北孟韃子的王帳,若非那韃子的王跑得快,就得和他的八皇子一樣,被呂大人把腦門給射穿!
羅大虎換了單膝跪地的姿勢,兩手一抬:“將軍,老虎餓了半年,快成病虎了,若有買賣可賺,有肉可吃,再硬的骨頭也啃得下來!”
呂曉璇則勾勾手指,示意他上前來:“我聽說這附近鬧水匪,前陣子還沉了一船官鹽?”
羅大虎聞言面色一變:“果然是硬骨頭。”
……
自呂曉璇走後,燕紅琴越發沒了顧忌,上完課便拉著呂瑛練功,他自己擅使軟劍,就要呂瑛也練,這一看,就發現呂瑛已有了劍法的底子。
他眉頭一皺:“你以前練過劍?你的劍術不差。”
能讓西洛教教主誇一句不差,呂瑛的劍術自是好的。
呂瑛嘆氣:“偷練的,被外祖發現了,就練不成了。”
燕紅琴:“呂家家傳的潮青劍卻為江湖一流的劍術,許多人若是你外祖,看到了你的天賦,便是拼著你的命不要,也要讓你練下去,好看你能將武道推演至何等境界。”
一旁打龍華拳的秋瑜想起那本說呂太后英明神武的野史,事實證明那本野史可信度挺高,那麼書裡說秦湛瑛是劍聖級別的高手,估計也是真的了。
有部古偶還特意以這本野史裡的秦湛瑛為原型,搞了個對女主戀而不得的悲情男配,可惜演員顏值辣眼睛,沒瑛哥千分之一的帥氣,讓劇組其他演員發了筆醜難財,真是杯具。
等一套軟劍練完,秋瑜過來給呂瑛擦汗,呂瑛氣喘微微,靠著他流了好一陣虛汗,燕紅琴覺出不對,一摸小孩額頭,罵了一聲,將人抱起送進屋裡,又寫藥方一貼,讓秋瑜趕緊去抓藥。
秋瑜也嚇住了:“怎麼就病了?我昨晚明明給他煮薑湯了呀。”
秋瑜上輩子的父母都是運動員出身,他自己人在幼兒園時就因身高被排球隊挖走,自小飲食科學,勤奮鍛鍊,身板子好得很,呂瑛是他兩輩子見過的最柔弱的人類。
也是為了減輕運動帶來的傷病,他在學校裡還找中醫的系主任學過幾手推拿正骨,背過醫書,在中醫一途不算門外漢。
他看著方子,感嘆道:“難怪說醫武不分家,紅姨的醫術不錯啊。”
秋瑜手上的可不是太平方子,有幾處用藥頗狠又不會傷到根基,可謂恰到好處,是針對呂瑛身體出的對症良方。
秋瑜拿錢去城裡藥鋪抓了藥,回來親自煎,苦澀的藥香在室內漫延,呂瑛側躺著,秋瑜給小爐子扇扇子的身影便落在他眼裡。
待一碗藥灌下去,燕紅琴用內力為呂瑛推拿,推出一身的汗,又換了新衣,拿被子裹好。
小孩看起來懨懨的,燕紅琴在他眼前揮手:“別動你那腦瓜子了,躺下睡吧。”
呂瑛小聲說:“我在想娘去剿匪的事,她是不是要找鹽幫的麻煩?”
剿南方十七寨,便是對上鹽幫,對上鹽幫,就要被南方十七寨找麻煩,這是常識。
燕紅琴冷哼:“鹽、鐵、茶乃是朝廷命脈所在,這南方十七寨卻敢鑿沉載有官鹽的船,說他們背後沒有鹽幫支援,誰信?”
湖興坊也是水運上的,秋瑜也知道一點內幕:“今年鹽幫幫主的老孃過七十大壽時,連本地巡撫都要讓人上門送禮,只為換官鹽上了水道能平平安安,武林幫派做到這份上,絕了。”
巡撫可是從二品的大官,是封疆大吏,放後世,誰敢想象省級大員給地方幫派送禮?
呂瑛裹著被子:“巡撫不是對鹽幫低頭,是對鹽幫背後的人低頭,左不過雲、宋、鄭、仇那幾家。”
此四家為湘地豪族,歷經兩朝,在孟朝,這四家一共出了四十八位進士,到了禹朝,依然富貴難言,只是暫不派子弟科舉,卻依然樹大根深,盤踞此地。
秋瑜:“這我就沒聽過了。”
在秋瑜看過的史書上,永康帝,也就是他面前這位生病的小人家在登基後曾血洗各地官場,捲進去的地方豪族不計其數,抄出數量驚人的財富,讓永康帝拿了做軍餉一統天下去了,誰知道那四家是不是也是用命獻軍餉的倒黴蛋呢?
呂瑛又說:“我不放心她,你拿我的玉牌去城中的雙扣衣鋪,那是賣估衣的地方,實則是我們呂家安插在此處的暗線,讓那的人送信給我外祖,就說呂玄要帶兵幹鹽幫,讓我外祖派人過來幫忙。”
秋瑜心說自己今日跑腿個沒完,可見呂瑛臉色潮紅,頭髮汗溼,病得可憐兮兮,還惦記著母親,又沒法說不字,轉身出了門。
燕紅琴將坐墩踢到床邊,坐好,說:“你這心眼子再不少點,別說早逝了,只有夭折的份。”
早逝起碼得是十幾歲的少年人,活不到那歲數就走了便叫夭折,在會醫術的人眼裡,呂瑛就是左臉寫夭,右臉寫折的模樣。
燕教主打量他:“沒想到你底子這麼差,這樣的身子配你的悟性和頭腦,可惜了。”
呂瑛並不在意,這年頭健壯的孩子照樣會夭折,原因多種多樣,有掉池塘裡淹死的,染腸闢拉肚子拉死的,被生父活活打死的。
孩子未必懂死亡,也避不開死亡。
“一切都是命。”呂瑛回了這麼一句話。
燕紅琴看他冷漠的表情,一時失語,他幼時不得父親喜愛,走到哪都被罵紅毛鬼、鬼崽子,最深刻的童年回憶便是縮在荒僻的院子裡,在牆角下躲著冬風瑟瑟發抖,金山在西北,是朵喇漢國的土地,教內總有提著鑲寶石馬刀的少年朝他扔石子。
可就算活著那麼難,他也還是活下來了,等他的父親發現自己生不出兒子,紅毛鬼也登了大雅之堂,呂瑛有那麼好的母親護著,卻對死如此從容,令燕教主琢磨不透。
燕紅琴:“你小小年紀,倒是看破生死。”
呂瑛回道:“死是唯一鬨不了人的東西。”
“那為師也送你一句話。”燕紅琴按住他的腦門,“莫想那麼久遠的事,人生際遇之奇,你想都想不到。”
呂瑛操心他娘,但他娘不怎麼需要操心。
呂警官兩輩子啥大風大浪沒見過?
非洲多方混戰的戰場她滾過,最慘的時候身上被彈|片穿了好幾個洞,血流得滿地都是,耳朵還被震得有點聾,這輩子又提著偃月刀親自去冷兵器時代的戰場上打仗,羅大虎這批衡州府的軍士都是她在戰場上帶過的兵。
別看當年呂曉璇沒空把他們當現代軍人去操練,但這幫軍士有多少戰鬥力,該怎麼用他們,呂曉璇比本地巡撫、總督還清楚得多!
手裡有了千來號人,呂曉璇又去和那位年初備受屈辱的巡撫打了招呼。
這位劉巡撫是本朝第一位探花郎,外表憂鬱斯文,妻子早逝,獨自帶著女兒在此地為官,有種寡寡的氣質,談吐清晰有條理。
她雙手抱拳,利落一禮:“下官見過巡撫大人。”
劉千山望著傳說中的神弓呂,先是為對方高大英武的武人身段、俊美逼人的臉龐震懾,見對方如此有禮,他連忙去扶。
“呂大人不必多禮。”
年初對北孟的戰沒打完,全國各地的衛所兵力幾乎都抽調到了前線,劉巡撫手頭無兵,又要護著官鹽,不知受了多少鹽幫的委屈,如今天降一悍將願意幫他打水匪,心裡只有樂意的,要錢給錢,要糧給糧。
託劉巡撫的福,呂曉璇在極短時間內將打南方十七寨需要的兵力、糧草集齊,順帶疏通本地官員中的“帝黨”,確認了豪族派官員是哪些,將之匯總成名單,以密摺形式送去了京城,並帶著兒子的份寫了個請安折。
摺子的內容大概是陛下,自戰場一別已有半年,我帶我的兒子,您的侄子游山玩水,十分愉快,感謝您給的假期,現在我已復工,並要為了陛下在湖廣一帶的權威,與鹽幫、水匪、地方豪族展開大戰。
另附一份本地物價表給陛下,又帶我家瑛瑛向您問好,祝您萬福安康。
如今呂曉璇和那位已確認是穿越者的秋瑜,大概是天底下唯二知道皇帝陛下真的沒法生孩子的人。
承安帝因腮腺炎而失去生育能力是《禹太宗實錄》裡有明確記載的,承安一朝最大的宮廷新聞,就是承安帝獨女慧柔公主的身世謎團。
總之,在封建王朝時代,皇帝大伯要是還想找繼承人,呂瑛便依然是有力的皇位競爭者。
呂曉璇也不知道兒子以後會不會還想做皇帝,但媽媽可以先幫他刷點印象分,以備不時之需。
在等待陛下回信時,呂曉璇先回客棧,看了發燒的兒子,將他們連著難民打包送到劉巡撫家安置。
劉巡撫不算貪,但這年頭能供出一個探花的家庭也窮不到哪去,他府上的環境自然比客棧更好,更適合孩子養病。
呂瑛是被秋瑜抱著到劉府的。
劉巡撫與呂曉璇正在探討剿匪大事,只有劉小姐來迎他們,她看起來與秋瑜年紀相當,都是八歲左右,穿藍襖白裙,衣著素淨,指揮丫鬟僕婦時爽快利落,將一切安排得妥妥當當。
秋瑜抱著呂瑛,捏他的手腕,發現孩子的心跳有點快,低聲問:“是不是很難受。”
呂瑛微微搖頭:“比以前好多了。”
以往生病時,若外祖父在外跑船,娘也不在家,他才是真的難受,現在身邊有人陪著,噓寒問暖,他便覺得好過許多。
晚上,娘也來看他。
呂曉璇看起來有些疲憊,在見兒子前特意去洗漱換衣,她拿著一卷畫,在呂瑛面前展開:“寶貝,快看這是什麼?”
呂瑛震驚:“這圖畫得好粗糙。”
呂曉璇面露委屈:“瑛瑛,這是孃親自畫的。”
知道兒子是ssr級的書畫雙絕,不耽誤做孃的被打擊時表達傷心。
呂瑛立刻改口:“細節處頗有巧思,這些虛線實線,可是用來分州縣河流的?”
呂曉璇摟著他,指尖在圖上滑動:“沒錯,這是娘畫的簡易版軍事地圖,你看這幾個標了紅的河段,便是六個水匪寨子出沒的區域,他們居然是分割槽幹活,說不是一夥的誰信吶。”
她興致勃勃的,與呂瑛說了她如何探查附近的地理環境,又如何推出水匪的大本營所在。
“打仗不是直接莽上去,而是從前期準備就開始積蓄勝利,進攻不過是整個計劃的收尾階段,後勤更是重中之重。”呂曉璇點著兒子的小鼻子。
“沒錢可打不起仗,幸而劉巡撫是個能臣,有他管後勤,娘才敢去剿匪,為了得他的助力,娘方才也和他細細講了一遍為何打這場仗,如何打,他才看起來有信心,要和我拼這一場呢。”
呂瑛靠著母親,專注聽她說如何認地圖,如何整合軍士、後勤,怎麼做作戰計劃,為何要剿這些匪。
“那些匪盜對百姓沒有同理心,他們想不起自己也是百姓中走來,卻做了豪族、武林門派控制老百姓的一把刀,匪盜不光可四處劫掠,地方勢力也可藉此控制商道,又從百姓身上收保護費,颳了一遍又一遍,匪盜也刮百姓,搶錢,搶糧,搶人。”
呂瑛想了想,“每個水匪寨子不過百餘人,對百姓之害卻酷烈至此,他們若不死,朝廷便是想治理此地,也無從下手,百姓更是過不下去。”
呂曉璇疼愛地撫摸兒子柔軟濃密的髮絲,許諾道:“娘保證,他們很快就要死了。”
燭光之下,呂瑛看到母親疲憊卻自信的雙眼,她知道她即將打的是一場有利於百姓的仗,她的付出會是值得的,而她的敵人必將被她摧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