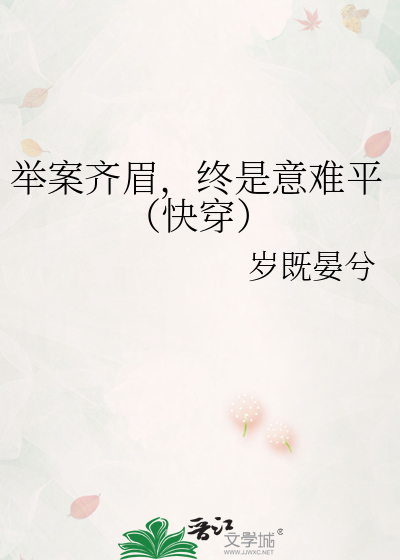火燒花果山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大駙馬被這一巴掌給打懵住,大公主怎麼會出現在這裡!
“還請大駙馬歸還我的帕子,”崔姣趁機道。
大公主氣勢洶洶又給了他一耳光,“帕子還給她!”
大駙馬捂著半張臉,將那一方帕子拿出來,崔姣忙搶到手裡,自覺避到隔房內,苻琰也在裡面,人沒出來,該是大公主收拾的,他不好參與進去。
苻琰看著她手裡攥著失而復得的帕子,指著桌上的油燈,“燒了。”
崔姣走到油燈前,背轉過來撇嘴,就算他覺得帕子被大駙馬碰過髒了,回頭洗乾淨就好了,燒了多可惜,這料子可是織成①的,十分名貴,還燻過香,要不是給大駙馬設局,她哪裡用得上這等好料子。
崔姣心如刀割,還是將帕子燒了。
再扭頭,太子突然推開門出去,崔姣急忙跟上,正堂內大公主和大駙馬都已經離開了,崔姣本來空出地方好讓大公主發洩,但顯然大公主再置氣,也不會丟了公主的體面,估摸是要回去了斷。
崔姣看太子臉色,溫吞問他,“殿下,大公主真的會休駙馬麼?”
太子走在前面腳步未停。
崔姣就知道他也回答不上來。
--
大公主連夜搬離了鄭府,回宮後找皇后哭訴,皇后只有這一個女兒,大公主受委屈,斷不能忍,帶著大公主去紫宸殿找皇帝,彼時皇帝才跟王貴妃賦詩一回,殿中樂聲陣陣,王貴妃賣力的跳了一曲綠腰哄得龍顏大悅。
皇后這時過來,皇帝的好心情敗了大半,等到聽皇后為大公主請他下旨休棄大駙馬,皇帝已無好臉色,不耐煩道,“深更半夜,皇后不睡覺,說什麼胡話。”
王貴妃在一旁看熱鬧。
皇后此刻已經氣上頭,哪管的上她,將大駙馬的所作所為悉數說出來,皇帝聽完也氣的吹鬍子瞪眼。
他將皇后母女安撫一頓,決定明日一早便下旨,再命中官將她們母女一路送回蓬萊殿。
等她們走了,皇帝再無心歌舞,大公主是他的長女,哪有不心疼的。
皇帝頭疼。
王貴妃給他按摩,“大駙馬儀表堂堂,向來愛重大娘,怎麼就做了這樣的糊塗事。”
皇帝嘆了口氣,“當初挑他給大娘做駙馬,就是看重他人品貴重,又能與鄭氏聯姻,是兩全之舉。”
王貴妃道,“陛下不如傳大駙馬來問一問,若真是他混賬,再下旨也不遲,就怕這當中有什麼誤會,畢竟他們鄭氏門楣清正,也免得他們小夫妻就這麼散了。”
皇帝深以為然,遣人召大駙馬進宮。
至次日早,聖旨未下,皇后不便前去,遂命宮女過去打聽,宮女回來告訴她,“皇后殿下和大公主走後,因王貴妃勸了陛下幾句,陛下昨夜召大駙馬問話,大駙馬說,大公主夥同東宮的崔掌書設計他,他百口莫辯,但絕不認這栽贓,陛下現對大公主十分不滿,等著朝後要問。”
皇后臉都氣白了,“原來是這賊婦攪局!”
隨後便命那宮女去東宮將太子和崔姣叫來。
皇帝沒下旨,崔姣猜到恐怕事情有變,等到了聽皇后一說,自己也有苦說不出,主動摻和,果然要出事。
崔姣心裡急,但在皇后面前不能表露,只能看著太子行事。
苻琰坐在椅子上八風不動。
皇后沒他這般定心,“崔姣不是說他與街邊酒肆中的胡姬有來往,不如現將那胡姬綁來,看他還能說什麼。”
苻琰道,“只怕晚了。”
崔姣手心裡出汗,約是真晚了,大駙馬昨夜能在皇帝面前狡辯,胡姬恐怕也轄制不了他了。
大公主抓住皇后的手,哽咽道,“阿孃,兒不願再和他有任何瓜葛,哪怕和離兒也認了。”
崔姣很敬佩大公主的決心,但現在能決定這件事的是皇帝,皇帝如果覺得是她們有錯,大駙馬無辜,大公主應和離不了,還得回鄭家去,她就更慘了,她是大公主的幫兇,皇帝捨不得降罪大公主,卻不會對她憐憫,到時太子都保不了她。
崔姣著急了,悄悄伸手扯苻琰的袖子,苻琰沒理她,她耷拉著嘴角,神仙打架,小鬼遭殃,他們若心狠點,為了息事寧人,把她一個人推出去頂罪都可能。
皇后把大公主抱懷裡,安慰道,“有阿孃在,絕不會讓那豎子欺你!若陛下不肯降旨,我讓你外祖來長安一趟,有你外祖出面,沒什麼可怕的!”
崔姣心裡羨慕,若她阿孃也活著,她一定也能躲在阿孃的懷抱裡,不用背井離鄉來到人生地不熟的長安,受太子的鳥氣!
大公主哭著搖搖頭,“外祖年事已高,兒不能麻煩他……”
皇后頓了頓,“就算你外祖來不了,你舅父難道還能看著你被欺負?”
皇后的父親翼國公今已近古稀,致仕後回河東頤養天年,現今裴氏郎主是皇后的長兄裴戟年。
裴氏手握朝中兵權多年,積威日久,不管是冀國公還是裴戟年來長安,皇帝看在他的面上,也得准許大公主和離,但皇帝必定心有芥蒂,更會與皇后疏遠。
皇后不在意,大公主卻不能不在意,這關係的不是她一人。
正在她猶豫間。
苻琰出聲,“母后,此事不需勞動裴家舅父。”
皇后、大公主看向他。
苻琰轉頭對崔姣道,“慈恩寺內你看到什麼了?說出來。”
崔姣往周圍的宮女看了看。
皇后揮手叫人都退下了。
崔姣才敢將大駙馬與五公主前次在慈恩寺內私相授受說了出來。
大公主震驚不已,“他竟跟五娘也不清楚!”
皇后氣在臉上,哼笑道,“上樑不正下樑歪罷了。”
她這句就把皇帝和王貴妃一起罵進去了。
崔姣禁不住想到在女史嘴裡聽過的話,王貴妃還沒出閣時,與皇后是閨中密友,後來皇后嫁給了皇帝,皇后常召她入宮說話,一來二去的,她跟皇帝竟然揹著皇后勾搭上了,那時候皇后剛懷了大公主,知道這事後動了胎氣,差點落了胎,她跟王貴妃的樑子也就此解下。
皇后立刻就要去紫宸殿,被大公主按住了,“阿孃,既是牽涉到了五娘,這事咱們就不能善了,總得有辦法將這醜事揭露在阿耶眼前才好。”
她深吸一口氣,“他們不知羞恥,我也不怕丟人。”
但還得想到辦法才行。
崔姣道,“乞巧節快到了。”
皇后眼睛一亮,後宮有座乞巧樓,是皇帝為表雨露均霑修建的,等到了乞巧節那日,皇帝會賜宴給百官,後宮的妃嬪齊聚乞巧樓,對月穿針,快者得皇帝賜巧。
確實是好時機。
皇后對崔姣很是嘉許,與太子道,“三郎,這孩子機靈又心善,難怪你留在身邊,上回她一個小娘子敢上場與襄王打馬球,還把襄王打的節節敗退,我就瞧出來有意氣,有她陪著你,我也沒什麼可操心的。”
太子薄唇抿成了一條線,半晌道,“母后過讚了。”
崔姣心還懸著,沒空關心皇后的讚賞,一直低著頭,皇后看來,就當她在害羞,誇兩句,但終歸就是個侍妾,皇后道,“三郎,而今你已及冠,東宮是時候進太子妃,也該讓我抱孫子了。”
太子頷首,“勞母后費神,是兒不該。”
皇后命人拿貴女們的畫像來,“拿回去看看有沒有合意的。”
崔姣看著那些畫像感嘆,得有多少貴女啊,太子選妃,這些貴女中除了太子妃,估計還有其他位份的娘娘,等把她們娶進東宮,說的好聽太子是她們的丈夫,其實要她看,太子還不如那平康坊內的教坊女郎,尚且有五陵年少爭纏頭②,擲賞錢,太子還得自己倒貼錢。
皇后見崔姣一臉老實,很滿意,雖生了副豔美嬌人的容貌,人卻本分,沒什麼叫人煩心的。
“三郎身上有傷,回去養著吧,崔姣暫留我這裡,陛下那邊有我,你不必管。”
崔姣立時鬆氣。
苻琰起身告辭,臨去時乜了崔姣一眼,那一眼太快,崔姣也辨不清他是何意。
不久,皇帝果然叫大公主去見他,皇后與過來的內侍叮囑,大公主今早便身體不好,召來太醫診脈,直說大公主鬱氣攻心,沾染了風寒,崔姣與大公主交好,自願來服侍大公主,讓皇帝等個幾日,大公主病好了,便帶著崔姣過去見他。
大公主生病,皇帝再因她與大駙馬置氣,也想來看望人,但被皇后一句,大公主現在什麼人都不想見給堵了回去。
崔姣在皇后的蓬萊殿也沒閒著,她找宮女要了各色絲繩,每日大公主和她埋怨大駙馬薄情寡義時,用來結綵縷打發時間,不然她耳朵都快起繭子了。
大公主養尊處優,這些東西她從沒做過,但崔姣結好了彩縷,她就認得出這彩縷是七夕那日要戴在身上避邪祟、招好運的,連連誇崔姣手巧,於是崔姣第一個結好的彩縷就只能送給大公主了。
崔姣又給皇后送了一個彩縷,自己和阿兄留一個,太子也留一個。
等到了七夕日,大公主不能去參加乞巧宴,她也不能過去,只有皇后一人去赴太液池的宴。
那時天才矇矇亮,崔姣起的很早,央告一位小黃門,讓他帶她到玄武門等候苻琰。
清早有霧,遠遠見太子在玄武門前下馬,卸了腰間佩劍,踏步入內,便歡喜的揚起手招了招。
她人在霧中,靈秀姣美宛若姑射仙子,臉上笑容異常明媚。
苻琰腳步微頓,驀地踱過去,淡道,“何事?”
崔姣忙從荷包裡取出彩縷,笑道,“妾給殿下做了彩縷,想為殿下戴上。”
苻琰盯著那條彩縷有些許恍惚,從他的傅姆死後,他已經有許多年沒戴過這東西,都快忘了它長什麼樣子,卻仍記得記憶裡有個人,給他戴了彩縷,摸他的頭,說一句歲歲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