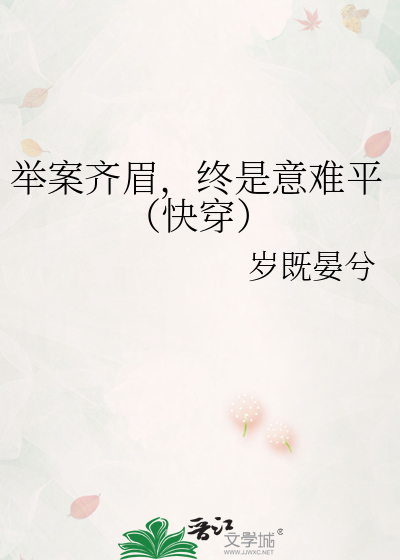火燒花果山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崔姣在苻琰處碰了壁,直生悶氣,但苻琰是她的主子,生悶氣也只得憋著,該當的差也少不了她,只能開心點想著,雖然苻琰沒有招她阿兄為食客,但他應該會幫她造藉,至少可以先和崔氏長房分戶了。
崔姣等了小半月,造藉的事一直沒音信。
正到了休沐日,苻琰有空休息,因他是習武之人,不能長久鬆懈懶怠,未傷時,早晨還會打一套拳,如今傷勢見好,拳不能打,宜於養生,遵照醫師的囑咐,每日晨間練半個時辰的五禽戲。
崔姣杵崇文殿殿門前,瞅著他把那套五禽戲練了足有五六遍才停下,忙遞上巾帕讓他擦汗,抽空小聲問他,“殿下給妾造藉了麼?”
苻琰一頓,擦完了汗,看也不看她,自坐到廊下茶床旁,等著她煮茶飲用。
崔姣再傻也明白了,他這是不打算給她造藉,先前是糊弄她的。
崔姣坐到他身側,才拿出茶餅,便落淚,兩隻眼都紅了,低頭斷斷續續發出小小的哭腔,“……沒有這麼欺負人的。”
廊下還站著女史,她一哭,那幾個女史不用指示,紛紛自覺避遠了。
苻琰擰著眉瞥崔姣,垂著的兩排睫毛都被眼淚沾溼了,啪噠啪地的掉眼淚,嘴裡嘟嘟囔囔,只敢小聲埋怨,“說好的又騙人。”
還太子呢,說話像放屁。
她連鼻尖都哭紅了,朝陽的光縷映照在她臉上,猶如粉邊堆雪玉雕的白瓷甌,剔透緊緻又羸弱。
苻琰不耐煩的敲茶床,“孤渴了,煮茶。”
渴死你最好!
崔姣往爐子裡添炭,引燃了炭火,哭的眼淚模糊了視線,不小心把手給燙了,疼的直抽氣。
她抱著燙紅的手哭得更慘了,還摸索著要給他煮茶,這要是煮下去,茶水裡都是她的眼淚。
換其他時候,苻琰必定要斥責兩句,然現在確實是他不對,答應人家的事沒做到,任她哭一陣就算了。
苻琰道,“你下去吧。”
崔姣爬起身,還不忘行退禮,迴廊房哭去了。
苻琰自己動手煮茶,煮出來的茶水索然無味,喝幾口便覺沒意思,撤了茶床,換一身常服出東宮,往長安的折衝上府①去巡視了。
至晚間方歸,這事沒放心上,夜裡理政時還召人來跟前侍奉,可崔姣顯然在這事上過不去,兩隻眼都哭腫了,坐到他身邊繼續落淚。
哭的苻琰定不下心,又讓她出去,她也乖乖走了。
她這副哭相有了一兩日才消停,後面人也沉寂了,只要出現在他面前都耷拉著臉,只做事,不再跟他討嬌,擺明了是與他鬧脾氣。
就這點小事,沒完沒了。
說到底就是個侍妾,柔順情深確實讓苻琰熨帖,但仗著寵愛再這麼鬧下去,苻琰也煩了,已經在思索,不如就此放出去的好。
他有了這想法,本來應該立刻放人,正趕上皇帝要過千秋節,朝堂內外都有的忙,地方藩王、外國來使都匯聚長安,南北衙各處軍士都需打起精神防衛,皇帝過生辰,苻琰肩上擔子更重,一時分不出時間來放人。
這日下雨,家令打著傘迎苻琰下軺車,苻琰剛從大明宮回來,有許多事情要交代他,兩人沿著宮道匆匆回內殿,轉過前步廊,遠遠見山水池上得湖心亭中,崔姣領著女史在躲雨,家令正要叫人去送傘,卻見郭守山一路小跑進亭中。
苻琰腳步一停。
家令度量著他得神色,不像高興的樣子,只能乾站著,不好提醒。
那亭中崔姣也沒想到會碰到郭守山,與他見禮後,笑問他從何處來。
郭守山還和之前一般靦腆,說,“去書齋買了紙筆,並一些雜物。”
崔姣好奇道,“郭夫子為殿下修《水經》,怎麼還會缺紙筆?”
郭守山道,“纂修《水經》不缺紙筆,是某自己用的。”
他顯得過於老實,都做了苻琰的食客,就是借修《水經》的紙筆用用,也不會有人說什麼,他分的這麼清,可見苻琰挑對了人。
崔姣想到苻琰就慪氣,這幾日下來,她跟他不對付,也沒見他鬆口為她造藉,定是鐵了心不幫她了。
心裡氣不能發出來,還要服侍他,她苦悶了好幾天,今日苻琰不在才想來園圃轉轉,不想下這麼大雨。
看向郭守山身上背的書袋,郭守山忽想到自己在西市買了些單籠金乳酥,忙取出來道,“這是某在東市買的,崔掌書若不嫌棄,請嘗一口。”
崔姣一來長安就進了東宮,沒機會品嚐外面的美食,聽他這麼說,便大大方方的伸手過來揀一塊單籠金乳酥來吃,纖纖玉手,指尖掐粉,拿那塊糕時,郭守山的心跳都不覺加快,唯恐輕薄了佳人。
單籠金乳酥十分香軟酥糯,崔姣道了句好吃,問他這是什麼菓子。
郭守山答了,紅著臉說,“某也是隨手買的,崔掌書帶回去吃吧,若、若喜歡的話……”
他不是寬裕的人,崔姣也不好意思收他的東西,躊躇要拒絕。
橫街上,苻琰臉色又黑又沉。
家令試探道,“僕叫人去送傘吧。”
苻琰抬了抬下巴。
家令忙命一小僕送傘過去。
小僕跑到亭前,衝他們喊道,“崔掌書、郭夫子,太子殿下叫下僕來給你們送傘。”
崔姣這才看見苻琰站在橫街上,拉著張臉,彷彿她又做了什麼不可饒恕的事情了。
崔姣先謝過郭守山,拒收了菓子,跟著她的玉竹接過小僕遞來的雨傘撐起來,和她手攙著手一起離開。
郭守山免不得片刻落寞,舉袖向苻琰方向行了拜禮,也接了小僕的傘,離亭走了。
崔姣走至苻琰身側,正欲襝衽施禮,苻琰沒看她一眼,抬步就走。
崔姣咬了咬唇,她做錯什麼了,怎麼有人自己騙人還要給被騙的人臉色看,憑他是太子就可以這麼過分!
崔姣也只能腹議幾句,跟著他回去了,本來還以為要在他跟前侍奉,結果讓她迴廊房安生待著,不許亂跑,崔姣忍忍氣,不亂跑就不亂跑,在廊房舒服的很,總比伺候他強。
千秋節依例有假三日,崔姣閒的沒事幹。
苻琰一早就往大明宮去了,崔姣破天荒睡遲了,用過朝食,女史們本來應該撤走食床的,但是廚下送了不少茶水菓子來,說是千秋節,聖上與民同樂,照著以往的規矩,送來這些吃的大家一起享用。
崔姣便和女史們圍著食床一起談心。
“往年的千秋節都特別熱鬧,陛下在花萼樓宴請百官,群臣獻甘露醇酎和萬歲壽酒,王公貴戚身上都要佩戴金鏡,士人庶民也要隨身攜承露囊,外國使節還會進獻許多珍奇寶物!”
“現在花萼樓的壽宴大概已經開了,宴上一定有舞姬跳霓裳羽衣舞,還有角牴萬夫,跳劍尋撞,蹴球踏繩,舞於竿顛②這些有意思的百戲!可惜咱們瞧不見。”
崔姣趴在茶床邊,枕著腦袋道,“我看殿下都忙的團團轉,咱們就是去了花萼樓,也是伺候人,哪有功夫看百戲呢?”
南星點點頭,“掌書說的對,能在千秋節這日舒坦的,也只有聖上了。”
皇帝有美人相伴,時常歌舞奏樂,哪日不舒坦了,倒是苻琰這個太子累死累活的。
木香啃著手裡的桃子,張著大眼睛問道,“下僕聽其他姊姊們說,千秋節上還有外邦進獻美人!”
“是有這事,送來的多是外邦公主,要不進宮成了陛下的妃嬪,要不被陛下指給哪位親王權貴,”玉竹道。
崔姣那雙多情眸彎了彎,“那會不會指給殿下呢?到時候咱們東宮就有一位外邦太子妃了。”
幾人被她逗笑。
南星道,“掌書莫說笑,外邦的人如何能做太子妃。”
崔姣嗯了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③,皇后殿下鐘意的太子妃必定是長安內最賢惠得體的貴族女郎了。”
三人見她說起太子妃並無吃醋拈酸之意,都暗暗稱奇,她不會真的不喜愛太子殿下吧,這樣也不錯,以後東宮進了太子妃,就算失去太子殿下的寵幸,她也一樣能過的很好。
四人又說其他趣事,再把茶點吃了,才各自散開自己找樂子。
--
千秋節這日,苻琰忙碌至夜間才回了東宮,聽家令稟報廊房動靜,崔姣一整日都沒出來過,也沒來崇文殿尋過他,從她入東宮以來,除了之前對東宮不熟不敢亂跑外,後面熟了,自己來崇文殿找他,常常黏在他身邊。
從那天她鬧彆扭後,只要他不召人,她就不來,還吃別的男人手裡的東西。
只消一想到崔姣面對郭守山巧笑嫣然,苻琰便難以扼制胸腔裡惱火,他想,一個侍妾而已,最初帶她回東宮也只是一時有用處,時至今日,她早已沒什麼用處了,不過是嘴甜,不過是那點溫情脈脈。
他沒什麼好留戀的,他也不該留戀。
苻琰自此決定將崔姣冷落。
不召見也不詢問她的一切,就當東宮沒這個人。
崔姣也發覺了他不再召她去黽齋夜伴,她本來是在氣頭上,在廊房窩了兩日後,自己慢慢把自己勸的氣消了,她人在東宮,不說以後,至少目前身系苻琰,惹惱了他,被趕出東宮,她無法在長安存活,也回不去清河。
苻琰是她得罪不起的人。
崔姣想通後,便主動去找人了。
此時才過完七月,將將八月初,夜晚已經涼下來了,崔姣站在黽齋前,聽家令傳話,“殿下說以後晚間不需崔掌書隨身相伴,崔掌書回去睡吧。”
崔姣仰起頭,眼眸中浸著淚,“殿下真是這樣說的嗎?”
小娘子眼含淚的可憐像很叫人心軟,但是苻琰已經決定的事,誰也不能做改,家令點了點頭。
崔姣便像霜打的茄子,垂下腦袋往回走,早說苻琰這人惹不起,這幾個月來她好不容易才讓他心裡稍微在意一點,現在又變成原先不近人情的死模樣。
崔姣有點後悔了,她想要的東西都靠他施予,她哪有跟他使性子的底氣,弄成現在這樣,她也不知道怎麼辦了。
只能先回廊房,再想想別的辦法吧。
--
直過了兩日,果然如家令所說,苻琰真不叫她去伺候了,崔姣漸漸變得苦悶,女史們也發現了,便又想著,太子只是兩日沒喚她過去,她就發愁了,可見之前是她們想錯了,她是愛慕太子的,只是因為一直有太子寵愛,所以才會不當回事,一旦失寵,她就難過了。
可是如果真的失寵,她難過又有什麼用呢。
女史們只能報以同情,往好處想想,就算太子不疼她了,她也還是內坊掌書,有月奉拿有她們陪伴伺候,不也挺好的嗎?
到第三日,崇文殿那頭忽有一僕過來廊房傳苻琰的話,讓她隨他去襄王府赴宴。
苻琰竟然帶她去赴宴。
崔姣欣喜道,“容我去換身衣服。”
小僕道,“殿下說,崔掌書就穿女官服過去,因是襄王府遞了請帖來,特邀您和殿下一同過去。”
崔姣眼裡一暗,原來不是他想要她去的,她一個小小女官,還跟襄王有過過節,襄王邀她去赴宴,赴的是鴻門宴吧。
崔姣不想去,但見小僕催的緊,不去也得去,只好硬著頭皮跟他一起走。
太子凡出行必乘軺車,崔姣沒資格坐軺車,坐在後面的馬車裡,至襄王府,下車時見苻琰根本不等她,已經。
她此刻對苻琰的怨念到了極致,既然不待見她了,找個由頭不帶她過來,襄王還能說什麼。
她小跑近苻琰,咕噥了聲殿下,不見苻琰回頭看她,在心裡哼了聲,便跟著他到門前。
襄王苻承澤和一個一臉黑鬍子、長相異域的男人迎上來,襄王先帶著那個男人向苻琰行禮,然後看向崔姣,咧嘴笑道,“崔掌書咱們又見面了,這位是大食國王子陀婆離。”
苻承澤又和那位陀婆離說了下崔姣,陀婆離身邊的舌人幾里哇啦一桶,陀婆離頷了頷首,一雙牛眼對著崔姣打量,視線既讓崔姣不舒服,崔姣想躲到苻琰身後。
苻承澤卻道,“陀婆離王子聽聞崔掌書很會打馬球,對崔掌書十分佩服,等會席間,還請崔掌書再露一手馬球功夫。”
崔姣察覺到了他的不懷好意,一時想不出理由拒絕。
苻琰忽道,“她身上有傷。”
苻承澤故作關心,“崔掌書傷在何處,因何傷的。”
苻琰那張唇微微動,“為了五孃的名聲,襄王真要孤說出來?”
苻承澤當即領會,她是那次和大公主合謀設計鄭孝饒傷的,鄭孝饒人在獄中,五公主也在公主禁足,這事不能提,遂罷休,領著他們一起進王府。
宴席擺在後堂,崔姣第一次來襄王府,進來才覺這座府邸非常大,府內更是隨處可見奇花異草,越朝裡越聞到沉香味,至後堂,即見那湖邊亭竟是沉香木所制,沉香木何其珍貴,襄王府竟然造了一個亭子,苻琰平日薰香都極少用沉香,這也太奢侈了。
待進後堂,崔姣陡覺一陣涼意,入目是立在松樹盆栽旁的風松石,這石頭比東宮那塊還要大一點,已經看不出風松石的雅緻,被雕刻成了蟒形,只有其上松樹紋理依稀可判斷是風松石。
崔姣暗暗想著,皇帝真偏心啊,這麼大的風松石竟然給了襄王,她以為崇文殿內那塊要大一些的,而且襄王還敢將風松石刻成蟒,誰不知蟒乃無爪之龍。
襄王想成為太子的心真是昭然若揭。
她看苻琰並無喜怒,似乎這些都已經很常見了。
襄王引他們入席,崔姣是苻琰的女官,不好坐席上,只能站在苻琰身側,看著那一道道炊金饌玉呈上了席案,隨後襄王拍手,僕役們端了個鐵架和鐵籠到堂中。
“我近來品嚐到一道美味,名叫鵝鴨炙,特請三哥和陀婆離王子賞鑑一番。”
苻承澤拍了拍手,婢女開啟了鐵籠,在籠子上鋪一層調料,隨後點著籠下炭,再將活鵝活鴨放進去。
那可是活生生的鵝,在鐵籠裡被火烤的又叫又跳,苻承澤和陀婆羅離邊看邊哈哈大笑。
空氣中都能聞到調料香,崔姣卻幾欲作嘔,但見苻琰面色無常,自己也不能表露噁心。
“襄王的癖好非一般人忍受,孤不喜這道菜,可以撤走了,”苻琰抿了口酒,淡淡道。
苻承澤道,“三哥沒吃過自然不喜歡,等吃了就會喜歡了。”
苻琰勾唇,“孤不喜歡。”
苻承澤看他雖笑,卻冷冽,現今朝政有大半捏在他手中,皇帝年歲上去了,已不甚處理雜政,朝中擁護他的居多,苻承澤仍處劣勢,今日這宴,也不是要與他撕破臉。
而是為了五娘報仇。
苻承澤揮手叫人把鵝鴨鐵籠抬走了,隨後舞姬們從側門魚貫而入,堂中絲竹樂聲起。
崔姣觀察到那些舞姬跳的是胡旋舞,褐發碧眼,蒙著面紗扭動著曼妙細腰,像西市裡見過的酒家胡,但沒有酒家胡面板白皙。
這是大食國來的舞姬吧。
像是應證她的猜測,領頭的舞姬轉動著身體到苻琰的食案前,熱情的展示著她的舞姿。
但是苻琰一直低頭慢慢品酒,舞姬得不到他的目光,只能退回場中,將胡旋舞跳完,然後解了面紗,是個非常豔麗、膚色微黑的異域美人。
陀婆離與舌人在說什麼話,半晌,舌人向苻琰行叉手禮,道,“太子殿下,陀婆離王子對您身後的女官一見鍾情,他想用舞姬跟您換這位女官。”
崔姣僵住了,這大鬍子想要和苻琰換她,如果苻琰答應了,她就要背井離鄉,跟著大鬍子去大食國。
她這時候才明白過來,為什麼襄王會邀她過來,苻琰會帶她來,大鬍子是大食國的王子,大食國與大梁多年友好,這大鬍子想要她,苻琰很可能就會把她送出去。
崔姣臉都嚇白了,瑟縮著看向苻琰。
苻琰喝完杯子裡最後一口酒,抬起了頭,衝陀婆離露出一個似有若無的笑,說,“孤的女官不送人。”
崔姣緊緊交握的兩隻手都是汗,因這句話放鬆,竟破天荒覺得,即使他不是個好伺候的主子,但至少他沒想把她送人,他是個好人,她在這一刻,是感激他的。
陀婆離露出一副失望的表情,又唧唧哇哇說了一通,然後起身向苻琰再行個不倫不類的退禮,就帶著他的舞姬走了。
苻琰也起身道,“多謝襄王招待,孤還有政務處理,不便久留。”
苻承澤叫住他,“三哥,這不是我的主意,是陀婆離聽人稱讚崔掌書,所以才要我做東來請你們。”
苻琰冷淡的嗯一聲。
苻承澤聲調稍微低了,“三哥,五娘已經被關了一個月,她知道錯了,想跟長姊賠禮道歉,你能不能與長姊知會一聲?”
苻琰掀起眼看他,“襄王都開口求孤了,這個話孤會替你告訴阿姊,只是阿姊原不原諒五娘,要看她的意思。”
苻承澤心裡暗恨,朝他彎腰拜了拜,“多謝三哥。”
苻琰心安理得的受著,轉身帶崔姣離開襄王。
回東宮剛過未時,崔姣跟在苻琰身後進了側殿,側殿內有溫湯,苻琰沐浴從不喜她進來,這是她第一次進。
他們繞過了山水鎏金屏風,苻琰脫了長靿靴站上紫茭席,朝她張開手,示意為他褪衣。
崔姣抖著手解掉腰帶,撥開他的上衫,結實的胸膛一點點袒露出來。
片刻要解褲子時,她的臉被一隻手給託了起來,她忽覺得腿軟,不受控制的往席上坐,她的臉還被那隻手託在手心裡,手的主人一寸寸觀摩著她,從臉到頸再往下,最後再重回到臉。
苻琰的酒意有點上來了,思緒也放開,其實陀婆離提出要她時,他有過動搖,但也僅有那瞬息間的動搖。
因為他發現,他捨不得。
所以他要徹徹底底打上自己的印記,任何人都不能覬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