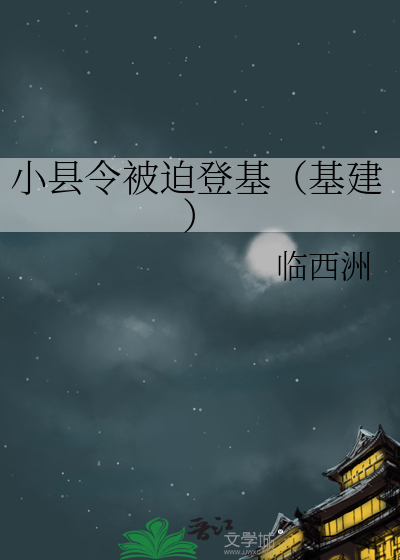初雲之初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作為老夫人院裡的人,她很清楚前者是不是真的身體有恙。
馮四夫人早知道會如此,覷了她一眼,冷笑出聲:“若老夫人這病是假的麼——”
那婆子不由自主的叫了聲:“四夫人。”
馮四夫人反倒不看她了,只問丈夫:“夫君現下官居幾品?”
馮四爺怔了下,方才道:“從四品。”
馮四夫人又問:“是在什麼衙門當差啊?”
馮四爺已經明白她想幹什麼了,當下苦笑著摸了摸下頜的鬍鬚:“清水衙門。”
馮四夫人再問:“還有可能入三省為宰相嗎?”
馮四爺長舒口氣,嘆道:“不可能啦!”
馮四夫人便猛地拍一下桌案,但聽“砰”的一聲響,桌上的盤子碟子都震了三震:“咱們大姐乃是宮中太后,何等尊貴?大哥更是尚書僕射,當朝宰相!拔根寒毛都比你腰粗!人家正經的邢窯白瓷都不怕,你個破罐子怕什麼?!”
“真要難看,那大家就一起難看!大不了我去敲登聞鼓,叫滿長安的人都來瞧一瞧看一看,給馮家這事兒評評理!咱們怕丟臉,別人便不怕?幾個臭光腳的,還替人家穿鞋的擔心起來了,也不撒泡尿照照,咱們有這個資格嗎?!”
那婆子聽到此處,已經慌得站不住腳,連聲道:“夫人息怒,息怒啊!常言道家醜不可外揚,都是一家人,何必鬧成這樣?”
馮四夫人嗤了一聲:“喲,你也知道醜啊?!”
繼而神色一轉,疾言厲色道:“真要是想鬧,那咱們就乾脆鬧個天翻地覆!我不怕丟臉,但願府裡其餘人也不怕!我有手有腳,嫁過來的時候孃家也不是沒陪送嫁妝,離了馮家還能被餓死不成?大不了就叫夫君辭了這個清水官兒,找家書院教書去!”
“我勸你先去問問大老爺,看他還記不記得四書五經?在朝廷上鑽研之餘,閒來無事的時候也翻翻舊時書卷吧,備不住哪天雞飛蛋打了,能用得上呢!夫君先他一步去教書,備不住能做個院長,到時候顧念兄弟情誼,倒可以提攜他一二!”
那婆子只是訕笑,卻不敢作何評論,呆站在一邊,手搓著衣袖,不知該如何是好。
馮四夫人見狀,皮笑肉不笑的問她:“喲,光顧著說了,卻忘了問你,老夫人她還病著嗎?”
婆子趕忙道:“好了,好了!老夫人身體康健,病痛全無!”
馮四夫人冷哼一聲。
馮四爺用手帕擦了擦腦門上的汗,褒讚不已:“夫人真是華佗在世啊!”
第12章
那婆子遭逢四房夫妻嘎嘎亂殺,力有未逮,倉皇逃竄。
馮老夫人只見她回來覆命,卻不曾見馮四夫人這個兒媳,臉色隨之一沉:“老四家的呢?難道她真敢把我的話當耳旁風?!”
那婆子心下叫苦不迭,神色躊躇,為難不已。
馮老夫人見狀,聲色為之一厲:“她到底是怎麼回的?你一五一十的講!”
那婆子惶恐不已,再三告罪之後,方才躬著身子,小心翼翼的將馮四夫人的話講了。
馮老夫人氣個倒仰!
她十六歲嫁進馮家,從孫媳婦做起,現在底下已經有了孫媳婦,這麼多年下來,從沒聽聞過如此狂妄之語!
“好個四夫人,真真是好兒媳婦,竟敢威脅到我頭上來了!”
馮老夫人將面前茶盞摔在地上,霍然起身:“帶路,好叫我去瞧瞧你們四夫人的威風!”
那婆子蜷縮著身體候在底下,大氣都不敢出,見馮老夫人的陪房擺了擺手,趕忙見個禮,快步退出去了。
那陪房又勸馮老夫人:“四夫人是個混不吝的,一股小家子氣,您何必同她一般見識?且她有諸般不是,也總有句話是對的。”
馮老夫人道:“哪一句?”
陪房扶著馮老夫人重新坐下:“瓷器不與瓦罐鬥,不值當。”
馮老夫人合上眼,默默喘息了半晌,終於發出一聲冷哼:“且叫那幾個眼皮子淺的再蹦躂幾天!”
……
這一晚,四房算是同馮老夫人撕破了臉。
只是雙方出於種種思慮,都不曾將事態擴大化。
第二日,馮四夫人照舊往婆母院裡去請安,馮老夫人冷著臉敲打了兒媳婦幾句,也渾然不曾再提過生病侍疾的事情。
於是日子就暫且這麼糊塗著過下去了。
又過了兩天,馮四爺遞上去的奏疏得了批覆,翻開瞧了瞧,新帝只說了些“馮卿忠君體國”的車軲轆話,並不深談當下政局。
可馮四爺這上疏原本就是站隊,與朝局無關,這會兒見了這兩句話,一顆心也算是安了。
待到返回府上,私底下又寬撫妻子:“我觀當今天子近來動作,不似庸人,料想不會因馮家之事而遷怒蘭若,現下又如此批覆,可見蘭若無憂了。”
馮四夫人連唸了幾聲“阿彌陀佛”。
再想起這幾日大嫂不復往日親切的面孔,又不禁冷哼:“長房打得好主意,送我女孩兒進宮去吃黴頭,自己心裡邊不知道憋著什麼壞水兒,不成想倒叫蘭若得了前程,氣也氣死他們!”
……
四房揚眉吐氣,長房難免暗生陰霾。
馮珠娘坐在正房隔間裡做刺繡,心思卻飄到了隔壁。
那邊兒馮大夫人侍奉著丈夫改換常服,到底沒忍住,低聲問:“咱們這步棋,是不是走錯了?”
她期期艾艾,語氣中已經有了些許懊悔:“若當日被選進宮的是珠娘,承恩公府長房嫡出的女孩兒、太后娘娘嫡出的外甥女,必然是要做皇后的!可現在,常家的兒子不過是個六品官……”
馮珠娘聽得微怔,直到針尖兒扎破手指,方才猛然回神。
她將手指送到口中,輕輕吮吸。
那邊馮明達斥了一聲:“婦人之見!你懂什麼?”
說著,話音轉低,簾幕掀開,他到隔間來,瞧見了低著頭不語的女兒。
馮明達心下愈發不快,語氣倒還和煦:“珠娘,回去歇著吧,我有些話要同你阿孃講。”
馮珠娘溫婉一笑,起身道:“是。”
臨走前,馮明達又叫住了她:“珠娘,你別多思多想,阿耶如今做的,都是為了我們馮家。”
馮珠娘柔聲應了聲:“阿耶寬心,女兒都明白的。”
等她走了,馮明達的臉色方才徹底陰沉下去:“錯非你是幾個孩子的阿孃,錯非我不對婦人動手,剛才我就該給你一巴掌!”
馮大夫人不由得低下頭,語氣不無委屈:“你怨我做什麼?”
“方才我不知道珠娘在這兒,難道你也不知道?!”
馮明達壓抑住怒火,將聲音降低:“你心裡猶疑,大可以私下同我講,在珠娘面前說這些,除了亂了她的心思,叫她生出不必有的遐思,又有何益處?!你難道不知道,全家賭上性命做這件事,究竟是為了誰?!”
馮大夫人忽然氣餒,頹然坐到繡凳上,低低的抽泣起來:“夫君,我不知是怎麼了,這幾日總是在做一些不好的夢,我,我後悔了……”
她用帕子擦了眼淚,憂慮所致,一時難以為繼:“馮家簪纓世族,鐘鳴鼎食,富貴已極,何必再去謀求其他!”
馮明達冷笑一聲,見妻子如此傷懷憂愁,卻也不禁心生嘆息,坐到她旁邊,低聲道:“我難道便不怕嗎?可是怕有什麼用?馮家誠然鮮花錦簇,可你難道不知月盈則缺?”
他攬住馮大夫人肩頭:“我位居宰相,又是國公,太后娘娘無子,繼位新君與馮家又有何交情?馮家的顯赫與富貴,便是馮家人的催命符!若不趁機謀劃來日,難道引頸就戮?!”
“罷了,罷了!”
馮大夫人搖頭苦笑:“事到如今,哪裡還能回頭呢!”
馮明達沒有言語。
時值半夜,萬籟俱寂,只有一輪明月高懸,無聲的注視著世間萬物。
……
四房既然跟馮老夫人翻了臉,有些事情就不得不早做打算了。
父母在,不分家,現下馮老夫人還杵在這兒,她不開口,四房斷然沒有分出去單過的可能,只是現下兩邊兒既然鬧掰了,馮四夫人就得盤算一下分家之後該如何過活了。
大樹底下好乘涼,馮四爺生在馮家,總歸也是得了家族廕庇的,雖是庶子,自幼卻也不曾為銀錢發愁,因他頗有些讀書的天賦,馮老太爺一碗水端平,如前邊嫡子一般為他聘請名師,諸事都操辦妥帖,叫他無有後顧之憂,這才有他少年登科、得中進士的榮耀。
之後他外放為官,頗有政績,三十五歲便成為一州刺史,雖是下州,卻已經是從四品官位,就這前程而言,馮家也是出了力的,只是後來……
不提也罷!
此時他任職的鴻臚寺是個清水衙門,政令多仰承禮部,而禮部又歸屬於尚書省,馮明達如今官居尚書右僕射,妥妥一個閉環,把他四弟拿捏的死死的。
只是這會兒馮四爺蹉跎數年,也沒了年輕時候的豪情壯志,馮家的名望是榮耀,也是枷鎖,離開了也好。
此時見妻子坐在妝臺前翻閱陪嫁的賬目,細細盤算自傢俬房,他臉上不由得浮現出幾分柔情:“只是委屈了夫人。”
馮四夫人笑:“這有什麼好委屈的?我阿耶如今也不過是個五品官,天下較之馮家遠遠不如的多了去了,難道都不活了?”
頓了頓,又說:“我倒願意離了這是非之地,去過些安生日子,便是清貧些,也是不怕的。”
馮四爺想了想,點頭道:“倒也不無不可。”
他說:“我生於高門,少年登科,妻賢子孝,官場也曾得意過,很可以知足了。待到此間事了,便辭官去做個教書先生,卻也很好。”
馮四夫人不無詫異:“我那晚說的都是氣話——”
馮四爺語氣不無喟嘆:“官場上浮浮沉沉,我是真的有些累了,去歇一歇也好。再則,今上經了太后娘娘一事,怕也不願叫后妃母家高踞朝堂,我自行退去,對蘭若而言也是件好事。”
馮四夫人神色微動,一時無言,正在此時,卻有僕婢急匆匆在外通稟,喜不自勝:“老爺,夫人,宮裡內侍來府上傳話,陛下嘉賞昭儀娘娘侍奉太后娘娘純孝,晉封娘娘為淑妃了!”
馮四夫人與丈夫俱是一驚,繼而齊齊面露喜色,匆忙更衣往前院去謝恩,卻見長房馮大夫人並珠娘也是匆匆而來。
視線碰撞到一處,幾人神色各異。
馮大夫人執掌馮家內宅多年,卻是頭一次被人搶了風頭,偏生她還不能說什麼怪話,只能儀態得體的微笑——封淑妃的畢竟是四房的女兒。
內侍又講:“淑妃娘娘在宮中一切都好,只是惦念家中親人。奴婢離宮之前,娘娘特特叮囑,此次命婦入宮謝恩,要請長房的堂姐一道前去,姐妹久不相見,思念不已。陛下讚許淑妃娘娘友愛姐妹之心,特旨準允。”
馮大夫人眼皮子猛地一跳,下意識同女兒對視一眼,行動上卻不遲疑,齊齊拜謝天恩。
馮老夫人年高,又是皇太后的生母,是不必親自到前院來的,稍晚些聽大兒媳婦講淑妃傳召長房孫女珠娘一道入宮,不禁微微挑眉。
“她這是怎麼個意思?”
馮大夫人道:“兒媳也猜不透呢。”
馮老夫人既厭惡庶子,也厭惡庶子媳婦,更不會對庶房的孫女心存好感,聞言便譏誚道:“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區區一個淑妃,便叫她歡喜的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誰了!”
她是有資格說這句話的,她的女兒入宮之後先為皇后,之後又做了皇太后,自然看不起區區妃位,馮大夫人卻不可以,便只是微笑著侍立一側。
馮老夫人見狀,又寬撫她:“宮裡邊有太后娘娘在,一個黃毛丫頭,翻不出什麼浪的,只管放心去便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