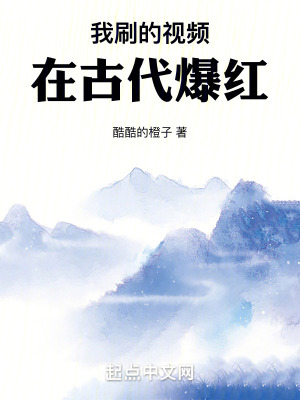懸姝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回應她的是從茶坊快步走下來的歸言。
“二小姐,公子讓屬下送您回府。”他偷偷抬眼用餘光瞧了一眼沈觀衣,見她順從的點頭,心下稍緩。
在探春的攙扶下,沈觀衣踏上馬車。
相較於她們先前那隻能容納三人的小馬車,李鶴珣這輛則要寬敞的多,內裡的小櫃微微敞開,裡面放著幾本泛舊的遊記。
探春突然雙眸一亮,“小姐,你聞到什麼味道了嗎?”
圓潤的鼻尖如貓兒般輕輕聳動,沈觀衣驟然明白過來探春說的味道是什麼,“這馬車內燻過香。”
那是李鶴珣喜歡的香味,如冬日雪松,凌冽淡雅,他的物件兒上幾乎都沾著這種味道,用她的話來說,便是這麼些年早就給他醃入味了。
前世她有一段時日想學著上京貴女們弄香,彰顯自己的高雅,於是每日晌午李鶴珣處理公務時,她便懶洋洋的趴在他身上折騰給他抹香,互不耽誤。
無論多濃烈的香味,最終似乎都會消散,除了他身上的松香。
後來她才發覺,不只是李鶴珣,上京貴族子弟,薰香便如同飲茶一般尋常,那是身份的象徵,更是為了區別世家與寒門的不同。
沈觀衣瞧了一眼探春沒見識的模樣,想來她先前應該從阿讓那裡學到不少上京城的規矩,所以才會自己琢磨著在她的衣裳被褥上薰香。
眼下觸及到了她不知曉的規矩上,正是新奇的時候。
歸言見裡面遲遲不曾說話,方才在心中打好的腹稿忍不住溜了出來,“二小姐,您身上的傷沒事吧?”
沈觀衣回過神來,聽阿讓一問,這才察覺到肩胛蔓延至腰窩那一片有些疼,她頓時蹙眉,“有事。”
歸言握著韁繩的手一緊,回想起方才公子的囑咐,訕笑道:“屬下認識一個大夫,能活死人肉白骨,治傷更是不在話下,待屬下送小姐回府後,便叫那人來給小姐瞧瞧。”
“好啊。”
“不過那位大夫吧,脾氣有些不好,不喜歡不聽話的病人,到時候恐怕小姐還需多擔待。”
脾氣不好?能有多不好?
沈觀衣不以為然。
半個時辰後,沈府。
紗帳被纖細的手指猛地掀開,沈觀衣怒道:“你讓我半月之內足不出戶,臥床休養?”
“我是殘了還是遭了內傷,不就背上淤青一片,那也並不影響我平日走動啊。”
說罷,她狠狠的瞪向一旁的歸言:這就是你找來的庸醫?活死人?肉白骨?
治死人差不多!
歸言心虛的別開頭,不敢吭聲。
大夫面不改色的收拾桌上的瓶瓶罐罐,頭也不抬的道:“小姐的傷勢瞧著沒有大礙,但再耽擱下去,就會傷到骨頭。”
“傷筋動骨一百天,小姐是想修養半月還是三月,但憑您自個兒做主。”
沈觀衣不說話了,狐疑的瞧著大夫,“你的意思是我現下並未傷到骨頭,那為何耽擱下去便會傷到了?”
“信與不信在小姐自己,多說無用,老夫能告知小姐的便是,若傷到骨頭,那滋味比之嗜心剝皮也差不了多少,小姐不信,也可以另請高明。”他雙手抱拳,揹著小箱子便要走。
嗜心剝皮之痛……
想起那時的滋味,沈觀衣面目蒼白,哆嗦著唇,顫著音兒喚道:“等等。”
大夫回過頭來,見沈觀衣與先前張牙舞爪的模樣大不相同,眸中竟帶著殷殷懇求,“若我聽你的,你能保證我不會、不會……”
見他緩慢的頷首,沈觀衣頓時鬆了口氣,抿著唇重新躺在床上,自己乖乖的將被子捏在腋下,對著大夫討好一笑。
“小姐要記得按時服藥,藥膏也不能斷,否則……”
“放心。”沈觀衣信誓旦旦,眉眼認真,“我很聽話的。”
歸言見此,總算卸下了心中的重擔,與沈觀衣告辭後,親自送大夫離開。
二人走至沈府外,歸言才笑道:“此事多謝於大夫了。”
“好說。”於大夫提了一把肩上的藥箱,見歸言欲言又止,明白他想問什麼,“二小姐身子無礙,背上也都是尋常傷。”
“那您方才開的藥?”
於大夫笑道:“自然是玉肌膏與安神補氣的藥,對二小姐的身子無礙。”
“那在下便替公子多謝於大夫了。”
等他擺手離去,歸言才沉沉的吐出一口氣,回茶坊覆命。
這頭,沈觀衣因擔心背上的傷,自大夫離開後,便整日待在沈府,不曾踏出院門一步。
中途,她也想過會不會是這大夫瞧錯了,甚至想要讓探春再找個大夫來瞧瞧。
但她向來信壞不信好,便是再找一個大夫來,她也不見得便全心全意的信那人,於是猶豫來去,十日已過。
探春日日在她跟前唸叨,數著婚期還剩下幾日,生怕到時候她身子沒養好耽擱了事兒。
沈觀衣倒是不在意,整日不是窩在院兒中的軟榻上曬太陽,便是在窗邊撫琴哼曲兒。
這日,天剛大亮,繡坊那邊便派人送來了嫁衣。
文錦紅袍上的繡工精緻,豔的灼眼,與前世那件一般無二。
突然,沈觀衣想起了什麼,將目光從嫁衣上移開,看向她跟前的繡娘,“你們繡坊叫什麼名字?”
“回小姐,是三彩繡坊。”
上京做工最細緻,卻也最難等的繡坊,平日哪家公子小姐要裁個衣裳都得等上十天半個月,而這樣一件繁瑣的嫁衣,少則三月多則半年,怎會如此快……
“這件嫁衣,你們從什麼時候開始做的?”
繡娘垂首,“回小姐,一月前。”
沈觀衣漫不經心的從雲線上撫過,“一個月,你們便能趕製出這件衣裳?沈家給了多少銀子?”
“不是沈家。”
沈觀衣先前在聽見三彩這個名頭時心中便已然有了猜測,但仍舊忍不住抬頭看向她,聽她緩緩說出從心中輾轉而過的名字,“是李大人親自吩咐的。”
果然是他。
前世她對上京算不得熟,更不知三彩繡坊出來的衣裳在上京是怎樣的存在,直至後來她的身份跟著李鶴珣水漲船高,她的衣裳全都出自三彩繡坊與宮中繡娘時才知曉一套精緻的衣裳需要多長時間,後來更是發現那套嫁衣,竟也是三彩繡出來的。
李鶴珣。
貝齒之中反覆咀嚼著這個清風朗月的名字,沈觀衣突然笑了。
原來前世她出嫁當日出的醜,竟不是因這嫁衣,而是某些用心險惡的人啊。
比起讓她相信李鶴珣在嫁衣上做手腳,不若相信唐氏母女吩咐了將她背上花轎的庶兄,刻意給她使絆子,令她在眾人前衣衫不整,差點就此毀了兩家姻親。
“知曉了,嫁衣留著吧。”
繡娘走後,沈觀衣施施然起身,琢磨著背上的傷已經好的七七八八了,這兒離唐氏的主屋算不得遠,走這兩步應當沒什麼。
比起成親當日丟臉,有些事不若提前打點清楚的好。
-
沉檀院中,石榴花出奇的紅豔,蜜蜂自遠處飛來,穩穩的停在花蕊上。微風徐來,斑駁花影間,唐氏與沈觀月正坐於院中的石凳上飲茶。
砰——
茶底狠狠的嗑在桌上,水漬翻湧而出,紊亂的灑在石桌與手背上。
唐氏咬牙道:“她怎就如此命好!”
“娘……”沈觀月想安慰,卻不知從何說起,因她心中也難受嫉妒的厲害。
“當初就不該心軟,以為將她送去莊子上自生自滅便能安枕無憂,早知道就該讓她與柳商那賤婢一起去死。”
沈觀月怕唐氏氣傷了身子,起身行至她身後,掌心溫熱,貼在她背上,順著她的氣兒。
“娘,她既馬上就要嫁入李家,咱惹不起還躲不起嗎,您彆氣了,當心氣壞了身子。”
“嫁入李家怎麼了?”唐氏眼底鑽出一絲恨意,“不到最後關頭,她能不能嫁過去還兩說呢!”
沈觀月頓時蹙眉,看向一旁不動聲色,專心侍奉的冬暖,“冬暖姑姑又給您出什麼主意了?”
“爹爹這兩日可告誡過您不少次,您也知曉爹爹有多在意這門婚事,若在您手上出了岔子,爹爹一定會……”
“放心。”唐氏眼尾得意的上揚,“你爹找不出我的錯處,就算怪也是怪在別人身上去。”
一箭雙鵰,既除了那妾氏與她底下不成器的庶子,又能毀了沈觀衣的名聲,讓她自此無門,任由拿捏。
沈觀月心中一喜,“當真?”
唐氏揚著唇,抿了一口茶,對上冬暖肯定的目光,頓時眉開眼笑,“自然是真的。”
“太好了。”沈觀月激動的扯到了還未痊癒的傷口,但那處再痛,哪能比得上這則訊息令她痛快。
“來,祝咱母女能一雪前恥。”
唐氏心情極好的端起茶盞,以茶代酒,似乎只有如此才能疏解心中徘徊的興奮之情。
茶盞相碰,二人彷彿已經預見了之後的情形,相視一笑。
伴隨著清脆的聲音響起,不遠處遙遙傳來少女的輕笑,“什麼事這麼高興啊?”
那口茶還未嚥下,這道熟悉如噩夢的聲音便令二人臉上的笑容同時僵硬,只覺一股涼氣從腳底蔓延至心口,慌亂無措。
她什麼時候來的,聽到了多少?
饒是冬暖,都不由得慌了神,“二小姐,您怎的來了?”
沈觀衣瞧了她們一眼,在她們青白交加的臉色中,慢吞吞的從沈觀月的手中拿走茶盞,放在鼻下輕輕一嗅,隨即撲哧一聲笑了出來,“我還以為沈夫人與大姐姐高興的大白天便開始飲酒呢。”
“原來,竟是茶啊。”
沈觀月面如菜色,咬碎了忌恨往心裡吞,訕笑道:“二妹妹誤會了。”
“誤會什麼?”
沈觀衣彷彿沒有瞧見她們三人的尷尬,自顧自的坐下,吩咐道:“不若打些酒來,你們好生給我講講,方才說的,一雪前恥的計劃?”
唐氏/沈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