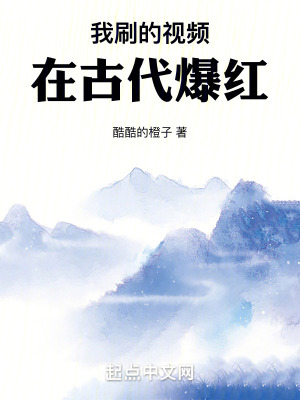懸姝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沈府今日熱鬧的出奇。
平日安心待在自己那一畝三分地中的妾氏與家中晚輩紛紛露了臉,站在正堂等著送二小姐出嫁。
沈書戎這些年納了不少妾氏,如今滿堂姝色,唐氏瞧了心中頗為憋悶,但面上仍舊禮數周到,拉著庶出子女們嘮家常。
她年輕時傷了身子,至今也未能給沈府誕下嫡子,但她心許雲姨娘誕下的年哥兒,年紀尚輕,卻是個聰明的,與她也很是親近。
若不是沈觀衣突然發難,斷了她的謀劃,今日她不但能讓沈觀衣下不來臺,還能將髒水潑在雲姨娘身上,之後也能以管教不嚴的名義,將年哥兒抱養過來。
想她為了促成這件事,低聲下氣的拉攏雲姨娘許久,結果如今通通因為沈觀衣化成了一縷炊煙。
雲姨娘年紀尚輕,性子溫婉,見唐氏面色不愉,以為她是在擔憂今日之事,安撫道:“夫人,二小姐定會平安順遂的嫁過去,您別擔心。”
“是啊夫人,二小姐那般得老天眷顧的女子,定會安順的。”
“今兒個我可要好好沾沾二小姐的喜氣,讓我家蓉姐兒將來也能嫁個好夫家。”
先前還各不搭理的一屋子人,如今因為沈觀衣而侃侃而談,你來我往,言語之間多是討好諂媚,唐氏勉強的勾了下唇,乾脆眼不見為淨,低下頭一個勁的喝茶。
“夫人,到了,姑爺到了!”
話音剛落,便瞧見沈書戎揹著一小姑娘緩緩走來,五步一喜字,十步一紅綢,小姑娘戴著喜帕,瞧不清臉蛋兒,於是她懷中抱著的那把琴,便格外引人注目。
年紀尚輕的女兒家拉著自家姨娘的衣袖,好奇的睜大眼睛,“姨娘,二姐姐為什麼要抱一把琴啊?”
雲姨娘算是陪著沈書戎一步步走到如今的老人,她不喜爭搶,除了自家孩子,對許多事也算不得上心,但那把琴,她不會忘。
柳商這個名字,如今想起,都仍舊令人惋惜。
那般驚才豔豔的女子,最終卻落得那麼一個下場。
而罪魁禍首……
雲姨娘抿著唇側頭看去,只一眼便低下了頭,這府中的人,誰也不想步柳商的後塵。
唐氏氣的嘴唇發顫,臉色蒼白。
沈觀衣由沈書戎揹著從正堂走過,不曾停留半分,新嫁娘拜別主母是燕國一直以來的禮儀規矩,而今日,沈觀衣不但壞了規矩,還抱著那把本該消失的破琴,堂而皇之的出嫁!
怨毒的目光似要化為釘子從沈觀衣的脊樑狠狠穿過。
沈觀衣察覺到了,甚至心情甚好的揚起了嘴角。
心情怎能不好呢?前世的今日,唐氏可高興的快要合不攏嘴,以為事事都在她的掌控之中,想要壓得她這輩子都翻不過身來。
如今再回想,竟能理解唐氏當時的心緒。
瞧著憎恨之人被玩弄於股掌之中,還得打落牙齒混血咽,那等心情,當真美妙。
門口吹打得聲音由遠及近,緩緩消散,沈書戎將她送入轎中,氈簾放下的一瞬,她聽見了諸多聲音。
與前世的嫌棄謾罵不同,她們或是討好或是真心,那些從前恨不得用唾沫星子將她釘死在不貞不潔上的姨娘與下人們,竟也能說出這般讓人高興的吉祥話。
“吉時已到,起轎——”
到底那三十多年沒有白活,她至少從李鶴珣身上學會了如何讓那些人閉嘴,如何讓自個兒高興。
-
迎親隊伍,十里紅妝,繞了大半個京城,終於在戌時前去到了李家。
轎子穩穩停下,耳畔喜婆正高聲喊著話兒,氈簾掀開的一瞬,一雙修長乾淨的手將她從轎中扶了下來。
涼風習習,喧鬧不休,他們離的那般近。淺淡的松香似乎隔著喜帕撓了一下她的鼻尖,又癢又麻。
沈觀衣不是第一次嫁人了,但她垂目瞧見那一雙乾淨到不沾塵土的長靴時,仍舊有一瞬間的恍然。
她又成了李鶴珣的夫人。
如命運的刀雕刻成了眼前斑駁的人影,混著光,透過喜帕投向心湖,浮出漣漪,激盪的連耳唇也突然滾燙。
沈觀衣知道,這些與風月無關。
與他有關。
成親的繁文縟節其多,底下賓客瞧著熱鬧,年紀尚輕的人都伸長脖子想要看的清楚些,沒人注意到與新人同樣著緋衣的男子端坐在角落,一雙眸子緊緊的盯著那二人。
“世子。”阿讓輕輕喚了一聲,怕他因衝動做出些什麼事來。
寧長慍望著那並肩而立的人,周遭的紅連帶著他自己的衣裳,都覺著礙眼,礙眼至極!
那是他從前不曾想過的場景,就像他不曾想過,小姑娘有一日會長大,會嫁作他人,再與他無關。
半個時辰前他還想著,一個女子罷了,有何不捨,他偏要來看著她成親,可當真看見了才知曉他自詡的灑脫也不過如此。
他從來沒放下過,怎麼敢來看她成婚的。
“阿讓,我是不是做錯了?”他出神的問著。
“三個月前我若不離京,是不是便不會有今日?”
“或者我對她耐心些,不回那樣讓她生氣的信,她是不是會等到我回來?”
“又或是我回京便去找她,不那般固執的非要等她一個女子來哄我。”
“這樣……她是不是就會和從前一樣。”
阿讓喉中哽咽,不忍再看寧長慍這副空洞的模樣,“世子,你該為姑娘高興的。”
為她高興?
那他呢,誰又讓他高興了?
那是他養大的姑娘,她的一顰一笑,她的一切難道不該是他的嗎?
如今卻被另一人牽著拜堂,而他只能眼睜睜看著!
寧長慍猛地起身,眼尾紅的出奇,酸澀嫉妒如狂風翻湧而出,他滿心滿眼都是要將那礙眼的兩人分開!
“世子!”阿讓大驚失色,連忙拉住寧長慍。
他狠厲的回頭,眸中的不顧一切令人生駭,“連你也要攔我?”
阿讓抿著唇,緩緩放開了手。
寧長慍大步流星的朝著那二人走去,心間顫意不止,他越走越快,越走越快,似乎下一瞬便能將他看著長大的姑娘搶回來。
直到——
小姑娘從喜袍袖籠中伸出手勾住了身旁男子的尾指,輕輕一扯。
那樣親密無間的小動作,若不是信任與依賴,以沈觀衣的性子定是做不出來的。
那些潮汐在瞬間褪去,化為岌岌而終的風刺進骨血,冷的他肌膚生疼。
在疼痛蔓延之時,他緩慢的,緩慢的垂下了雙眸。
沈觀衣似有所感的想要回頭,耳畔卻突然傳來一道告誡的聲音,“放開。”
她回過神,頓時不滿道:“李鶴珣,我腳疼。”
李鶴珣面上從容,身子微微傾斜,遮擋著二人袖袍下勾纏的手指,旁人壓根看不出異樣。
但聽沈觀衣拜堂之時喊腳疼,饒是他心性再好,此時也忍不住黑了臉,冷冷的丟出兩個字,“忍著。”
沈觀衣是真的疼,出門時還不覺著,如今才發覺鞋中似乎多了個圓疙瘩,她站了這般久,早已疼的咬牙。
聽見李鶴珣如同斥責的聲音,沈觀衣氣性上來,壓根不管現下是何等場合,便要掀開喜帕將自己受苦的腳救出來。
就在她鬆開手,抬手揪住喜帕的同時,李鶴珣手疾眼快的按住了她,面色一緊,“你要做什麼?”
她嗔怒道:“我說了,我腳疼。”
她是真的能為了讓自己舒服而不將眾人放在眼裡!
李鶴珣倒吸一口涼氣,額頭青筋直跳,怒火中燒,可向來知曉分寸的人不會在此時為了發洩情緒而不管不顧。
他忍著火氣,只能放柔了聲音哄道:“再有半刻鐘,待祝詞說完,我便讓人扶你回房,聽話一次可以嗎?”
方才那般大的動作,離得近些的人應當早已察覺異常,李鶴珣餘光瞧著母親竟然沉了臉色,抿唇思慮片刻,他微微低頭,幾乎俯在沈觀衣耳畔。
“可以嗎?”
沈觀衣動了動腳趾,額角的汗珠從腮邊劃過,她咬著唇嗯了一聲。
聲音雖小,李鶴珣卻聽見了,他頓時小小的舒了口氣,面不改色的對上爹孃打探的神色。
待祝詞結束後,沈觀衣被探春攙扶著離開,而李鶴珣則要留下招待賓客,直至夜深。
他不願在外多留,心中念著沈觀衣喊疼的腳,也不知是真是假。
饒是李鶴珣心中再不耐,眼下也依舊遊刃有餘的輾轉賓客之間,從容應對,點到即止。
酒過三巡,他行至寧長慍身前,將白日託歸言轉告之話再次說了一遍,寧長慍笑道:“李大人與令夫人真是伉儷情深,為此你可謝了我兩遍了。”
李鶴珣從前與寧長慍不常打交道,或者說上京的權貴子弟,他幾乎都稱不上熟識,只是偶有聽聞寧長慍此人喜好風月,流連花叢,對男女之事懂得甚多。
他輕笑道:“今日多得世子相助才能不誤吉時,口頭上的謝再多世子也當得。”
都說李鶴珣此人如鶴如風,向來從容自持,寧長慍瞧著他眼尾的淺笑,只覺得甚是礙眼,他飲下杯中清酒,赫然提醒道:“我把李大人當朋友,今日之事李大人不必放在心上,不過……”
他眸中掛著一絲輕佻的笑意,“你也知曉我喜好風月,所以不得不提醒李大人一句。”
在李鶴珣不解的神情中,寧長慍微微側頭,掩去眼底的嘲弄,小聲附在他耳邊說了一句什麼。
只一瞬,李鶴珣黝黑的瞳仁驟然緊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