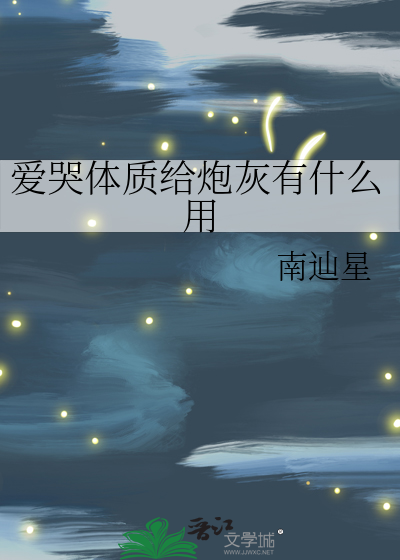關心則亂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等遊觀月終於騰出空來換下血淋淋的衣裳扒口飯時,蒼莽的瀚海山脈再度被籠罩在深藍色的夜空中了。頂著漫天星子,疲憊不堪的遊觀月懷著身為新君心腹的熾熱念頭,不顧此時已是半夜,直奔慕清晏處覆命,誰知恰好看見他那敬愛的新主君被蔡昭奮力推出房門。
蓬著滿頭亂髮的美貌小姑娘兩眼血絲情緒惡劣,從門縫中留下一句‘我困死了要睡覺是人是鬼都不許來吵我否則吃我一刀’後,就砰的一聲關上房門,差點撞到慕清晏的鼻子。
遊觀月見狀,扭頭就想溜。
慕清晏倒是毫不在意的叫住了他,遊觀月見勢趕緊稟報起來,“各處關隘與極樂宮內的聶氏黨羽已盡皆俯首就擒,尚有零星餘黨因為回援聶喆不及,尚且散落在外。卑職以為他們成不了什麼氣候,可待日後徐徐擒殺之。”
“自從青羅江之戰後,他們就大勢已去。剩下的貨色不過是一群靠著聶恆城腐屍過活的蛆蟲罷了,以後慢慢收拾好了。”慕清晏反問另一件事,“東西帶來了麼?”
遊觀月立刻奉上一方小小的黃楊木匣子,匣子外似乎凝了一層薄薄的白霜。
慕清晏接過匣子,“宋公子的情形怎麼樣了?”
“入夜前便醒了,用過藥後又睡下了了。”遊觀月已從上官浩男處得知了宋鬱之的身份。
慕清晏點頭:“如此,咱們就去瞧瞧宋公子罷。”
遊觀月蠕動了下嘴唇,他本想說宋鬱之到底是傷者,半夜三更的吵醒人家不大好吧。
但他最終沒說出口。
誰知剛到西側殿,就看見宋鬱之房間燈火通明,似乎正在等人。
慕清晏笑著跨進屋內:“重傷之下,宋兄依然這般好風采,真是可喜可賀。”
遊觀月瞥了眼靠坐在軟塌上的宋鬱之,只見他臉色蒼白,鳳頰凹陷,掩飾不住重傷初愈的虛弱之態,只一雙黑黢黢的眸子深沉有力。
“我猜著時辰,少君也該來了。”他輕聲道。
慕清晏坐到他對面,“宋兄傷勢如何了?”
“俱是皮肉筋骨的外傷,並未傷及丹田本元,再歇息半日就能走動了。”宋鬱之很清楚對方的意思,索性自己先說了,“師妹呢?她沒事罷。”
慕清晏含笑:“昭昭好的很,適才我本想找她一道來見宋兄,不想卻被她一頓痛罵,趕了出來,只說是還沒睡夠。”
宋鬱之忍不住打量起眼前這位笑意蘊藉的俊美青年來。
他與慕清晏相識猶在蔡昭之前,多少知道些對方的臭脾氣——慕清晏是那種自己不痛快就見不得別人痛快自己痛快了還是不願別人痛快的極品,並全然不會掩飾自己的尖酸刻薄。
往日自己只要多提蔡昭一嘴,他就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此刻居然態度平和的判若兩人,彷彿蒙山了一層溫潤燻然的笑假面,叫人看不出深淺來。
慕清晏道,“宋兄於危難之際救下了我教教眾,這份情我記下了,以後必有所償。”上官浩男是他的屬下,這筆恩情自然得主君扛下。
“行俠仗義本就是我輩應盡之責,少君不必介懷。”宋鬱之擺手,“不知那紫玉金葵……”
“我正要說這事。”慕清晏道,“之前我已命人開啟寶庫,細細搜尋了一番,然而……”
他頓了頓,“然而遍尋不得紫玉金葵。”
宋鬱之一驚:“遍尋不得?紫玉金葵不在貴教之中?”他對紫玉金葵下落的推斷其實也不過憑著全憑猜測,真要說憑據,卻是沒有的。
“難道蔡女俠沒有奉還紫玉金葵?”現在唯一能確定的,反而是紫玉金葵最後的經手人是蔡平殊。
“如今教中人事混亂,其中細處尚不得知。”慕清晏搖頭。
在宋鬱之滿臉的失望中,他將那隻凝有白霜的木匣推到桌上,“此物還請宋兄收下。”
宋鬱之接過木匣,開啟一看,發現匣中躺著一枚掌心大小的玉石,通體雪白,寒氣逼人,透著厚厚的木匣猶自滲出霜寒之氣。
“西域大雪山下的萬載冰玉?”他生長於天下第一等的世家名門中,自然是識貨人。
慕清晏微笑道:“此物雖不如紫玉金葵堅實厚密,但緩和灼熱內勁的功效,猶有過之。只盼宋兄不嫌棄,收下此物。”
他又道,“聶喆之亂尚且釐清,紫玉金葵興許落在別處也未可知。紫玉金葵說是寶物,其實在一等高手眼中也不過是雞肋之物。若非治療幽冥寒氣之傷,我也想不到其他用處了。倘若日後尋得了,我即刻給宋兄送去。”
宋鬱之緩緩合攏冰玉匣子,點頭同意,然而心中卻想,就算你說的是假的,我難道還有別的選擇麼。
他本非疑心之人,因他逐漸長大懂事之時,聶恆城及其死忠心腹早已煙消雲散,正邪兩派進入井水不犯河水的平靜相持階段,是以並未真正見識過魔教行徑。
然而這回進入瀚海山脈,著實叫他大開眼界——將受魔教管制庇護的平常百姓活活製成屍傀奴;沾之即腐的蝕骨天雨;一言不合便炸碎地下石室,哪怕其中還有己方親友;更別說還有之前武元英所遭受的非人慘事。
此番種種下來,他終於相信長輩所言,魔教果然是一群殘忍邪惡之徒。
“以宋兄的身份,在本教多留無益。”慕清晏起身,“宋兄再睡一覺罷,待明日天明,我便派人送宋兄出去。”
宋鬱之拱手相送,心想我哪裡還睡得著。
……
夜風徐然,慕清晏大步在前,衣袂飄揚,徑直走向東側殿中胡鳳歌養傷之處。
為免主君等待,遊觀月本想找個婢女去將胡鳳歌叫醒,不曾想胡鳳歌屋內也是燈火明亮,並且屋內早已有客在訪,此情此景倘叫蔡昭見了,必要吐槽‘你們魔教都是半夜不睡覺的麼’。
於惠因原本坐在榻前,與胡鳳歌輕聲細語的說著話,一見了慕清晏與遊觀月,三十多歲的中年文士緊張的像個籬笆下與心上人偷著親嘴的少年,紅著臉溜走了。
慕清晏望著於惠因的背影微笑:“本君莫不是打攪了胡長老的好事?”
胡鳳歌利索的下榻行禮,聞言爽朗一笑:“少君說笑了,惠因從小就是靦腆性子,不過心地不錯,常偷著給我送吃喝和傷藥。唉,他自小被陳曙和聶喆欺負,做小伏低慣了。”
慕清晏看了遊觀月一眼,遊觀月領會,躬身而去。
然後慕清晏示意胡鳳歌躺靠下說話,胡鳳歌則道:“打小從天罡地煞營爬出來的,這點傷算什麼。若是身子骨不夠硬挺,早死在那座養蠱場中了。”
慕清晏坐下,拱手道:“此番能反敗為勝,還要多謝胡長老那要緊的反戈一擊。”
胡鳳歌不敢託大,趕緊單腿跪下:“卑職不敢擔。”離教教規森嚴,既然認了慕清晏為主,就必須銘記上下尊卑之分。
她微微抬頭:“少君,聶恆城死時惠因年紀還小,未參與過任何聶黨行事;聶恆城死後,他因屢次規勸,惹惱了聶喆,便隱居山間。您看是不是……”
慕清晏一擺手:“只要於惠因不想著復興什麼聶氏榮光,本君不會為難他的。”
胡鳳歌試探道:“那思恩小公子……”
其實她對李如心母子並無好感,自己在天罡地煞營掙命時,常能看見這位千嬌萬寵的大小姐高傲的走過,眼皮子都沒往底下那群沾滿泥巴血漬的死士抬一下。不過於惠因念著聶恆城的恩情,倘若慕清晏執意要處死李如心母子,事情就麻煩了。
慕清晏似乎看透了她的心事,微微一笑:“聶恆城能容下家父與我,難道我還容不下聶氏區區一名幼子麼。”
胡鳳歌大喜:“少君英明!”起身後,她補充道,“其實思恩小公子先天不足,身體孱弱,不但練不了上乘功夫,我看壽數也長不了。”
慕清晏無所謂的揮揮手,“隨他去吧。”
胡鳳歌望著他的面容,怔怔出神:“少君,您與令尊生的真像,但是……”
“但是神氣大不相同,是麼。”慕清晏淡淡道,“我不是父親。”
胡鳳歌嘆口氣,“入夜前屬下聽說遊觀月將少君之母孫夫人帶上山來。少君,恕屬下僭越,孫夫人的確有種種不是,但,但……”
她殺人放火酷刑折磨是把好手,言辭卻不如何利索,最後只好道,“一樣帶兩個翅膀的,既有不懼風雨的蒼鷹,也有棲身屋簷下的家雀。孫若水,她,她只是個全無自保能耐的尋常女子,請少君將她置於一旁,不去理她便是了。”
話雖說的委婉,但明裡暗裡皆是怕慕清晏傷害孫若水,是以隱晦求情。
慕清晏長眉一挑,頗是好奇,“胡長老居然為孫夫人說話。”
旁人就罷了,胡鳳歌可是從天罡地煞營中一路殺出來的,兩手血腥,殺人如麻,手下無辜的有辜的亡魂不知有多少——此刻居然一臉憐惜的替孫若說分說。
胡鳳歌悵然的嘆息一聲:“少君不知道吧,其實我與你娘是一同被帶進離教的。”
慕清晏察覺這話中的異常,“一同?胡長老與孫夫子是同村之人?”
胡鳳歌的回答很微妙:“我與孫若水是同村來的,但與孫夫子卻不是同村之人。”
“孫夫人不是孫夫子之女?!”慕清晏立時明瞭。
胡鳳歌苦笑:“天災襲來,全村都遭了殃,哪裡就會逃出一個弱女子呢。是聶恆城想要拿捏你爹,但真的孫小姐已然亡故,只好在手底下養的女孩中挑一個最最美貌溫柔的出來。反正也沒人見過長大後的孫小姐,只消讓若水牢記孫夫子生平與文章即可。”反正慕正明也不是疑心病重的人。
慕清晏整個人宛如冰凍住了一般,眼神寒意森森。片刻後,他才恢復融融笑意,“如此說來,父親是從頭受騙到尾的了。”
胡鳳歌看他這樣,眼前出現了那個真正溫和寬厚的貴公子,不由得又是一聲長嘆,“若水也是難的很,倘若她是真正的孫小姐,只要豁出去傾吐苦衷,令尊看在孫夫子的情分上也會護著她不受聶恆城加害——可她偏偏不是。她能怎麼辦,只能聽聶恆城的了。”
有件事她按下沒說,正是在那段難熬的日子中,聶喆的軟語溫存安慰了孫若水。
慕清晏笑起來,“聶恆城手下不留無用之人,能進天罡地煞營的人,要麼根骨好,要麼長相好。路成南做事講究個腔調,每每等新入營的孩子定下神來,就會讓他們自己選,是做死士還是為間。胡長老選了前者,孫夫人選了後者吧。”
在用人前,他早就將胡鳳歌的過往查的清清楚楚。結論是,哪怕胡鳳歌不為自己所用,她也是個值得敬重的人。這份敬重,不分男女。
胡鳳歌一怔——當年抉擇時的種種,竟如前世一般,自己都快忘了。
為了讓自己全然死心,她甚至用碎瓷片割爛自己的臉,就是為了徹底斷了自己的後路。從此之後,斷不能憑臉蛋取利了,只能靠辛苦練本事。
她不自覺的撫上自己滿是疤痕的臉頰,很是感慨。自己也曾是個美貌可愛的小姑娘,只不過她不願將自己的安危榮辱寄在別人的憐憫愛慕或色迷心竅上,她想要自己握住兵刃,哪怕哪天死無葬身之地,也勝於等人垂憐。
二十多年前的抉擇,如今看似分出了高低,她還是高高在上的七星長老,孫若水卻免不了後半生幽居一隅了。
可胡鳳歌知道,哪怕自己此刻還是顛沛流離刀口舔血,孫若水依舊過著養尊處優風花雪月的日子,自己也不會後悔。
話說到這裡,胡鳳歌知道自己也不用勸了,大不了將來孫若水幽居之時多去看望她,也算全了幼時同村小姐妹的情義。
這時遊觀月進來,“少君,嚴長老醒了。”
慕清晏點頭,與胡鳳歌道別後,轉身去了東側殿最後的一間屋子。
屋裡瀰漫著濃重的藥酒氣息,嚴栩猶如一尊扭曲的地藏老菩薩般盤腿坐在榻上,見到慕清晏後恭恭敬敬在床上行了個禮,“嚴栩見過少君,待來日行過繼位大典,老朽便記少君為本教第十二任教主。”
老頭抬臉一笑,“老朽就是因為不肯記載聶喆為教主,還想著請你父親出山,重掌神教,這才惹了聶喆的恨,設下陷阱擒住老朽。”
“你找我來就是要說這個?”慕清晏雙手負背站在榻前,“當年你記載聶恆城為第十一任教主也是本教唯一一位異姓教主時,也是這般歡天喜地?”
嚴栩提高嗓門道:“老夫知道少君心裡對當年之事不痛快,但老夫還是要說,聶恆城當年繼位教主,那是理所當然的!”
“你曾祖父因為婆娘死了就灰心喪氣顧影自憐時,十幾歲的聶恆城立意革新教務。”
“你祖父與他那攪家精的婆娘要死要活時,聶恆城為了神教殫精竭慮宵衣旰食。”
“你老子只顧著自己躲清淨時,聶恆城拉開架勢要與北宸六派一爭高低!”
“少君以為神教是什麼,是屋裡收藏的一件東西麼,想捧著就捧著,就撂下就撂下?!還是你們慕家後院的一畝三分田,想耕種就耕種,想荒廢就荒廢?我呸!良言難勸要死的鬼!後來你家三代受制於聶恆城,能怪誰,自己作孽自己受著!”
“我生於神教長於神教,對神教的忠心日月可鑑!當初你家父祖但凡有一個肯聽勸的,我怎會贊成聶恆城繼位教主!”
站在窗邊的頎長身形一動不動,彷彿凝成了一座冰雕。
嚴栩見慕清晏這般情形,心知這番重錘是敲響了,頓時心中大喜。他決意趁熱打鐵,臉上裝的老成肅穆,“少君啊,既然你都聽進去了,趕緊與那臉上笑嘻嘻的小姑娘斷了!大丈夫何患無妻,少君的親事就包在老夫身上,包管替少君找一位……”
“她姓蔡。”慕清晏終於開口了,“她叫蔡昭,父親是落英谷谷主蔡平春,母親寧氏夫人,舅父乃長春寺覺性禪師。她還有個過世的姑母,叫蔡平殊。”
離教教規所定,一旦兼任了秉筆使者,就不能多插手教務,教中恩怨也必須儘量置身事外,務求心靜如水不偏不倚的記錄教史。所以蔡平春寧小楓覺性禪師什麼的,嚴栩還有些稀裡糊塗,但是蔡平殊三個字在離教中簡直如雷貫耳!
嚴栩當即從床上一跳三尺高:“蔡平殊!就是那個蔡平殊!你你你,你怎麼可以……”人氣到極點,反而不知道該罵什麼。
慕清晏的曾祖母不過是身體孱弱了些,慕清晏的祖母不過是脾氣執拗了些,慕清晏的母親不過是聶恆城派去的細作罷了——雖說都不是靠譜的女人,但到底還是同教中人啊。
哪裡知道慕清晏居然青出於藍勝於藍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直接弄來個北宸六派的小妖女!蒼天啊大地啊,這是哪路神仙要滅我離教啊!
嚴栩癱軟在床上,腦袋嗡嗡的。
慕清晏還在一旁氣定神閒的吩咐:“待會兒我要辦件事,既然嚴長老中氣十足,不若一道來看看吧。觀月,命人去抬副步輦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