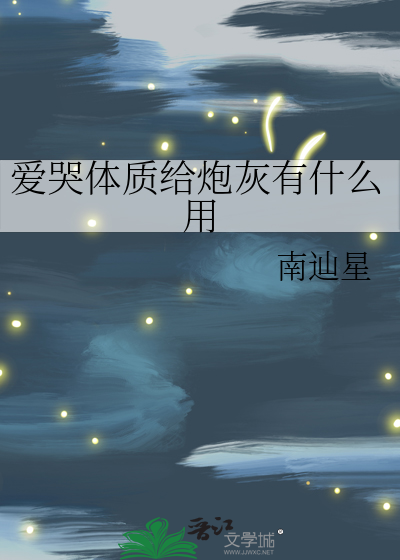關心則亂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眾人抱拳稱是。
嚴栩雖受了斥責,但心中快活要跳舞,尤其應的大聲。
“今日我有兩件事。第一,寶庫中的紫玉金葵哪兒去了?”慕清晏轉回頭。
遊觀月連忙道:“這兩日屬下仔細搜尋了各處藏庫,的確沒有此物。”
“你們有誰見過此物。”慕清晏再問。
其餘人都搖頭,只有胡鳳歌上前道:“屬下年幼時曾見聶恆城把玩過這件寶物,後來據說失竊了。”
嚴栩若有所思:“教主要尋這件東西麼?這個老夫倒有些知道——當年它的確失竊了,據說是北宸六派下的手,不過後來又被還了回來,也不知那偷兒搞什麼鬼。聶恆城為此一氣殺了十幾名看守寶庫的頭領。誰知不久後,它又被盜了。”
“啊。誰這麼囂張了,偷一次不夠,還敢偷第二次?”上官浩男道。
嚴栩拈著稀疏的鬍鬚:“第一次誰偷的老夫不知,但第二次是盜寶的卻是路成南。”
此言一出,眾人皆驚。
“這是為何。”胡鳳歌尤其吃驚,“路四哥對聶恆城可是忠心耿耿啊。”
“這個老夫也不知道。”嚴栩搖頭,“只知道聶恆城發現後勃然大怒,重重擊傷了路成南。老夫當時也在場,依老夫看來,聶恆城那一擊是下了死手的。”
“竟有此事?真是奇怪了。”胡鳳歌大奇,“聶恆城這人在外頭狠辣無情,但對自家子弟卻十分疼愛。陳曙那等不成器的他尚且百般維護,何況路四哥是他四大弟子中最受器重的一個。我在天罡地煞營中常聽頭領們說,將來承襲聶恆城衣缽的,必是路成南。”
慕清晏問:“那後來呢。路成南去哪兒了?”
“那天夜裡聶恆城有點怪,神情激動狂亂,若不是知道不可能,我還當他練功走火入魔了呢。”嚴栩道,“韓一粟也瞧出了他師父不對勁,一面拼死攔著聶恆城,一面叫路成南快跑——於是路成南就跑了。此後再未出現,也不知去哪兒了。”
慕清晏點點頭,“這麼說來,紫玉金葵是與路成南一道不見的。”他心中有許多疑問,便習慣性的在案几上點著手指。
“這件事先撂開一邊,說第二件。”他轉言道,“數月前,武安常家堡被滿門屠滅,這件事誰做的?”
遊觀月與上官浩男面面相覷,嚴栩與於惠因一臉茫然。
胡鳳歌思忖片刻,上前道:“這件事我隱隱聽到些傳聞,應當是聶喆所為。”
“好端端的,五哥去滅常家滿門做什麼?”於惠因奇道。
“我也不知道。”胡鳳歌神情凝重,“聶喆嫉賢妒能,手底一直留不住能人。他輕視我是女流之輩,許多事倒願意與我商議。但我知道,他在暗處一直另有幫手。不說遠的,只說這幾個月,無論是屠滅常家堡還是沿途偷襲北宸六派,我都是事後才知道的。”
“事後我問過參與常家堡行動的弟兄,他們也好生奇怪。要知道常家堡藏的極其隱秘,便是當年路四哥也破解不了常家堡的藏身陣法,誰知卻被聶喆輕易找到了——弟兄們說,行動那夜,有人在沿途預先做了記號,他們才能順順當當摸上常家堡。”
這番道來,慕清晏倒有些始料未及。
他原先一直以為是聶喆滅了常家堡,到時將聶喆及其手下全宰了,就算給常家報仇了。現在聽胡鳳歌說來,竟是另有元兇。
“看來,這事得問聶喆了。”慕清晏利落的決定,“幾日前聶喆傷勢加重,如今無法動彈,我們走過去看看。”
眾人同時起身,隨慕清晏一路行去,拐到偏殿一處盈滿苦澀湯藥氣息的屋舍內。
門口守衛肅色抱拳,為慕清晏推開房門。
一行人魚貫進入病舍,但誰也沒想到,躺在病床的聶喆已經成了個死人——傷口血漬凝固,臉色鐵青,面目扭曲,身體冰冷,死去至少數個時辰了。
“啊!五哥,五哥!”於惠因撲上去叫道,“這是怎麼回事!這是怎麼回事!”
門口數名守衛嚇的面無人色,連忙跪下請罪,並表示這一日來,除了送飯換藥的小廝,再無人進入這間病舍。
“他是被內力震碎了心脈。”慕清晏探了探聶喆的心口,“應當是有人假扮送飯換藥的人,進來取了他性命。”他根本沒想讓聶喆活著,是以門外守衛更多是防備有人來營救,便疏忽了有人來滅口。
嚴栩驚呼:“不知是哪路高手殺了聶喆?”
上官浩男上前看了看聶喆的屍首,搖頭道:“未必得是高手。聶喆受傷已重,幾乎毫無抵抗之力,尋常修為之人皆可取他性命。”
“今日送飯換藥的幾名小廝中,有一人至今未歸。”遊觀月問完手下,返還病舍,“想來凶多吉少了。”
於惠因從病床邊起來,含淚道:“教主,屬下有一言早就想說了。之前教主指出令尊被毒殺一事……是不是孫夫人動的手屬下不知,可屬下以為此事並非五哥指使。”
“五哥曾不止一次說過,令尊性情淡泊,無心權勢,而五哥權位不穩,正需要令尊這樣的幌子。每回有教眾質疑五哥得位不正,五哥就反駁‘慕氏的正經後人都沒說話,有你們什麼事’,以此推諉過去。五哥盼令尊安健康泰還來不及,怎會指使孫夫人去毒殺他呢!”
“糟了!”胡鳳歌神色一凜,“若水!”
她反身一躍,飛快出了門,其餘人趕緊隨上。
然而還是晚了,孫若水也死在了病床上——一樣的面色鐵青,五官扭曲,身體冰冷。
上官浩男失聲道:“又是被震碎心脈的。”
慕清晏不疾不徐的走來——他是最後一個進屋的。
他道:“大家不必著急。既然有人要滅口,自不會只殺聶喆一個。聶喆屍身冷去已久,孫夫人自然也早就被殺了。”
嚴栩毫無頭緒,“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啊?哎呀,孫夫人沒了教主您別難過啊。”
看著孫若水的屍首,慕清晏內心毫無波動。
很早之前,他就對生母死了心。
軟弱,思慕,渴求,這些尋常孩童對母親該有的情感,慕清晏早就埋葬在了那間腐朽破敗的小黑屋中了。那種被至親無情傷害後還趴上去舔的卑賤情緒,他是一分一毫也沒有的。
成長過程中,他越瞭解孫若水的過往和品行,對這個生育過自己的女子便只剩下‘鄙夷’二字。知道她毒殺了父親後,更添了‘憎惡’二字。
唯一可恨的是,當初為了不讓父親傷心,他並未嚴正表明自己對視孫若水若敝履的態度,反叫父親誤會自己對生母還有幾分在意,進而給了孫若水加害的機會。
便是沒人來滅口,他本也不打算讓毒害過父親的人活下去,孫若水也不例外。
只不過聶孫二人這麼一死,便掐斷了所有線索,重重迷霧之上更籠了一層輕紗。
首先,若紫玉金葵只是用來凝神靜氣的雞肋之物,聶恆城為什麼那麼著急它。
其次,路成南作為聶恆城最受器重的忠心弟子,又為何要盜走紫玉金葵。
再次,暗中幫助聶喆的人是誰?嗯,十有八九是北宸六派的。然而是誰呢?
最後,孫若水為什麼要毒殺慕正明?兩人既已合離,慕正明完全不會礙著她的路,她還有什麼理由下此毒手呢。
慕清晏站到窗邊,藉著明亮的日光,不動神色的視線掠過屋內每個人的面龐——
苦思冥想的遊觀月,抓耳撓腮的上官浩男,嚴栩喋喋不休著‘為什麼為什麼’,胡鳳歌略帶哀傷的闔上孫若水的雙眼,於惠因安慰的輕拍她的肩背,加上如今不在場的那個牆頭草呂逢春……除掉聶孫二人滅口的人,會在這些人中麼?
或者,另有其人。
慕清晏長眉緊蹙,神思幽深。
他轉頭隨口道,“昭昭,你覺得會不會是……”
聲音戛然而止。
一室寂靜,眾人神色各異。
慕清晏一動不動,看著空空如也的身側。
“別怕,也別擔憂,總有法子的。”
有人曾經這樣對他承諾過,有人曾經溫柔的親吻在他臉上。
父親過世後,在他篤定清冷孤寂的人生中,曾照進過一束明媚溫暖的陽光。
她有一雙極漂亮的眼睛,她曾笑言親友長輩常說她會長,將蔡平殊臉上最好的地方像了去,尤其是笑起來時,明亮的大眼中像微起漣漪的春日湖水,純淨又溫暖。
——別怕,也別擔憂,總有法子的。
既然做了承諾,為何不守諾呢。
卻留他一人獨自在這片焰火熾烈的深淵中。
【本卷終】
第90章
終於逮回了兩隻小兔崽子,北宸眾人日夜兼程趕回九蠡山。
戚雲柯急著掌門規,蔡平春急著行家法,宋時俊急著給兒子恢復功力。稍許拉扯,嗓門最大的宋時俊勝出。
藥廬之中,宋鬱之雙手合著那枚冰玉,靜靜盤腿調息。戚雲柯,蔡平春,宋時俊,分別伸掌虛貼在他頭頂百會,胸口膻中,後背風門三大穴位上,勻勻的運起氣來。
北宸三大掌門同時發力,自然非同小可,這股雄渾洶湧的內力猶如波濤翻滾的巨浪在宋鬱之體內奔走,這股氣勁倘若直衝丹田,固然能驅散氤氳其中的幽冥寒氣,然而宋鬱之的丹田與全身經絡不免同時受害。
宋鬱之按著雷秀明的囑咐,小心的將三位長輩的內力引向自己右掌,透過冰玉湧向左掌,再經由天溪與期門兩穴流向丹田,如此一來,三股內力原生的燥熱交困被消磨殆盡,湧入丹田的內勁渾然一體,圓熟溫潤。
宋鬱之額頭隱隱冒汗,左右兩掌稍稍分開數寸,懸空兩掌之間的那枚萬載冰玉,在強勁內力逼迫下發出微微嗡鳴。
條案上的香菸逐漸燃盡,忽聽一聲短促清晰的玉石爆裂之聲,站在宋鬱之身前一側的蔡平春最先察覺,輕喝一聲‘收功’——三位掌門同時收起內勁,回掌調息。
與此同時,數聲清脆的玉石墜地之聲響起,只見那枚號稱‘至堅至剛’的萬載冰玉已然碎裂成幾片,跌落在地。
宋鬱之大汗淋漓,衣衫溼透,全身不住顫抖。
戚雲柯沉聲道:“鬱之不可歇怠,趕緊運功調息,以‘洗髓經’上三篇中的功法運氣自愈,調養經絡丹田。”
其實此刻的宋鬱之周身虛乏,幾近脫力。但他自幼性情堅韌,聞聽此言,立刻咬牙運功。
宋時俊端詳地上碎裂的冰玉,“看來那魔教賊子還算實誠,這塊冰玉的確天下罕有。”
戚雲柯見宋鬱之臉色雖然蒼白,但眉心那股氤氳不散數月的青灰之氣已然消退,便放下心來。趁著宋時俊守著藥廬不肯離開的檔口,他趕緊拉上蔡平春,審訊不肖弟子蔡昭去也。
蔡昭早吃了寧小楓一頓排頭,此刻當著父親與師父的面,一五一十的將此次魔教之行全都說了,除去兩人之間的私密細節與雪嶺上的秘密,幾乎是和盤托出。
蔡昭生平難得一氣說這麼多實話。
“這麼說來,你取得雪鱗龍獸的涎液,都是靠了那小子的幫忙?”
“差不多吧。”
“你追去魔教,是為了回報他的相救之恩?”
“是,但並沒幫上什麼忙。”
“他待你好麼?”
“……很好。”
“不知此子有沒有別的圖謀?”
“有或沒有都與我無關,反正我以後不會與他私自相見了。”
蔡平春與寧小楓對視一眼,皆察覺到女兒語氣中的苦澀哀婉之意,盤旋在舌尖的責罵便放不出去了。反倒是之前最著急的戚雲柯聽完蔡昭的話後靜坐一旁,望著地上不知何處微微出神,寧小楓叫他數聲才回過神來。
“小昭兒過來。”戚雲柯指著面前的小杌子。
蔡昭老實的過去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