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NA耶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好端端的,觀南鏡忽然撲進獄門疆裡和五條悟殉情去了(不),這一切發生得太快,讓他們完全反應不過來是怎麼回事。
“啊呀!怎麼會這樣呢?”
真人從屋頂上跳下來,跳在第一次顯得很破防的羂索身邊,帶著十成十的惡意快樂問:“你弟弟拋棄你和別人跑了?他不要你了嗎?你的身體怎麼也不聽你的話呢?哦呀哦呀,這到底都是怎麼一回事呢?”
跟在一邊的脹相三兄弟則是都很錯愕:“鏡怎麼會也被關進去?這也是你設計好的嗎?你早就想做掉他?你說話呀!”
漏壺則是眼睜睜看著己方忽然折損一枚強大咒靈,頭上的火山都噴起來:“五條悟身上帶著什麼法寶,他是怎麼把觀南鏡吸進去的!可恨,這該死的邪惡咒術師!鏡恐怕是凶多吉少了,他可能會在裡面被這魔頭殺掉!”
大夥:……
不是,漏壺,好像只有你稍微有點點弄錯情況了。
羂索沒有理會他們,只是蹲了下來檢查獄門疆的情況。已經在很短的時間內調整好了情緒,又或者沒調整好也沒辦法——封印確實完成了,但獄門疆要處理五條悟的速度比預料中慢了太多,對方還有餘裕來發動咒術把自己固定死在這裡是計劃外的一步。第二個問題在於觀南鏡奮不顧身地離開他撲了進去……
真是煩透了。
羂索已經過了遺憾於自己沒有所謂的“絕對力量”的年紀,他早就不再粗暴地想要擁有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天賦和咒力,渴望自己成為被上天眷顧和賜福的最強者。他從誕生時起,就弱小得彷彿無足輕重到根本上不了棋盤,無論是天元、宿儺、源信還是後來的太多強大的咒術師,他們才是攪弄時代風雲的傢伙,是咒術世界的中心、可以隨意主宰他人命運的主人。可事實如何呢?現在在玩弄這些傢伙的命運的是他。
他從連棋子都不配當的傢伙,變成了下棋人。
——但偶爾的偶爾,比如現在,他還是會有點感到一種暴怒:如果我擁有最強大的力量就好了。
為什麼命運如此愚蠢,總是讓那些只知享樂和為所欲為的人擁有最非凡的才華。
我會,直接殺掉你,五條悟。根本不用機關算盡、費盡心機,忍受你的所有這些,因為強大而肆意妄為、隨便侵毀他人心血的行為。
把我的孩子還給我!!!
“你們請自便。”在咒靈們商討下一步幹嘛的嚷嚷聲中,他平復心情,又冷靜下來思考對策——無論如何封印五條悟算是暫時完成了,雖然時間上出了點差錯,但一切依然算是在他的控制之內。他會想到辦法來救觀南鏡出來的,五條悟肯定不會殺掉他,只是不知道他會不會做些別的什麼……離間他們骨肉親情的事。
那倒是比殺掉觀南鏡還糟糕的情況,他用手撐住臉,眼睛暗沉下來。
“可以請您不要再握著我的手了嗎?”獄門疆內,觀南鏡正一邊細緻地用咒力造一個舒服點的房子出來:要雙人間,不知道能不能變出食物來,也不知道他們雖然不會死但會不會餓,但總之也留個廚房的位置,然後是客廳……一邊第不知道多少次無奈地被銀髮男人吸引走注意力。
“怎麼樣呢,有想起來一點嗎?”對方倒挺開心的,眼罩下的嘴唇翹起來,嘻嘻哈哈地晃著他的手說:“我們以前經常這樣哦。”
觀南鏡看了他一會兒,抽回手藏在身後,篤定道:“說謊。”
“真是的,怎麼還是這麼不好騙。”五條悟摸了摸自己的臉:“……啊,對了,那裡我想要一把巴塞羅那椅可以嗎,就是那種有腳踏的,對對對——太棒了!鏡的能力真是太棒了!”
觀南鏡:……
他確信自己從前認識他了,因為如果換成是別人在這麼戲弄他,他現在一定已經和對方打了三百回合了;如果是羂索敢亂鬧,那更是“屍體在說話”。但五條悟這麼做,他竟然挺心平氣和的,還按照對方的描述把沙發又改了改。
“這樣好了嗎?”對方舒舒服服地躺在了上面,觀南鏡的手從椅背上抽開,讓咒力維持住現有狀態,按了按彈軟程度,確認真皮的手感就要挪開,然後他的手就被另一隻大手握住了。
只是很短暫的一瞬間的過界,五條悟下一秒就規矩到簡直可以說是紳士地從懷裡掏出手帕放到扶手上,再托起他的手放到手帕上,從自己的中指上拔下了那枚戒指,溫柔地說:“就說鏡是笨蛋,我要是不給你的話,你什麼時候想起來要回去?”
他的眼睛,某一隻。
“一直在替你保管,該還給你了。看到這個,還是什麼都想不起來嗎?”
觀南鏡的指尖顫了顫,垂下睫毛看著對方緩緩把戒指套到他左手的無名指上……嗯?左手的無名指上?
“五條先生!”他終於有點受不了這種戲弄,無可奈何地搶過戒指,背對他坐到地毯上表達抗|議。對方躺回椅子裡放聲大笑起來,笑了一會兒後卻變成了捂著臉說:“別那麼叫我,鏡。”
“嗯?”觀南鏡隨口應付著,仔仔細細地打量眼珠。它和心臟完全不一樣,脫離身體時顯然已死去,被封在了寶石中。
看起來很美,栩栩如生,彷彿仍然活著,但確實已經乾涸得不能再幹涸了,詛咒縈繞,惡毒得很,如果不進行抵抗,盯著它看還會產生很多幻覺。
沒必要也不可能拆出來再放回眼眶裡。
“‘悟’,你以前都是叫我名字的。”五條悟沒起身,也沒在盯著他看,卻垂下一隻手偷偷卷他的頭髮,像一隻手段豐富的貓:“先從稱謂開始回憶吧?”
“又騙人。”觀南鏡不想把自己的眼睛戴到手指上,於是只收進口袋裡:“你說你是我的學長……那我只會叫你‘前輩’才對。”
“前輩……”這個詞脫口而出時,他卻是自己先愣住了,把字眼像怪味的糖一樣放在嘴裡,翻來覆去地,不知道是在逃避味道,還是在細細品嚐它,失神地來回呢喃。
想要順著這種感覺,找到迷霧重重的源頭:“……前輩。”
“嗯。”五條悟的手指碰了碰他的耳垂,輕聲應:“我在哦。”
06年的早春比往常要更冷。五條悟能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為終於在山裡找到觀南鏡的那個漆黑的凌晨實在是冰冷刺骨,冷到他不得不一直在增加咒力輸出,來抵抗寒冷,保持體溫。
在他身邊的夏油傑在用一隻小小的噴火咒靈取暖,此時也很體貼地挪到了兩人中間讓他蹭蹭暖氣,嘴上卻不饒人地嘲笑他:“至於嗎?我們又不是在北極,這麼點風凍得你。”
“你他爹有本事把咒靈收回去再說……”
他們倆就這麼一路罵罵咧咧上了山,在日出前才爬到頂,爬到頂才明白了為什麼在山腳下時連六眼都看不到那座任務書標註出的寺廟在哪兒,害得他們不得不慎之又慎地靠腿走——這座山已經塌陷了一半。
所以準確來說他們爬上的也是山的一半。
另一半正好在背面,已經深深嵌入在了地面深處。隨著初升的太陽,可能是最後施放結界的詛咒師撤離或沒命了,完整的情況才終於暴露出來,石頭破敗,在三分之二的高度能看到坍塌的廟宇和大片大片血跡,腥氣彷彿都撲到這裡來,整一個地獄圖景。
作為目前咒術界最年輕、也最有天資的兩個一級咒術師,五條悟和夏油傑搭檔的一年來已經處理了八起特級案件,但這個場面還是比他們之前見過的每一起都更誇張——那些畢竟是充滿破壞慾的咒靈乾的,這一次卻和咒靈無關,是人類所為。
更準確點來說是詛咒師們。
“人類的下限總是會嚇到我。”夏油傑喃喃自語,揮出一隻會飛行的咒靈去下面探探情況:“‘混沌體’到底是什麼意思,他們要一窩蜂來搶?那孩子一個人不可能應付得來,該死,我們是不是來遲了……”
“畢竟一個億的懸賞,什麼檔次,和我一個價……不過沒來遲哦。”五條悟手插在口袋裡專心致志地看著下方,不知道什麼時候抬起了兩片圓圓的小墨鏡,柔軟的銀髮被大風往後吹去,璀璨的眼睛亮得驚人:“我看到了。”
和夏油傑看到的“已經結束”的場面並不同,在五條悟的眼睛裡,這半座山其實都還籠罩在一種奇怪的、無形的咒力中時刻變化,並依然在不停殘忍地絞殺掉所有其他咒力源頭,無論它們是咒靈還是詛咒師,像是擁有了駭人的靈魂——直到只剩下一個人。
這片咒力的主人。
塌陷停止了,最後一顆石塊也咕嚕咕嚕滾了下去,發出沉悶的響,激起一片小小的塵土風暴,他們遙遙看到大概是寺廟正殿倒塌滾出的橫樑與瓦礫下,有一隻沾滿灰塵和血液混合物的小髒手從裡面伸了出來,掙扎著扒拉住了石頭路面的邊緣,又被割得鮮血直流……然後就沒有然後了,他好像被卡住了。
“啊!他怎麼這就不行了?”五條悟驚叫一聲,重新把墨鏡卡上:“這下是真的緊急了!喂,傑——”
求問,大概幾百公斤的石頭和木頭壓死一個忽然咒力潰散的重傷小男孩需要多久?再怎麼樂觀計算,情況顯然都十分不容樂觀。
夏油傑早抓著一隻鷹形態咒靈的爪子飛下去了。
“你倒是帶我一下啊,小氣鬼!”五條悟不滿地大聲嚷嚷,在霞光中迎著山風與累累血氣,縱身跳了下去。
把人從石頭裡挖出來後,他們又被迫等了大概兩個小時輔助監督開車來接,才踏上了回程的路:帶著這麼個好像剛從災難片片場裡被刨出來的屍體(……)上公共交通的話,他們毫不懷疑自己會被路人當場拿下扭送警察局。到時候還要高專去撈他們,那才真是大水衝了龍王廟,沒準還能上上社會新聞“兩名dk疑似當街拖屍”什麼的,豈不是要被夜蛾給罵死。
在等待和回去的漫長時間裡小屍體一直沒醒,五條悟犯困,都睡了兩覺還纏著輔助監督繞路去給他買了一後備箱的甜品啃啃啃啃啃了五六七八個後……對方還是昏沉沉地躺在那兒,一動不動的。
隨著幾次急剎車,卷著他的毯子也逐漸鬆開了,露出他髒兮兮的灰撲撲的血跡斑斑的臉,還有垂在座椅下隨著車晃動一起晃動、彷彿已經完全失去了控制的小手,就連一路沉穩的輔助監督都沉默了,不放心地瞟了好幾眼後忍不住問道:
“……這孩子確實還活著的,對吧?”
和小屍體一起在後排的夏油傑明明能聽到他在喘氣呢,卻故意裝模作樣地俯身聽心跳,然後瞳孔緊縮、大驚失色地彈了起來!
輔助監督被他嚇得差點沒方向盤脫手:“怎,怎麼了?”
五條悟完全看穿了他在惡作劇,屏氣凝神,高度配合,一副也很驚愕的樣子,更是把輔助監嚇得七上八下的心臟擊沉到了海溝深處去:“到,到底是什麼情況?沒命了還是要變異了?”
“監督……”夏油傑滿臉凝重地轉過頭來看著他:“你不說我還沒發現,他呼吸變強了,可能很快就要醒了,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吧。”
五條悟在副駕駛上用力點頭:“是啊!真是不得了呢!”
輔助監督:……
在接下來的車程中,他像是把嘴縫合上了一樣,哪怕五條悟在旁邊唱“監督你的耳朵為什麼那麼大,監督你的嘴巴為什麼不說話”都無動於衷,非常冷酷地一言不發,誓要用行動拒絕戲弄大人的可惡dk。他身邊的兩個也不惱,各自戴耳機聽歌,五條悟一直在看窗外,遇到有美女開車或者後座有可愛薩摩耶還按下車窗和人家sayhi,夏油傑則是閉上了眼睛養神——這一趟出門不用吞咒靈,對他來說倒是省了點噁心事,所以現在就格外舒服和倦怠。
直到小屍體確實在夏油傑預估的時間醒來了,他們倆才終於有了新的可關注物件。
“喂,混沌體,你叫什麼名字?”五條悟扒拉著椅背往後探著頭看,只看到對方髒兮兮地爬了起來裹著毯子蜷縮在對於他來說顯得太寬鬆的靠椅裡,彷彿聽不懂人話似的。
“嚇傻了嗎?”他嘟噥著,向夏油傑遞眼神。對方不用他暗示,已經出於仁義抽了幾張溼巾出來,溫柔地遞送在身邊人面前:“先擦擦臉好嗎?再喝點水。”
車子的速度很快,窗外的景色飛馳而過,外頭有轟隆隆的風聲。觀南鏡迷茫地看著他,其實耳朵還處於暫時失聰的狀態,可能是鼓膜破了,但他並不知道。他暫時還反應不過來發生了什麼事,頭一漲一漲地疼,心臟也是,彷彿在絞痛。記憶錯亂地盤桓在一起,仇恨的眼,尖刀,喊叫,倒塌,石頭,血,血一樣的流動的半透明的東西從他的身體裡冒出來。
他忽然捂住了嘴,夏油傑一怔,顧不得禮貌不禮貌的,一手按住他的脖頸不讓他嘔吐窒息,另一手捧著溼巾接在下面,背後也冒了個咒靈出來打算隨機應變,然而從觀南鏡的指縫中落下的只是絲絲縷縷黏稠的鮮血。他終於捂不住,又吐了一大口出來,消瘦的脊椎骨節礙手,在夏油傑的手掌中不住地顫抖。輔助監督到底是靠路邊停了車,皺著眉頭問:“需要緊急去醫院嗎?”
“不,需要緊急找硝子。”五條悟又把墨鏡扒拉了點下來,蹙著眉頭說:“真荒唐——他一醒,他的咒力就在攻擊他自己的身體,我從沒見過這樣的事。”
“小事情哦,只是因為他從來都不用咒力,一下子用多了身體就會超負荷——這是很好懂的道理吧。”
送給硝子前,五條悟和夏油傑面面相覷,以為他們昨天才新鮮出爐的學弟就這麼凶多吉少了,小屍體恐真成屍體!送給硝子才十分鐘,不僅人沒事,還被硝子麻溜地擦乾淨了(硝子:我在學處理屍體呢,不過這孩子還沒死所以我沒脫他褲子),忽然從荒山野屍(…)變成了長得非常漂亮的天使寶寶一枚,躺在那兒很可愛很乖巧地安穩呼吸著!
他們一起誠心誠意地鼓起掌來:“妙手回春啊硝子大夫!”
然後被硝子賞賜了一人一個腦瓜崩。
“我還沒說完。”她熟稔地掏出一根菸,夏油傑也熟稔地掏出打火機遞火。自從她學會了反轉術式後,她的學習壓力和工作壓力一下子劇增,香菸就成為了她新鮮的隨身物品:
“但是,正常的咒術師從來都不會遇到‘超負荷’這種問題,不是嗎?咒力這種東西,是天賦決定的,生來有就有,生來沒有就沒有,生來多久多,生來少就少。咒力只會枯竭,會熔斷,但不會超負荷——因為咒術師根本不可能透支出自己沒有的咒力來進行使用。”
“常識就不用解釋了,這種東西連傑這樣半路出家的咒術師也知道啊。”五條悟一邊架住夏油傑試圖揍他的手一邊問:“也是因為他是混沌體嗎?”
硝子若有所思:“不……其實好像是因為,之前被封印住了。”
夏油傑本能反對:“沒有那種能剝奪人類咒力十幾年的東西吧……”
“不是他。”硝子用左手在空氣中繞著圈比劃了一下:“是那種結界。”
“啊。”五條悟懂了:“那座寺廟?或者那座山?是咒力禁止的領域嗎?那也怪荒誕的……”
“有可能吧。但前些天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封印肯定碎裂了,而且那裡有個混沌體的訊息也被掛到了暗網上,開了一個億的懸賞……前因後果大概就是這樣了。”硝子眨了眨眼睛,輕聲問道:“現場還有活口嗎?”
夏油傑很沉默,五條悟倒是輕鬆地回答了:“沒了哦。但是具體多少普通人,多少詛咒師死在裡面了,得等到那頭清理完才能知道,一週後看報告吧。”
說著,他就手插在口袋裡繞過硝子進門裡去了,俯身很是好奇地打量床上的人。黑頭髮,看起來很蒼白,漂亮是漂亮的,漂亮得像一株精美纖細的花,就是有點不太健康的樣子,是不是深山老林的,又跟著和尚過,營養不良沒肉吃,所以沒長高長重啊?對於天天練體術的咒術師來說,這副體格有點弱得悲慘了。
“是血沒擦乾淨嗎?啊,不是,是痣。”
他手癢摸了摸對方的下巴,發出驚訝的感慨。畢竟這麼沒血色的臉上點著這麼鮮豔的顏色,還挺奇怪的。這麼想著,就手癢又摸了一下。
“忘了說了,五條。”硝子探頭說了一句:“注意別太粗暴,他心臟好像有點問題。”
夏油傑靠著欄杆,沉沉地嘆了口氣。
觀南鏡醒的時候完全忘記從昏迷到高專的路途了。應激狀態過去後,他的記憶終於清晰了起來,端莊跪坐在蒲團上和夜蛾正道和兩個坐得沒形狀的男生細細地講自己的遭遇。
他能記得自己的名字是觀南鏡,能記得從小到大的所有事情,能記得前天夜晚時分忽然在寺廟中闖入的怪人,忽如其來的屠殺,擋住他讓他走卻被一刀捅死的主持,然後就是忽如其來的從身體裡湧出的奇怪東西(那是咒力,笨蛋,五條悟插嘴道,被夜蛾一拳按在頭頂擰了兩下)……
“然後我就醒了,臉這裡有個痣的‘前輩’——她說她比我大,讓我喊她前輩——說是她治好了我……”
“哈?!等一下,等一下。”五條悟差點墨鏡掉下來,瞪大了眼睛,滿臉不可思議地指著自己和夏油傑問:“這是怎麼回事啊,你是怎麼完美跳過最關鍵部分的,一點都不記得了嗎?是我們倆救了你啊,我們倆!大半夜頂著風爬了兩小時,理解嗎?昨天還在車上一直護送你,傑還給你擦臉擦手——”
他玩心起來了,說著說著就著話頭,決心狠狠嚇唬小學弟一把,於是擺出了冷淡又挑剔的眼神來:“總之就是這樣了,我們救了你。但我們可不是什麼好人,救你是有原因的——夜蛾,這傢伙這麼值錢,按原計劃直接殺了好浪費哦,怎麼辦,把他燉了吃掉嗎?”
帶著一點點貓捉老鼠的惡劣笑容,他託著下巴,語氣是衝著他人搭話,眼睛卻故意直勾勾地盯著觀南鏡看:“還是大卸八塊做成特級咒具呢?那我要他的眼睛,也就這裡長得漂亮點。”
夏油傑微笑著捧哏,眼睛和善地眯成漂亮又上翹的線:“那我就要心臟好了。聽說心頭肉的效力總是最強的。”
觀南鏡垂著頭,默默不語,過了一會兒後俯身趴下開口,他們才發現他竟然已經哭了,聲音裡帶著淡淡的顫抖:
“救命之恩,沒齒難忘,就算要以命相還,也是我的運數。只是,家入前輩說這裡是高中,所以我想問,可以讓我上一天學再殺我嗎?我從來沒有讀過書,真的很想知道上學是什麼感覺……”
啊。
這種故意欺負人,結果得到的回覆卻可憐到讓人感覺會半夜忽然一睜眼懊悔“我真該死啊”的感覺是怎麼回事!沒等尬住的兩個人接上話,夜蛾正道就忍無可忍了。就算是在新生面前也不想給這兩個混球學長面子了,都什麼惡趣味!
他額頭上彷彿彈出了井字,一人一拳,胳膊架到了兩邊一黑一白兩顆腦袋上,狠狠地按住,旋轉痛毆!
“你們兩個!明知道他就是新學弟還欺負人!!!給我停嘴啊!!!”
“不,請問,這是……啊……”
觀南鏡本能地伸出手又縮回來,看呆了,看凝固了,看茫然了。
這就是他進入咒術高專的第一天,穿著病號服,安靜地跟在兩個頭頂鼓起大包的學長後面,穿過長長的木製走廊,路過雞爪槭、尋常竹、山櫻和許多鶴望蘭,最後停留在一排和式排屋前,五條悟拔了鑰匙扔給他,一腳踢開門,雙手抱胸靠在門框上,因為被揍了而情緒不算很高昂,頭側樂側示意這就是他的房間,和他說:
“喏,這間是你的,旁邊兩間是你同級的,他在外面出任務,明天你們再見面。考慮到你家都沒了,行李肯定是沒有了,需要什麼東西列個單子,會有人去買,急用的就先朝我們借吧——”
夏油傑無奈,直接和觀南鏡說:“不用擔心,也不用借東西,我有備用的,等會兒拿一份下來給你。”
觀南鏡輕輕說好,扭頭看向窗外,剩下兩個人不由得視線一起投過去。雖然是古式的房子,窗戶卻不是宣紙糊的,而是換成了落地窗。此時外面梨樹正花落紛紛,好像一場春日大雪。
“啊,都忘了這棵樹在你屋外——喜歡梨樹嗎?不喜歡的話換房間也沒關係,空房很多的。”
夏油傑體貼地補充了一句。
梨樹。
儘管在書中讀到過,但這是觀南鏡第一次親眼見,飛舞的花瓣從他清幽的深綠色眼睛中落下,好像他的瞳仁中也在落雪似的。五條悟看了一會兒他的眼睛,鬆開手走過來,一隻插回兜裡,另一隻按住他的頭頂狠狠揉了揉:
“我們和硝子是同級——就是早上和你打招呼的那個女孩子。所以明白要怎麼叫我們了嗎?”
觀南鏡仰起頭看他,髮絲柔軟,臉龐蒼白又稚嫩,像一隻幼鳥停留在他掌心,遲疑著喊:“前輩。”
離這一聲前輩,竟然已經過去十二年了。
“鏡,我第一次再見到你的時候,也應該直說的。畢竟你已經忘了我,又能知道什麼呢?所以其實想說這個的一直是我。”
獄門疆裡,五條悟的指尖又纏回觀南鏡的髮尾,輕聲說:“我好想你。”
他就著這個姿勢輕輕往下扯觀南鏡的頭髮,後者順從地仰起臉,他們就這麼一高一低倒錯著對視。
觀南鏡感覺自己的頭快裂開了,有什麼東西在從縫隙中冒出,就和髮絲一樣,緊密纏繞在他們靈魂上的……該死,是什麼,是什麼……他雙眼失焦地問:“我們是不是有……”
“我不知道束縛還管不管用了……”成年男子修長溫熱的指尖滑動到他的嘴唇上,按住,低聲說:“但還是試試吧——觸發條件是要接吻哦。”
“……”觀南鏡剛找到點回憶的感覺,立刻又卡住了!
他感覺自己一口氣差點沒上來,第一次動了點捅刀的心:“能不能不要在這麼關鍵的時候又騙我!!!請嚴肅一點——”
五條悟舉手投降:“好吧好吧,不鬧了不鬧了!!!其實是吻額頭,因為設定這個的時候,我覺得我這輩子也不可能讓別人親到我腦門上來的,誰知道真的會用到——來吧。”
他拍了拍自己的腿,右手撐著頭,唇角翹起,拖長聲音說:“來親前輩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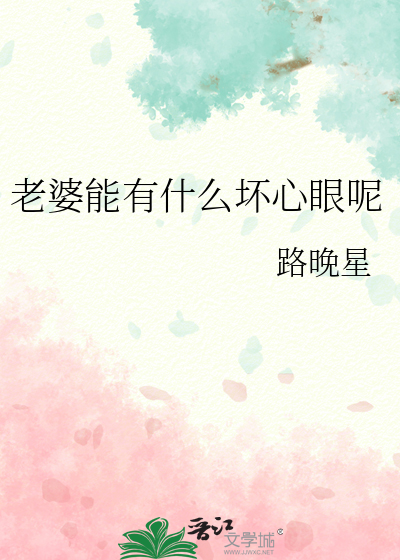

![太子今天被催婚了嗎[清穿]](https://img.shubaoinc.com/files/article/image/17/17743/17743s.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