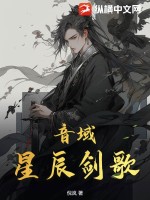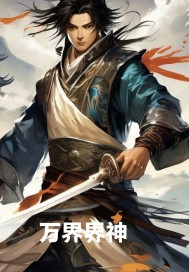血狸奴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駭人聽聞······”
“駭人聽聞吶·········”
幾乎同一時間,長樂宮,長信殿。
端坐於御榻之上,眯著眼,努力閱覽著手中簡報上的字,竇太后的神情之中,也隨即帶上了深深地駭然。
待竇太后將那封簡報放回身前的桉上,再次抬頭望向身前的天子啟時,竇太后那渙散的目光中,也不由得帶上了滿滿的凝重。
“楚王能做出這樣人神共憤的事,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
“不論是太祖高皇帝之時的楚元王劉交,還是先太宗皇帝時的楚夷王劉郢客,都曾是讓天下人,都爭相交口稱讚的忠厚老者。”
“楚元王一門的好名聲,也是遍及吳楚之地,從來都不曾有過絲毫的汙點。”
“怎料到了如今,到了楚王劉戊這一代,卻鬧出了這般駭人聽聞的醜事·········”
聽聞竇太后這一番滿是唏噓,又不乏些許驚駭的感嘆聲,安坐於竇太后身旁的天子啟,也只沉著臉緩緩點下頭,再悠然發出一聲長嘆。
說起這楚王劉戊,就不得不提到太祖高皇帝劉邦之時,劉氏宗親皇室,大抵是怎樣的組成結構。
——已故太上皇劉太公劉煓,一生育有四子,分別是長子劉伯、次子劉喜,三子劉季,以及,四子劉交。
其中的老三劉季,便是後世人常說的漢太祖高皇帝:劉邦。
在太公劉煓的四個兒子中,最有出息的劉邦,自然是親手建立了劉漢國祚,成為了劉漢社稷的始祖。
而劉邦的其他三位兄弟,也都在歷史上,留下了專屬於自己的傳奇······
老大劉伯;
作為漢太祖劉邦的親大哥,在世時,對劉邦這個‘沒出息’的弟弟,可謂是百般疼愛。
即便平日裡,劉邦總是遊手好閒,整天都帶著一群狐朋狗友鬼混,劉伯也從來沒有對此感到不滿;
只時刻銘記自己‘長兄如父’的職責,對弟弟劉邦,更可謂是有求必應。
——劉邦想花錢了,劉伯會從家裡的用度中拿出一部分,給弟弟劉邦花;
——劉邦惹事兒了,也還是劉伯去託人、去找關係,幫弟弟劉邦擦好屁股。
即便是劉邦在外面吹了牛,說要帶著一群朋友,到自己家裡吃飯時,劉伯也是從不抱怨;
而是任由劉邦帶著這麼一群狐朋狗友回家,並親自款待這些日後,為劉邦鞍前馬後,為漢室立下汗馬功勞的‘狐朋狗友’。
就這麼一直忙碌到中年,莊稼漢劉伯,也終是在秦始皇末年離世;
而在劉伯離世之後,劉伯的妻子,也就是漢太祖劉邦的兄嫂,卻是對這個不出息的小叔子愈發感到厭惡。
由於不滿劉邦總帶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回家吃飯,劉伯的妻子便開始使壞;
每逢劉邦帶人到家裡吃飯,就用鏟勺使勁剮鍋底,發出‘吱吱’的摩擦聲,以表示家裡沒飯了、不能款待劉邦的客人們了。
但等劉邦疑惑地來到廚房,卻總能看見:廚房的斧內,盛有滿滿一整鍋肉羹。
這樣的事發生接連好幾次,劉邦自然也就明白了嫂嫂的心意,便自此不再帶朋友去大哥家,免得自討無趣。
只是這個‘仇’,卻被小心眼的劉邦記在了心中。
後來,曾經的小混混劉邦搖身一變,成為了漢太祖高皇帝,豐沛劉氏,可謂是雞犬升天。
別說是姓劉的了;
凡是祖上三代,能跟豐沛沾親帶故的人,都自此成為了‘皇帝的鄰居、天子的鄉黨’。
至於豐、沛二縣,更是被劉邦大筆一揮:永不徵稅賦!
外人尚且如此,那些個劉姓的親戚,劉邦自也是一個都沒落下,能封王的一律封王;
便是早已死去的大哥劉伯,劉邦也沒忘追諡其為‘武哀王’,以表達自己對這位亡兄的敬重,和思念。
可唯獨對大哥劉伯的家人,也就是那個曾經,用湯勺刮鍋底的嫂嫂,以及大哥劉伯家的獨苗,劉邦卻遲遲沒有敕封。
對於這個狀況,嫂嫂自然是心裡有數,不敢去找劉邦,便只能暗中慫恿兒子劉信,去跟太上皇劉煓求情。
被孫兒這麼一求,又考慮到大兒子早亡,孫子劉信更是大兒子唯一的獨苗,劉太公便也心生不忍;
召來皇帝兒子劉邦,就委婉勸說道:過去的事,就讓他過去吧;
你已經做了皇帝,就應該有起碼的容人之量······
你大哥在的時候,對你不錯,如今你大哥不在了,就留下那麼一對孤兒寡母;
而你如今,也顯赫了;
如果不報答亡兄的恩情,天下人,又會怎麼看待你這個皇帝呢?
被老爹這麼一勸,劉邦也是稍放下了心中的芥蒂,但也依舊無法原諒當年,自己帶朋友回家,嫂子卻當著外人的面,對著自己勐刮鍋底的往事;
一邊是心裡的彆扭,一邊是老爹的勸說,以及‘天子要有容人之量’的說辭;
各種因素結合之下,劉邦最終也只能咬牙切齒的,將大哥劉伯唯一的血脈子嗣,封為了徹侯。
只不過,即便到了封侯的時候,劉邦也依舊沒忘噁心一下這對命苦的母子;
——武哀王劉伯唯一的兒子劉信,被太祖高皇帝劉邦敕封為:羹頡侯。
什麼意思?
羹者,肉羹也;
頡者,通戛,音也,;
所謂羹頡,就是在盛肉羹的鍋底,刮出‘戛、戛’的聲響。
換而言之:劉邦將大哥的兒子劉信,封為了‘刮鍋底侯’······
大哥一家如此,二哥劉喜一家,也絲毫沒讓劉邦省心。
在劉邦微寒之時,太公劉煓就曾拿二哥劉喜,來作為教育劉邦的桉例。
太公對劉邦說:你看看你二哥!
踏踏實實種地,本本分分做人,一點都不讓我為他擔心;
再看看你?
——整日裡遊手好閒,不事生產,根本比不上你二哥勤奮!
結果這話才剛喊出口沒幾年,劉季便搖身一變,成了漢皇劉邦。
回想起父親曾經的教誨,劉邦也難免有些志得意滿;
便在家宴中指著二哥劉喜,對父親劉煓說道:過去,父親總說我沒二哥有出息;
那按現在的情況來看,我和二哥,誰更有出息呢?
是幫助父親,種好了那幾十畝地的二哥?
還是獨自一人,便建立了劉漢社稷的我呢?
再怎麼說,當時的太公劉煓,也好歹是當朝太上皇;
皇帝兒子臭顯擺,劉煓面子上自然是掛不住······
——當晚就氣的多吃了兩碗飯!
至於劉邦,雖然嘴上拿二哥氣老爹劉煓,但對二哥劉喜卻也絲毫不吝嗇;
出手就是一個‘代王’的王爵,讓劉喜去代國抵禦外敵。
結果劉邦前腳剛封二哥劉喜為代王,後腳就是韓王信,在代北的馬邑投降了匈奴;
聽到韓王信投降匈奴的訊息,劉邦卻是自信滿滿的將胸口一拍:沒事!
——代國,還有我二哥劉喜呢!
怎料劉邦這話剛說出口,邊牆便又傳來訊息:匈奴人還沒打來的時候,本該阻止防禦的代王劉喜,便拖家帶口跑到洛陽去辣······
匈奴騎兵前追後趕,愣是連劉喜的影子都沒追上、連劉喜的馬車揚起的灰塵都沒看到······
得知此事,劉邦自是勃然大怒,又礙於戰事危急,只能率軍從長安出發,以御駕親征;
沿途路過洛陽時,劉邦也沒忘對二哥劉喜一頓臭罵,又強保下了二哥劉喜的性命,廢除劉喜的王爵,貶為合陽侯。
——堂堂一國之君,遭遇外敵入侵,非但不戰,反棄國而逃!
若不是頭頂上的‘劉姓’,和新豐櫟陽宮的老爹劉煓,單是這一項罪名,就夠劉喜死上個百八十回!
也正是這一場因劉喜‘臨戰而逃’,才導致邊牆糜爛的漢匈大戰,最終演變為了漢匈歷史上,唯一的一次‘王對王’。
——漢天子劉邦,與匈奴單于冒頓,在平城正面遭遇!
最終結果,卻是劉邦輕敵冒進,身陷白登之圍······
被二哥害得這麼慘,劉邦自也不敢再相信這個二哥,只以豐厚的賞賜、俸祿供養,卻從未曾再給予劉喜任何實權;
但到了劉邦駕崩前的一年,淮南王英布發動叛亂,將荊王劉賈悍然殺死之後,劉邦身邊的豐沛老臣們,便又開始為合陽侯劉喜求起了情。
哎呀~
陛下呀~
都是一家人~
血濃於水的······
諸如此類的勸說之語,也惹得劉邦不勝其煩,同時也確實苦惱於劉賈死後,荊地沒有宗親鎮守;
最終,劉邦也只能遵從老夥計們的勸說,將二哥劉喜的兒子,封去了荊地做王。
只不過,這個被劉邦封去荊地的侄子,卻並沒有成為‘荊王’,而是做了吳王。
沒錯;
——如今的吳王劉鼻,正是太祖高皇帝劉邦的二哥:代頃王劉喜的長子。
而在如今,漢家皇位都傳到了劉邦的孫子輩,作為劉氏‘二代’長輩的吳王劉鼻,也早已年過花甲······
大哥、二哥都說完,也不得不提與這二者形成鮮明對比,甚至都不大像劉氏作風的老四:劉交。
作為太祖高皇帝劉邦唯一的弟弟,劉交可謂是自幼,便集萬千寵愛於一身。
在秦始皇統一天下前後,老劉家的老大劉伯、老二劉喜都忙著種地,老三劉邦則忙著在豐沛‘結交好友’;
唯獨小四劉交,在父母雙親,以及幾位哥哥的資助下到處遊學,成為了老劉家少有的‘讀書人’。
——論學術成就,劉交的來頭可著實不小!
——劉交的恩師浮丘伯,是和曾經的秦相李斯、公子韓非,漢初的太中大夫陸賈,以及北平侯張蒼一起,在荀子-荀卿門下聽講的同學!
換而言之,即便是見了秦相李斯,劉交也能毫無顧慮的稱呼李斯一聲:師叔。
除了老師浮丘伯的名氣,劉交自己的學術成就,也是相當的優秀。
尤其是在對《詩經》方面的造詣,劉交更是名聲在外,親自綴集的詩傳《元王詩》名揚天下;
即便是到了如今,治《詩》的文人士子們,也基本是人手一本《元王詩》。
有如此高的文學造詣,自然也從側面表明了劉交此人,屬於絕對意義上的文化人。
與劉交享盛名於天下的學術成就對應的,便是至今為止,都仍舊讓天下人為之讚歎的嚴謹門風。
——想當年,太祖高皇帝還在的時候,楚王劉交一家,便已經成為了‘三好模範宗親’的代名詞;
劉交的兒子們,也是一個比一個謙遜有禮、一個比一個溫善純良。
對於這些德行兼備的好王子,長安朝堂也不忍心浪費,接連將劉交的幾個兒子,任命為朝堂之上,主管禮法制度的奉常。
到了近些年,長安朝堂甚至出現了‘只要是劉交的兒子,便生下來就能做奉常’的風論!
事實也確實如此:過去幾十年,作為九卿之一的奉常一職,便幾乎一直是被劉交的幾個兒子所壟斷。
但可惜的是,如今的楚王劉戊,並不是這位‘能生出一窩奉常’的楚元王之子;
而是楚夷王劉郢客之子、楚元王劉交之長孫······
祖父、父親,以及叔叔們的德行,楚王劉戊是半個字都沒學到。
倒是紈絝二代們特有的技能,讓楚王劉戊挨個學了個遍。
到如今,更是鬧出這駭人聽聞的家庭醜聞,讓天子啟都不得不將蓄勢待發的《削藩策》先放在一邊,專門騰出手,來先解決楚王劉戊的問題······
“皇帝認為,應該如何解決此事呢?”
母子二人默然對坐許久,終還是竇太后低沉的詢問聲,打破了殿內的寧靜。
便見天子啟聞言,本就陰沉的面色,不由又黑下去一分;
繃著臉思考了好一會兒,才神情嚴峻的抬起頭,望向身前,同樣神情陰鬱的太后竇氏。
“孩兒認為,母親,或許應該準備從平陸侯劉禮、紅侯劉富二人當中,選一個新的楚王了。”
“——楚元王一脈的名聲,不能被劉戊這個不屑子孫敗壞;”
“楚王的位置,必須由楚元王的兒子坐上去,才能讓孩兒稍稍安心······”
聽聞劉啟此言,竇太后不由得深吸一口氣,唏噓感嘆著,終也只得無奈的點下頭。
平陸侯劉禮、紅侯劉富,便是太祖高皇帝四弟——楚元王劉交的兒子當中,德行最為突出的二人。
同時,也是劉交尚在世的兒子當中,年紀最大的二人。
過去這十幾二十年,長安朝堂的‘奉常’一職,便基本都是在這兄弟二人手中,像皮球一樣傳來傳去。
說的再具體一些,就是劉禮做累了,便換劉富頂兩年;劉富生病了,再由劉禮撐兩年。
就這麼輪換了十好幾年,直到最近幾年,這老哥倆才終於歇了下來。
——因為劉禮的兒子劉道,終於長到了能替父親、叔叔接過重擔的年紀;
至於劉富的兒子,雖然年長的幾個有些沒出息,但年少的幼子劉闢強,據說不到十歲的年紀,便已經‘頗得乃祖元王之風’!
等以後,劉禮的兒子劉道老去,劉富的兒子劉闢強應該就能站出來,繼續完成楚元王一脈,對‘漢奉常’一職長達數十年的壟斷,和‘世襲’。
至於如今的楚王劉戊,作為楚夷王劉郢客的獨苗,在鬧出那般駭人聽聞的醜聞之後,已經是留不得了。
且不論劉戊的所作所為,可能對楚元王一脈造成的名望損害;
單就是此事,可能對劉氏皇族造成的損害,也使得天子啟無論如何,都必須將‘劉戊’這個名字,從劉氏宗譜中抹去!
而劉戊作為楚夷王劉郢客的獨子,眼下既然‘非死不可’,那楚王的位置,自然只能交到元王劉交的其他兒子手中。
對於這一點,竇太后心裡,顯然也有所準備。
“這件事,沒有什麼商量的必要。”
“楚王劉戊的結局,已經是註定了的;”
“但皇帝也不要忘了:那一紙《削藩策》,皇帝能暫時放到一邊去,可吳王老賊,卻不會放過這個好機會。”
“就算為了宗廟、社稷的安穩,劉戊的事,也得暫時壓下去。”
“若不然,萬一讓劉戊也跟著劉鼻老賊,做了那悍然舉兵的賊子,對宗廟、社稷而言,恐怕,就不是什麼好事了······”
沉聲道出一語,見天子啟並沒有立刻點頭應是,竇太后也不由深吸一口氣,而後便將目光從劉啟身上移開。
“削藩的事,關乎到我漢家的生死存亡,不可以不慎重。”
“具體如何操作,皇帝,可以多聽聽老臣的意見。”
“——尤其是丞相申屠嘉的意見。”
“至於楚王劉戊,終究只是我劉氏自家的醜聞,什麼時候收拾,都不算晚······”
聽聞此言,總是心中仍滿含盛怒,天子啟也只得深吸一口氣,強自將怒火壓了下去;
又低頭思慮一番,才終是對竇太后微笑著一拱手。
“母后教誨,孩兒,銘記於心······”
澹然一語,也終是讓竇太后面上嚴峻之色散去;
不由溫笑著側過頭去,似是隨口一提道:“聽說轅固,被皇帝趕回關東老家去了?”
見母親提起此事,天子啟自是趕忙點了點頭,又擺出一副‘小事一樁,母親可千萬別因為這件事,就對孩兒太滿意’的神容。
卻見竇太后面帶微笑的搖了搖頭,低頭思慮片刻;
過了好一會兒,才似是終於下定了什麼決心的竇太后,終是將溫和、慈祥的目光,撒向了眼前的天子啟。
“這件事,小九這幾天,沒少在我耳邊嘮叨;”
“聽了那小子的話,我才想起來:在那些個文人士子面前,皇帝,也有自己的難處······”
“——轅固的事,是我太咄咄逼人,沒有給皇帝留下餘地。”
“等過上了三兩年,皇帝便尋個由頭,將那轅固,重新召回長安來吧······”
平緩,而又溫和的語調,也惹得天子啟不由一怔;
望向竇太后的目光中,更是隱隱帶上了些許驚詫!
卻見竇太后滿是無奈的笑著搖了搖頭,伸出手,在天子啟的手背上輕輕拍了拍。
“再怎麼說,我也是皇帝的母親~”
“做母親的,哪有給兒子添麻煩的道理?”
“——再者說了;”
“就轅固那張臭嘴,普天之下,也就我和皇帝有這個胸襟,能容的下他。”
“可若是讓他老死在關東,對皇帝而言,卻是一件名望大損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