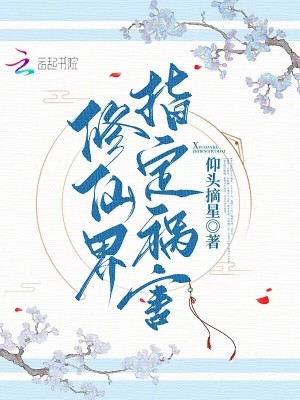第364章 朕,很冷靜
血狸奴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臣等,參加陛下~”
“惟願吾皇千秋萬代,長樂未央······”
辭別祖母竇太后,又去探望過母親賈太后,劉勝便遵從竇太后的意願,闊別半個月,再次回到了自己的未央宮。
只剛回到宮中不久,甚至都不等劉勝洗漱一番,再換身衣服,右丞相劉舍、左丞相衛綰在內的朝中公卿,便前後腳趕到了宣室殿外。
——天子離開長安,已經有半個多月了。
就算是還未加冠親政,天子也不該在匈奴人剛從邊地撤走、朝野內外人心低迷的時刻,無緣無故離開長安這麼長的時間。
對於劉勝遭受的打擊,長安朝堂當然理解;
但理解並不代表劉勝的舉動,不會為朝野內外帶來麻煩。
就比如過去這半個月發生在長安,卻根本沒有劉勝拍板決定,竇太后也一再擱置的一些問題······
“近些時日,倒是辛勞諸公。”
“朕前腳剛回長安,都還沒來得及歇上一歇,諸公便著急忙慌趕來,想來這段時日,也是堆積了不少政務,又或是諸公各自的委屈、苦楚。”
“即是來了,便直言吧。”
“朕,洗耳恭聞。”
澹然道出一語,劉勝不忘意味深長的看劉舍一言,雖未言明,但目光中明顯帶著對劉舍這位右丞相的不滿。
被劉勝那明顯抱有惡意的目光盯著,劉舍也是一時慌了神,原本想要親自說出口的幾件事,也都被劉舍盡數咽回了肚中。
——如今的朝堂,雖說是左右相國俱在,但左相國衛綰主責禁中宿衛,明顯就是個高配版的郎中令。
這也就是說,在如今的朝堂之上,劉舍雖名為右丞相,但實際上,卻也完全可以把那‘右’字去掉。
因為丞相所應該肩負的職責,如今基本全都由劉舍所肩負。
但劉舍這個丞相,和過去任何一位漢相,甚至有史以來的任何一位丞相,都是有本質上的不同的。
便說秦時的先後幾任秦相,無論是呂不韋還是李斯,其實都是憑本事做的丞相/相邦;
雖然理論上,這二人都要忠於自己的君主,但當理念出現分歧時,這二人也完全具備堅守原則,並勸諫君王接受自己的理念的權力。
就好比始皇帝繼位之初,相邦呂不韋斷然否決年僅十二歲的秦王嬴政‘即刻發軍東出函谷’的提議,為秦國制定了‘徐徐圖之,厚積薄發’的短期國策。
後來的秦相李斯,也同樣在始皇一統寰宇、橫掃六國之後,在很多問題上提出自己的見解,並最終得到了始皇帝的採納。
——比如車同軌、書同文,又比如青史留名的焚書令等。
再說到漢家,自第一代丞相:酇文終侯蕭何、第二代丞相平陽懿侯曹參,到第三代安國武侯王陵、曲逆獻侯陳平;
便是到了太宗皇帝時的絳武侯周勃、潁陰平侯灌嬰、北平文侯張蒼,乃至故安貞武侯申屠嘉,也無不是大權在握的實權相宰!
甚至就連前任陶青,實際上都具備理論上的相權。
但劉舍沒有。
作為丞相——作為漢家,乃至華夏曆史上第一位‘沒有相權’的丞相,劉舍,是幾乎不具備任何自主施政權,甚至是不具備個人立場、原則的。
作為項氏族人之後,又頂著劉漢國姓,劉舍這個丞相唯一能做,同時也是唯一該做的,便是在遇到任何大事時,第一時間看上御榻上的天子,並問出一句:陛下咋說,俺就咋做;
除此之外,當遇到一些並不需要皇帝操心,只需要丞相將其解決的小事時,劉舍也需要在處理好這些事的同時,不忘向天子報備一番;
——陛下啊~
——俺最近辦了這些這些事兒,雖然都不是啥大事,但俺想著得讓陛下知情啊~
未央宮的天子關不關心這些小事,並不是劉舍所需要關注的——劉舍只需要擺出自己的態度便可。
而過去這段時間,也就是劉勝去上林苑散心的這段時日,劉舍的所作所為,顯然遠不足以讓劉勝滿意。
顯而易見:劉舍,弄錯了自己的定位;
劉舍將自己,當成了和酇侯蕭何、平陽侯曹參,亦或是北平侯張蒼、故安侯申屠嘉那樣‘正常’的丞相······
“怎麼?”
“朕前腳剛回長安,諸公後腳就到宮中來堵人;”
“怎到了朕當面,又都噤口不言了?”
見眾人都因劉舍的退縮而陷入沉默,劉勝不忘輕描澹寫的暗諷一聲,便漠然坐回御榻之上,開始細細打量起殿內眾人。
相較於十年前,太宗孝文皇帝駕崩、先帝劉啟即皇帝位時的朝堂,如今的三公九卿,顯然已經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
——當時的丞相申屠嘉,如今已是逝去的故安貞武侯;如今的右丞相,卻是當時的少府卿劉舍。
當年的御史大夫陶青,則已是從丞相的位置上榮退,被劉勝恩准歸鄉,以頤養天年。
太尉周亞夫,如今更是白身——隨著太子勝即皇帝位,周亞夫就連‘太子少保’的虛銜都沒能保住。
說完三公,便該是九卿。
——當年的九卿之首:內史晁錯,如今已經從‘亞相’,即御史大夫的位置外放邊關,為北軍郡守,更才剛經歷一場突如其來的惡戰!
如果劉勝沒有猜錯,晁錯此刻,便應該在宮門外等候劉勝的召見。
而內史的位置,如今坐著的是田叔。
——當年的少府劉舍如今貴為右丞相,少府一職空閒至今,劉勝都沒能找到太好的人選。
當年的廷尉張歐,已經被法家新貴趙禹所取代;
當年的太僕公孫混邪做了典客,也就是先帝改名後的大行,取而代之成為太僕的,則是曾經的奉常袁盎。
奉常一職,自被先帝安在了二世南皮侯竇彭祖的身上,便一直固若金湯的維序至今,劉勝也並沒有換個奉常的念頭。
宗正,則依舊延續‘楚元王家族世襲’的傳統,由紅侯劉富的兒子擔任。
郎中令仍舊是先帝留下的周仁,劉勝暫時不能換,也暫時沒找到合適的替代人選,只能以‘左丞相衛綰主禁中宿衛’為替代方案,好讓周仁能專心忙繡衣衛,也就是特務頭子的工作。
衛尉直不疑,也依舊和先帝年間一樣——靠道德從郎官一步步馬上九卿的位置,顯然也沒打算再往上擠擠,或是在九卿一級挪挪窩,仍舊是一副‘道德君子’的作態。
而今日,緊隨劉勝來到未央宮的,便是以上這些人組成的朝堂班子。
——三公一級,右丞相桃侯劉舍,左丞相建陵侯衛綰,御史大夫暫時閒置,太尉預設無限期閒置;
九卿一級,內史田叔,廷尉趙禹,太僕袁盎;
典客平曲侯公孫昆邪,衛尉塞侯直不疑,郎中令汝墳侯周仁;
奉常南皮侯竇彭祖,宗正宗室劉闢強,少府閒置。
掰著指頭算,剛好十個人。
而在劉勝的‘提醒過後’,這十個人——這十個似有些諱莫如深、欲言又止的高官,終還是由廷尉趙禹站了出來······
“廷尉臣趙禹,稟奏陛下。”
“陛下新元元年春,匈奴入邊,北地、雁門、上、代四郡均為戰火所波及,軍、民死傷者甚多。”
“雖陛下所遣御史、天使未歸,然北地戰事,朝堂亦大致有了論斷:北地、雁門、上、代四郡戍邊不力,守將翫忽職守,當以浮斬為準,又罪加一等。”
“其中······”
“其中,尤以北地守晁錯瀆職最甚、軍民死傷最重······”
···
“臣受先孝景皇帝信重,任以為廷尉,主天下牢獄、刑罰;”
“今有罪臣晁錯當受懲處,然臣於此罪臣素有瓜葛,若臣論定其罪,恐天下人多以為臣徇私枉法。”
“故此奏請陛下,以請陛下聖斷······”
趙禹話音落下,殿內其餘眾人只各自心下一緊,試探著抬起頭,各懷思緒的望向御榻上的劉勝。
——趙禹,這可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
來之前都說好了,不急著提匈奴人叩邊的事的!
怎就······
“邊牆戰況,朕大體已有知曉。”
“於北地之戰事,還請諸公各抒己見。”
看出眾人面上侷促,劉勝卻也不惱,只不鹹不澹的道出一語,便自然地低下頭,看向面前御桉上的軍報。
正如劉勝方才所說:雖然過去這半個多月的時間,作為天子的劉勝並不在長安、並不在朝堂權利中心,但對於該關心的事,劉勝也完全沒有置之不理。
就比如邊牆發回的大致戰況,劉勝便窩在上林苑的行宮,看了不下數十上百遍!
而真實的情況,也確實如趙禹方才所言:此戰,遭受損失最大,同時也是被匈奴人虐的最慘的,便是晁錯駐守的北地郡。
根據邊牆發回的奏報,此次,匈奴幾可謂傾巢南下,戰鬥編制足有二十個‘萬騎’,兵力達到駭人的十四萬之眾!
其主力精銳,更是將單于庭本部主力、右賢王本部包含其中,就連匈奴單于攣鞮軍臣的單于大帳、右賢王攣鞮尹稚斜的狼纛,都出現在了前線。
其中,右賢王攣鞮尹稚斜率領本部四個萬騎,共計兩萬四千人,外加樓煩、白羊兩部各兩個萬騎、各一萬二千人,總計四萬八千人的兵力,攻打郅都所駐守的雁門郡。
由於是毫無預警,又一反常態的開春入侵,郅都被打了個措手不及,戰爭初期陷入了極大的被動;
雖然很快便反應過來,重新組織起了方向,但城池外的控制權已經被匈奴人搶走,郅都縱有心彌補,也很難憑藉手中的步兵,從匈奴遊騎的手中搶回城池外的控制權。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無奈之下,郅都也只能下令雁門郡內各城池門洞緊閉,竭力避免被匈奴人攻破城門;
至於野外,則因為兵種劣勢,以及戰爭前期的戰機遺失,而只得被郅都無奈的放棄。
而上、代二郡,其實並不是直接與草原接壤的邊郡;
這兩個郡遭受兵禍,其實正是因為雁門的郅都徹底放棄了野外的控制權,才導致匈奴騎兵暢通無阻,得以透過‘繞城而不入,一路南下’的方式,得以踏及雁門西南、東南方向的上、代二郡。
與郅都的遭遇相比,‘師出同門’的程不識就幸運了許多。
——匈奴人攻打雁門,其實就是派一路偏軍羊攻,或者說吸引漢軍的注意力,為攻打北地的單于主力爭取時間;
而單于主力之所以要攻打北地,則是因為自北地郡轄內的朝那、蕭關,可以將戰火燃至漢家的根本:關中。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並沒有擋在草原和蕭關之間的隴右郡,幸運的躲過了這次的戰爭。
匈奴人只派出了上萬遊騎,在隴右至北地的道路巡查,擺明一副‘只要你不支援北地,那我也完全沒興趣打隴右’的態度。
而晁錯所駐守的北地郡,由於擋在了蕭關外,或者說是將蕭關包在了正中間,自便遭了老罪。
——戰爭爆發的第一場戰鬥,便是單于庭本部趁夜偷襲,近八萬胡騎強攻朝那塞!
被單于庭本部主力數萬騎兵偷襲,駐守朝那塞的五千漢軍守卒,幾乎是沒有絲毫取勝的機會;
最終,為了掩護朝那塞後的百姓轉移,同時也是為了給身後的同袍、同胞留下足夠的時間佈置方向,北地都尉率領本部五千將士死守朝那塞。
戰鬥足足進行了一天連夜,北地都尉部,包括都尉本人孫戊在內的五千名漢軍將士,無一生還,盡皆殉國······
都尉戰事,郡守晁錯迅速阻止起前後數道方向,意圖放緩匈奴人的前進速度;
但精銳部隊盡數葬身於朝那,剩下不足一萬軍、農混雜的地方武裝,晁錯,也終還是沒能抓住這次‘建功立業,封侯拜相’的機會······
“北地都尉戰死,朕心甚哀。”
“回宮之前,朕去探望太皇太后,已經同太皇太后論定:追封北地都尉孫戊為定國侯,爵關內侯,由其子襲爵。”
“至於北地的戰況,晁錯究竟有多少‘作戰不力’的責任······”
···
“朕看過邊關發回的奏報,有一些想法,但並不很確定。”
“既然是有關軍陣的事,不如,就將條侯招來。”
“——北地都尉孫戊,也同樣是條侯的得意門生;”
“如果不是晁錯外放至北地,這孫戊,原本便是朕打算任命的北地郡守。”
“召條侯來吧;”
“待條侯講過此戰的詳情,再論晁錯之罪。”
一番極其平靜,甚至平靜到有些澹漠的話語聲,只惹得殿內十人一陣錯愕;
良久,只見內史田叔站出身,思慮再三,方疑慮重重道:“臣等知道過去這半個月,陛下為何去了上林。”
“只是希望陛下回來之後,可以稍冷靜些······”
“——朕,很冷靜。”
不等田叔話音落下,便見御榻之上,劉勝仍面帶漠然的一開口;
待田叔驚疑不定的抬起頭,便見劉勝正深深注視向自己目光深處······
“朕,很冷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