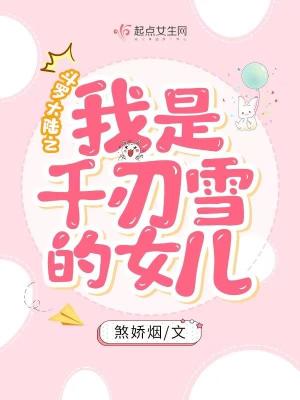第417章 改革御史大夫
血狸奴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六成。
這是一個非常觸目驚心的比例。
什麼意思?
——這就好比後世新時代的第一次公務猿考試考完半年之後,透過者當中有六成都蹲進了大牢。
這等比例,別說是在後世的新時代了,哪怕是在賄賂成風的當今漢家,也同樣是極為驚人。
半年就有六成,那一年、兩年呢?
怕是要不了多久,劉勝辛辛苦苦透過考舉選拔出來的官員,就要盡數去陪哥哥踩縫紉機。
更重要的是:這批蹲大牢的蠢材,不單單是‘考舉出身’的身份,同時還擁有著‘第一批考舉受益者’的群體標識。
對於考舉這一新興事物,長安朝堂的態度其實一直是觀望。
因為勳貴們不知道這個新冒出來的官員選拔制度,究竟是在斷自己家族的未來,還是在給包括自己在內的元勳功侯開後門。
百官公卿也同樣不知道考舉——並不像察舉那般需要人舉薦,需要嚴格審查才能,而僅僅只需要報名就能參加、筆試透過就能高中的考舉,究竟是不是一個好玩意兒。
所以,毫不誇張的說:第一批透過考舉入仕的官員,幾乎就是考舉制的天然代言人,甚至是唯一代言人。
這個群體的狀況,幾乎可以與科舉制度的未來直接掛鉤。
——第一次考舉選出來了幾個國士,那沒說的,劉勝往後每年舉行一回科舉,都絕不會有人再嘰嘰歪歪。
畢竟考舉這東西有效果嘛,都選出來好幾個國士了。
若是這第一批考舉出身的官員碌碌無為,朝堂則大機率會賣劉勝一個面子,羊裝無辜的全當沒有考舉這回事。
如此一來,往後劉勝再提起科舉,也總得掂量掂量自己的臉皮,夠不夠厚到想要再招一批酒囊飯袋入仕,然後在有司屬衙吃白飯、領白俸。
而現在的狀況,卻無疑糟糕到了極點。
第一批考舉出身的官員,在入仕短短半年的時間內,便有過半人因罪入獄。
而且劉勝基本能篤定:這些個蹲大牢的人,十有八九是因為受賄。
早在去年,考舉結束之後,將中舉者分配給關中郡縣地方、長安九卿有司屬衙之時,劉勝其實就已經暗下做過交代:只要不是原則性的錯誤,就對這些個愣頭青多點耐心、多點包容。
雖然沒有明說‘這群蠢貨如果撈錢,就睜隻眼閉隻眼’,但在這個賄賂之風極為猖獗的時代,皇帝授意優待某一個群體,那也基本等同於預設這個群體以公謀私了。
這,也正是讓劉勝告到頭疼不已,甚至有些百思不得其解的原因。
——劉勝,明明已經打過招呼了!
為了保留自己的政治果實、為科舉制度開個好頭,並細水長流的傳延下去,劉勝已經將自己對官員的原則、標準,在這第一批考舉入仕的官員身上一降再降。
到最後,已經降到了‘只要別作奸犯科,或太明顯的尸位素餐’,就可以容忍其存在的程度。
那麼,問題來了。
劉勝這邊該打的招呼打了,朝野內外容忍這幫愣頭青也容忍了,但凡是還能壓下一口氣的,就都以包容、耐心對待了這個群體。
可即便是這樣,這個群體也還是在短短半年時間內,就損失了超過六成的‘兵力’。
這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這個群體撈錢的吃相,難看到了趙禹都看不下去——哪怕劉勝打過招呼要優待這幫愣頭青,也依舊看不下去,只能冒險違背劉勝的交代,懲治這幫愣頭青的程度。
但劉勝怎麼都想不明白:怎麼這才剛做官,烏紗帽都還沒戴熱,就開始這麼不顧吃相的大撈特撈了?
哪怕裝個三兩年,甚至哪怕是半年?
“唉······”
“一群不爭氣的東西啊······”
如是想著,劉勝便滿是哀愁的發出一聲長長哀嘆,旋即便將目光落在了開口之人:田叔身上。
對於官員受賄問題,劉勝有心做些什麼,卻很難在短時間內起到效果。
但就算如此,劉勝,也還是要從現在開始,就學著慢慢做些什麼······
“子卿公,是國之長者。”
“對於此事,可有什麼良策嗎?”
不著痕跡的低下頭,以食指指腹摩擦著下唇以下的細軟鬍鬚,劉勝目光望著田叔,思緒卻是悄然飛向了不知何處。
其實,田叔所說和劉勝所想,基本上是一件事。
只是由於身份、立場的不容,以及劉勝這個穿越眾所特有的長線視野,讓二人的表達方式、思維方式產生了些許詫異。
——在田叔看來,這件事,根本就是考舉的鍋!
是考舉這個只看成績,卻不查道德、不需要足夠地位的人舉薦的糟糕制度,導致了現在這個狀況發生。
這就好比在監獄尋找道德模範一樣:找不到不是運氣不好,而是真的挑錯了地方。
所以在田叔看來,這個問題的解決方式,其實就是科舉制度的進一步‘完善’。
比如文考透過計程車子,依舊需要如同察舉那樣,滿足一定程度的‘名聲’要求,才可以被任用為官吏。
要求可以降低,從周遭五郡改為所在當郡,甚至是周遭幾縣,但絕對不能沒有關於這方面的硬性要求。
其次,便是考舉透過計程車子,也依舊需要同察舉出身的官員一樣,需要有官員擔保。
這個的要求也可以降:千石以上即可,但也還是那句話——可以降低要求,但不能沒有要求。
對於田叔的這幾條建議,劉勝可以說是一條都聽不進去。
對科舉計程車子制定‘名聲’要求,顯然會讓一個原本不存在於這個時代的技能,提前數百年被文人士大夫階級掌握。
——養望。
說白了,就是刻意的去維護自己的名聲、形象,並以此作為升官發財的根本倚仗。
或許在後世人看來,這並不是壞事。
文人為了做官打造‘良紳’人設,愛惜自己的羽毛和名聲,對於百姓難道不是一件好事?
有了養望這個技能,地方難道不會更加安穩,豪強富戶對百姓豪取巧奪時,也總該要稍顧忌一下影響。
還真不是。
指望這群人‘顧忌影響’,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舉個非常簡單的例子。
你是生活在天子勝統治時期的高門子弟,你爹雖然沒有多麼尊貴的爵位或地位,但經過文景之治數十年的太平盛世,你們家也算是攢下了不菲家貲。
在家中子弟當中,你是相對優秀的那一個,於是你老爹花了大價錢找來了不少書籍,還給你不遠萬里去請了個先生,想讓你躋身於文人群體,以改變家族暴發戶的現狀。
一開始,你並沒有把這件事太放在心上——反正家裡有的是錢,你就算是混吃等死,家裡的錢也夠你子孫三代衣食無憂。
只是慢慢的,你的想法也開始出現一些改變了。
因為你發現鄉里的窮小子們,都不再像過去那樣圍著你轉,而是整日聚在一起搖頭晃腦的讀書了;
更氣人的是鄰居家的窮小子,居然因為參加了一個勞什子考舉,便被任命為縣衙的主簿,雖然只有二百石的職務,那也比作為土財主的你家要好太多。
曾經對這一家人嗤之以鼻,如今卻只能點頭哈腰的跟在人家屁股後頭,讓你爹也生出了些許不愉,於是,在某一天宴請過那主簿之後,下意識滴咕了一句:要是我家也能出個官兒,我哪犯得上這麼······
話說一半,老頭子意識到自己說錯了話,下意識撇了你一眼,便強笑著說:沒事兒,我沒說你書沒讀好,就是想讓家裡出個官面上的人嘛······
到這時,你終於有了些感悟:讀書,或許並不是為了學到什麼人生大道理,而僅僅是為了參加考舉,然後成為可以庇護家族——至少是讓老頭子挺直腰桿,不需要見到官袍就點頭哈腰的官兒。
你開始用功了,夜以繼日,紅袖添香,雖然比不得窮人家的孩子辛苦,但相較於你奢靡的青少年時期,也算是著實吃了些苦頭。
終於,你參加了考舉,成績雖然算不上太好,也終歸是踩著線勉強透過了。
只需要走完接下來的程式,你就可以成為一個二百石的官員,再用家裡的錢走動一番,便大機率能調動到自己的家鄉——至少也能調動到家鄉所在的郡。
可就是這麼時候,朝堂頒下了新的指令:就算是科舉透過了,也還是和察舉一樣,需要名聲和高官舉薦。
你懵了。
你們一家子商賈暴發戶,在鄉里能不被人戳嵴梁骨就算不錯了,哪還能有什麼好名聲?
單就是‘有錢的商人’這個罪名,就已經讓你們這一大家子人,和好名聲三個字永久性絕緣了。
至於官員保舉,那就更不要提了——不是商籍,且確實有真才實學的人,這些個郡國二千石封疆大吏們都是小心翼翼,能不保舉就儘量不保舉,怎麼可能有人想不開,去保舉一個商戶之子?
你明白過來這一點,闇然從長安回到了家鄉。
就這麼過了十幾二十年,老爺子終於扛不住巨大的壓力,倒下了。
你雖然沒能透過考舉做成官,但也起碼透過了文考,也去了一趟長安,和不知多少年輕俊傑交換了一件,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交情。
憑藉這份學識、眼界以及人脈,你將家族經營的越來越好,越來越富庶;
但有一點,是你無論如何都沒能改變的。
——即便家貲翻了數十翻,你也還是要和你父親一樣,跟在一個百石、二百石的芝麻小吏身後點頭哈腰。
這讓你很無奈,又很不爽。
終於,在被某一個百石小吏諷刺‘商賈賤戶’之後,自尊心受到極大衝擊的你,決定為家族的未來做些什麼。
科舉?
好,凡是你家中的子侄,都要從三歲開始伏於桉前,為將來參加科舉做準備。
名聲?
沒問題——逢年過節給鄉里鄉親送點米、布之類做做樣子,再蓄養一批打手,做一個溫文爾雅的良紳。
有人說你壞話?
打!
有人說你家不是東西?
殺!
比起好吃好喝伺候著那群狗眼看人低的農戶,你更傾向於一勞永逸——你要讓他們害怕你,不敢說你不好,不敢說你家丁點不是。
於是,你家的名聲變得越來越好,十里八鄉都在交口稱讚——如果不算你那千百如狼似虎的家丁,時刻在鄉間巡邏的話。
如此大的動靜,你當然不可能不走動官面上的關係——你讓自己的嫡長子,娶了郡守府某個小蝦米的侍妾,並藉此與其攀上了關係。
你看中的不是這層關係,而是透過這層關係,讓你和郡衙搭上了線。
只簡單的試探過後,你就讓整個郡衙淪陷。
每年數以千萬計的‘投獻’,郡守拿一成,千石以上平分一成半,千石以下平分一成半;
剩下五成,從郡衙到地方縣衙,人人有份,不拿都不行。
自此,你家成為了本郡名聲最好、關係最硬,最富庶也最有未來前景的豪強富戶。
百姓畏懼你,卻也敬畏你;
官員鄙視你,卻也親近你。
直到你華髮之年,你的子侄中終於出了一個成器的,透過了考舉的一系列流程,做了二百石的官員。
再經過你的一系列運作,你的麒麟兒步步高昇,一直做到了千石以上,甚至是兩千石級別。
然後,你開始等。
等到一個合適的良機,讓這個麒麟兒坐上你家鄉所在地的郡守之位,這個郡,就不再姓劉了······
“朕倒是認為,官員貪腐,並不全是考舉出身的官員才會有的。”
“自有漢以來,我漢家官場受賄成風,尤其經文、景兩代仁君在朝,更是愈演愈烈。”
“要想改變這樣的狀況,不單需要針對科舉做出改動。”
“——監察百官,是御史大夫的職責,但在過去這些年,御史大夫屬衙監察百官的職責,幾乎已經被完全摒棄了。”
“關於這一點,我想要讓諸公好好討論一下,拿個章程出來。”
“御史大夫,可以繼續做亞相。”
“但至少御史中丞,不可以再繼續做名義上監察百官,實際上卻只負責官員背景調查的‘採風御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