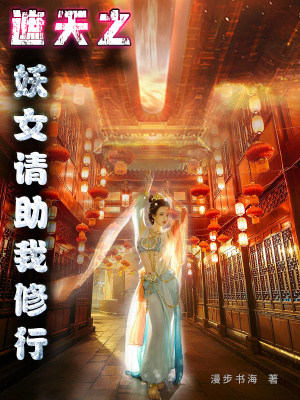第418章 天子冠禮
血狸奴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對於御史大夫(屬衙),劉勝寄予很高的期待和期望。
蓋因為在這個時代——在這個賄賂官員幾乎成為社會常態,整個社會都認為賄賂是正常的事,且應該存在的事的社會背景下,一個監察機構的存在,總是會讓人更安心些。
如今漢室的賄賂之風,究竟有多嚴重?
——郡縣地方官員入朝覲見,幾乎都是本能的要去打點宮裡宮外的關係,哪怕自己什麼錯都沒犯,此次入京也只是一次稀鬆平常的述職。
皇帝、太后派宮人外出辦事,但凡牽扯上和宮外的人溝通交流之類,那也是預設要得到那個宮外人的‘賞賜’的。
可以說,漢家上到朝堂之上的公卿百官、功侯貴戚,下到天子身邊的郎官寺人,乃至於這些官員的門房、下人——在這個時代,就好像沒有誰是不貪的、是不收受賄賂的。
想想先帝之時,丞相申屠嘉最為人所敬佩的一點是什麼?
清廉。
兩袖清風,鐵面無私。
明明只是每一個官員都應該做到的事,卻成為了申屠嘉名揚天下的‘獨特’素養,這個時代的行賄受賄之風有多濃烈,也就是可見一斑得了。
其實,當趙禹先前提到‘考舉出身的官員,在半年內就已經有六成免官下獄’的時候,劉勝本能的就想問上一句:那那些不是考舉出身的官員呢?
漢家的官員,有幾個能在當上官半年之後,仍舊保持‘處子之身’,仍舊保證自己沒有被糖衣炮彈所侵蝕?
當然有。
只是這樣的人,都和申屠嘉一樣——單憑著一個‘這個人做了官,居然不收受賄賂’的名聲,就成為了官員群體中的異類。
運氣好點,不受賄會成為這個官員的立身之本,成為這個官員受人敬仰的主要原因;
運氣差些,則會讓這個官員不被整個群體所接受,成為這個官員‘不合群’‘不懂事’的主要緣由。
所以,劉勝真正想要說的是:確實,第一次考舉出來的官員,至今已經有六成落馬,且絕大多數都是因為行賄受賄。
但這並不意味著考舉所選拔出來的,是一批漢家‘未曾有過’的貪婪之輩。
行賄之風,是整個漢家的社會風氣問題。
這些憑藉考舉出人頭地的年輕人,不過是在融入這個大背景、大環境的過程中,沒能學到其他前輩們的全部經驗。
說的再直白點,就是這些愣頭青只顧著撈,卻完全沒有類似‘藏著點握著點,吃相別太難看,別太落人口實’之類的認知。
再加上朝堂內外,本來就對這個新興群體抱有一定的戒備,剛好有把柄送上門,自然也就順手落井下石了。
行賄是重罪?
在後世或許是。
但至少在劉勝所身處的這個時代,行賄受賄,基本就類似於後世的官員不作為——可以批評,可以鄙視,但也屬於官場的常態,且遠遠還沒有到因此而治罪於彼、免彼官職的程度。
尤其是在太宗孝文皇帝年間的一件事之後,漢家的行賄受賄,就更是從藏著掖著進行,逐漸轉變為大庭廣眾之下也不用顧忌的事了。
眾所周知,太宗孝文皇帝,是太祖高皇帝劉邦的第四子。
漢十二年,太祖高皇帝劉邦駕崩,太子劉盈繼承大統,幾乎是在同一年,年僅七歲的代王劉恆離京就藩。
從漢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一直到呂太后駕崩的呂后十五年(公元前180年),代王劉恆都在自己的王都晉陽。
呂太后十五年,呂太后駕崩,諸侯大臣內外聯合共誅諸呂,迎立時年二十二歲的代王劉恆入繼大統,繼承漢家的宗廟、社稷。
既然是入繼大統,那劉恆自然也從晉陽帶了幾個肱骨心腹來長安。
其中,有後來被唱輓歌活活唱死的軹侯薄昭,太宗一朝的名臣宋昌,以及當時劉恆最拿得出手的武將:將軍張武。
以至於時至今日,都還有不少的人在說:太宗皇帝自晉陽入長安,身邊只帶了六個人;
而這六個人當中,除去母舅薄昭,太宗皇帝最信任的,便是宋昌和張武二人。
從太宗皇帝即位之後,迅速任命宋昌為衛將軍、張武為郎中令也不難看出:太宗皇帝對這二人的信任,已經到了足以將自己的人身安全託付給這二人的程度。
只是後來,太宗皇帝同這兩個肱骨心腹之間,也逐漸生出了些許隔閡。
——衛將軍宋昌,因為一些不可為外人道的原因,逐漸失去了太宗孝文皇帝的信任,幾乎是在太宗皇帝逐漸掌權的同一時間,以同樣的速度澹退於朝堂之外。
而張武,則是因為一次受賄的經歷,而被太宗皇帝徹底釘死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眾所周知:太宗皇帝自代地入繼大統之初,並沒有在第一時間掌握天子所應當掌握的權柄,朝內朝外的權力,都被陳平、周勃等老臣牢牢把控。
這也正是諸侯大臣共誅諸呂之後,選擇由代王劉恆入繼大統,而非齊王劉襄即皇帝位的根本原因——相較於兵多將廣,實力強大,就算拋棄整個長安朝堂,也能在第二天就組建起新一屆朝堂班子的齊王劉襄,代王劉恆,實在是太過於好控制了。
被封去晉陽,要肩負戍邊的職責不說,還要忍受代地地廣人稀、稅賦稀疏的糟糕財政狀況;
從小就老實,又遠離長安朝堂,乃至於中原太久,根本沒有任何掌控朝堂的可能性。
於是,陳平、周勃等老臣一致決定:為了我們自己的小命和小日子,就選代王劉恆來做這尊泥塑凋像吧!
代王劉恆,確實足夠老實。
至少在即天子位之前,劉恆老實的就好像一隻兔子。
但正所謂兔子急了也咬人——做了皇帝,劉恆自然不會還人畜無害,任由命運被掌握在他人手中。
即位的第一時間,劉恆任命將軍張武為郎中令,算是將自己的人身安全掌握在了自己手裡;
隨後,原本想要任命宋昌為衛尉,卻又擔心此舉會刺激到陳平、周勃等老臣的太宗孝文皇帝,便毫無遲疑的發明出了‘衛將軍’這一職務,並讓漢家初代衛將軍宋昌,成為了自己的皇宮衛隊統領。
再經過耐心的等待和佈局,太宗皇帝終於將本屬於自己——本屬於天子的權力,從死去的老丞相陳平,以及終於知道獄卒之貴的絳侯周勃手中拿了回來。
有過這樣的經歷,太宗孝文皇帝自然無比的珍惜‘大權在握’的日子,無比珍惜這讓自己費盡心機,才艱難拿回手中的權利。
於是,在自己徹底掌控朝堂之後,太宗皇帝開始防備自己身邊的近臣了。
先是宋昌被免職,衛將軍這一臨時職務也被罷設;
之後是薄昭在自己的靈位前自裁,讓天下人認清了太宗小文皇帝的決絕。
最後的張武,自也沒能逃脫這個命運。
張武是儒將。
就是那種即被文人士大夫尊稱為‘張公’,又深受行伍之人敬仰的、能溫聲和氣同人談論學術,也能披掛上陣衝殺敵陣的,溫潤如玉的儒將。
這樣一個人,曾讓太宗孝文皇帝無從下手。
一直到某一天,有人舉報張武受賄,才總算是讓太宗孝文皇帝揪住了張武的小辮子。
張武收受的賄賂很多,足有五百金。
至少對於當時,尚還處於重建階段的漢室而言,五百金,對於任何一個個體,都是一筆極為不菲的財富。
但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張武那五百金,其實也完全可以被粉飾為禮物——別人送給他的禮物、心意。
所有人都知道繼宋昌、薄昭之後,張武也要遭受太宗孝文皇帝的打擊;
所有人都知道張武受金,是太宗孝文皇帝難得的機會。
只是所有人都沒有想到:太宗孝文皇帝處理這件事的方式,居然會這般陰損······
按照常理,這件事的處理方式,不外乎以下兩種。
第一種,是在得知張武受賄之後一笑而過,隨後將張武私下召入宮,委婉的敲打一番,說一些類似‘別讓我難做’‘注意點影響’之類。
如此一來,張武大機率會引咎辭官,太宗皇帝也就不用再防備這個老熟人、老心腹。
第二種則是公事公辦,直接把這件事鬧大,指著張武的鼻子一通臭罵,然後以‘近臣犯法,罪加一等’懲治張武。
這樣一來,無論張武是被罰金還是下獄,都會同一時間被罷免官職,同時又完全沒有資格去抱怨。
但太宗孝文皇帝,選擇了第三種方式——一種非人的,非常人所能想到的方式。
——賜五百金,以愧其心。
在得知張武受賄五百金之後,太宗皇帝又反賜給了張武五百金,對外美其名曰:以愧其心;
與此同時,太宗皇帝也將張武叫到了身邊,說了一些讓人再也抬不起頭,從此徹底社會性死亡的話。
——張武啊~
——旁人是臣,你,可是朕的好大哥呀~
——你也知道朕來這長安,那是不知道有多少人等著看朕的笑話,你不幫朕也就算了,怎麼反而還跟著添亂呢?
——往後缺錢了就跟朕說~
——雖然朕連一個亭子都捨不得修、連一百金都捨不得花,但為了不讓你收受賄賂,我是願意給你五百金花花的~
——別為了錢,讓那些個外臣得了朕的口實,讓朕太難做啊~
——朕有多難,張武你是知道的啊~
···
就這麼一番陰陽怪氣下來,張武直接在漢室徹底社會性死亡,並自此失去了每一次三公九卿之位出缺時的競爭機會。
滿懷著羞愧和屈辱,張武決定用自己最擅長的方式恕罪,於是自請為邊將,鎮守蕭關。
最終求仁得仁,在守衛簫關的過程中戰死沙場,馬革裹屍,算是用自己的性命,洗刷了那‘貪婪受金之人’的汙名。
按常理來說,發生這樣的事,盛行於漢家的行賄、受賄之風本該得到抑制,起碼也是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哪怕是為了別成為下一個張武,官員們也應該開始注意自己的吃相,注意行賄、受賄所可能造成的影響。
但實際情況,卻是朝著另一個方向狂奔不止······
——什麼?
——張武受賄,太宗皇帝非但不懲罰他,還反賜他五百金?
——那豈不是說,我貪得越多,太宗皇帝也給我賜的越多?
——愧疚算什麼,名聲又值多少錢?
就這樣,張武受金一事傳著傳著,就傳出了‘你貪多少,皇帝就會再給你多少’的離奇版本。
雖然這個版本沒有被太多人所接受,但也潛移默化的讓天下人明白:對於收受賄賂,漢家的容忍度是非常高的,甚至高到了非但不用受懲罰,反倒還能得到皇帝養廉金的程度。
於是,漢家的賄賂之風,便在張武受金一事之後愈演愈烈。
如果說在那之前,人們行賄、受賄還知道藏著點、掖著些,在那之後,則已經是全然不避人了。
在那之前,行賄受賄還知道披個‘送禮’‘祝壽’之類的幌子,那之後卻完全沒有了。
——甚至就連把財物藏進袖裡,偷偷伸到對方袖口,以免被人看到這樣的掩飾,人們都不願意再做了······
“官風倡廉,並不單是考舉出身的官員所引發、所需要面對的事。”
“為了這件事,御史大夫的職能,就需要做出一些改變。”
···
“這些事,急不得,朕也不盼著三兩日之內,就讓我漢家的官員個個都成為故安貞武侯那樣廉潔的人。”
“但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這件事可以不急,但不能不做。”
“諸公都掛念著些,爭取儘快拿出個章程出來,看怎麼做,才能讓御史大夫屬衙發揮自己‘監察百官’的職能,抑制我漢家愈演愈烈的行賄受賄之風。”
···
“這件事,在夏天要有眉目。”
“至於開春時,朕的加冠大典······”
說到最後,劉勝才總算是圖窮匕見,從御榻上緩緩起身,在眾人身上掃視一週。
“諸公,可有什麼想說的嗎?”
“太后可是已經發話,要將冠禮定在春二月了。”
“這大典怎麼辦,在哪辦,又需要召哪些宗親諸侯入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