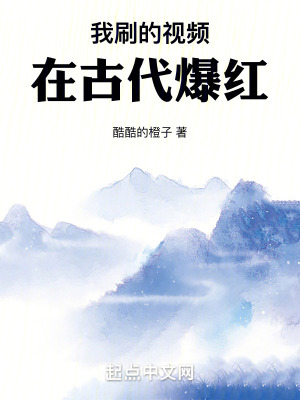懸姝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琴身有裂痕,琴絃算不得上乘。
除了料子好些以外,他著實瞧不出這琴哪裡入了她的眼,讓她非要得到!
李鶴珣望著沈觀衣許久,見她頭也不曾回一下,鬱氣積攢,想起自賞花宴再次見到她時,便沒有一次是順心的。
方才歸言匆匆回來,他聽聞之後丟下眾人與他過來,她不識好歹便罷,還冷著一張臉,給誰看呢!
諾大的上京城,風雨欲來,百姓步伐匆匆,周遭的人所剩無幾,雜耍高臺上,沈觀衣對襟青紗很是單薄,隨風而動,一頭青絲略顯凌亂,她背影堅毅執拗,彷彿任誰來勸說都無用。
在這種事上一身犟骨,任性妄為。
李鶴珣壓著心底翻騰的沉鬱,轉身便走,管她死活!
但,探春突然道:“那把琴,是小姐孃親生前之物。”
所以才那般珍貴。
所有的情緒匯聚成沈觀衣驟然看來的那一眼,平靜無波,好似今日說變就變的天色,上一瞬還明媚如春,此時卻已然褪去所有斑斕的光,悄無聲息。
李鶴珣步子一頓,嘴角抿直,斥責之言在他喉口滾了一圈,又沉沉嚥下。
孃親生前之物……
他驟然想起長公主先前的勸慰:“她是個命苦的,自小便一個人在那莊子上,孃親走的又早,沒人教導,性子難免頑劣,你是男子,多擔待些。”
罷了。
他回身,趨步行至沈觀衣一步之遙的位置,在她回頭看來之時,沉穩有力的聲音赫然響起,“班主,這琴可賣否?”
一刻鐘之前,如出一轍的話。
班主雖錯愕,回的卻一般無二,只是相較於之前,此時更為恭敬幾分,“這位大人,規矩不能破。”
沈觀衣歪頭看去,李鶴珣從容冷靜,身量極高,挺拔如竹的站在那兒,清如朗月。
她忽然想起前世這把鳳樓月,似乎是歸言派人送去沈府的。
只是不知這把琴,李鶴珣是從班主這裡尋來的,還是從別的地方。
若是從班主這兒,他可是站那兒不動,將性命交到別人手上?
但轉眼一想,沈觀衣又覺著不可能,以李鶴珣的性子,他定然不會任由旁人拿捏。
班主的規矩?
那個聲名赫赫,如山中玉石般的男人,在他心中,他的規矩,才是規矩。
“知道了。”
沈觀衣被聲音拉回神來,身旁的李鶴珣面色如霜,執筆而起,濃墨自筆尖浸入。
沈觀衣心下震驚,不曾多想,一把按住他的手腕,筆尖停在空中,水墨入紙,氤氳開一朵黑色墨花。
她揚聲錯愕,“你要替我拿彩頭?”
她自是不會認為李鶴珣要與她爭搶,但也不曾想過他會如此好說話。
他若想要得到一樣東西,有千百種法子,什麼時候一個小小的班主都能指使他了?
李鶴珣望著手腕上蔥白修長的手指,沉吟道:“不然讓你一個女子賭上性命?”
他語調清平,不曾看沈觀衣一眼,見她不放手,便就著她的手腕,兀自挪動,筆觸在紙上龍飛鳳舞的寫下三個大字,紙張錯落間,李鶴珣三個字隱隱與底下的沈觀衣重合。
他掃了一眼沈觀衣鬆開的手,“班主,可否不用繩子?”
班主神色猶豫,“這……”
李鶴珣轉身踱步至柱子前,負手而立,溫言道:“本官倒是不怕,就怕班主一個失手,殺害朝廷命官之罪,你可擔當的起?”
“大人,咱們可是簽了生死狀的!”
“本官知曉,所以才與班主商議可否不要繩子,若班主失手,本官也能保住一條命。”
他神色猶豫間,李鶴珣繼續道:“或是說,班主其實是賊人,特意等著本官自投羅網,不將本官綁了,怕殺不死本官?”
!
這帽子扣下來,班主冷汗連連的便要跪下。
李鶴珣指節敲打著掌心,慢條斯理的道:“本官只是將或許會發生之事說與班主聽,班主可以考慮一二。”
突然,震徹山河的雷聲滾滾而來,班主捏著黑巾的手一滯,心底掙扎半晌,他回頭望向跟著他多年的幾人,思緒來回翻滾,隨著雨滴滴答答的落下,他洩氣長嘆一聲。
這位大人說的不錯,但他卻考慮的更多。心中有了阻礙與畏懼,這耍了十多年的飛刀便沉如泰山,他無法心無旁騖,這二人又對這把琴勢在必得,如此,他只好退一步。
“既大人與姑娘這般喜愛這把琴,我今日便壞一把規矩,贈與你們了。”
沈觀衣怔住,抿著的唇微張,眼底的笑意逐漸蔓延開來,明媚的將陰雨撥開,如同初見微陽,“真的?”
她歡喜的從旁人手裡接過那把琴,指尖撫過琴身,愛不釋手。
李鶴珣抿唇瞧著,她所有的歡欣雀躍彷彿凝結成一團炙熱的火焰,深深烙進他眼中。
還是真是一會一個模樣。
短短几面,她便如那萬花筒一般,變了好幾種顏色。
女子,都是如此?
探春見沈觀衣如願,總算放下擔憂,上前提醒道:“小姐,大人,雨勢越來越大了,還是先找個地方避避雨吧。”
李鶴珣回過神,對於班主方才的決定並不算驚訝,轉頭對歸言使了個眼色,便率先快步離開,沈觀衣瞧見後抱著琴緊跟在後。
歸言行至班主跟前,他們正收拾著東西欲要離開,眼前突然多了一疊銀票,掃一眼便知曉不少於幾千兩。
班主連連擺手,“使不得使不得,便是買琴也用不著這麼多。”
歸言將銀票塞進班主懷裡,笑道:“不是買琴的銀子。”
“那是……”
“班主壞了這麼多年的規矩,這是您應得的補償。拿著這些錢開間藝坊,應當好過你們天南地北為家,都是公子的心意,班主接下便是。”
雨珠滾落,似乎掉進了眼裡,班主抬手匆忙拭去,彎腰接過,不顧歸言的阻攔,非要對著早已不見人影的街頭,跪地磕頭才肯作罷。
歸言辦好了事,瞧了一眼煙霧朦朧的天,雙手做傘狀,鑽入了雨中。
‘譁——’
雨勢太大,沈觀衣只好與李鶴珣躲在簷下,雨水順著房簷落下,築起水簾,霧色塵煙看不見盡頭,她擔心琴被淋壞了,只好又往裡面退了一些。
探春與歸言也不知何時才能尋到傘回來。
沈觀衣百無聊賴的撥動琴絃,清泠動聽,卻不是那個人彈出來的聲音。
她失望的抬眸看向李鶴珣,見他離她距離甚遠,忍不住湊近了一些,問道:“你方才為何幫我?”
前世,她不敢問,所以她一直都好奇,在她不曾引誘的時候,李鶴尋為何幫她?
雨聲淅瀝,夾雜著小姑娘清脆的聲音,李鶴珣望著對面的雲煙樓,不答反問,“你為何將夏嬤嬤趕走?”
提起那個老婆子,沈觀衣便有些氣,“你若不讓她來,我怎會有機會將她趕走?”
強詞奪理!
李家門生眾多,李鶴珣又是這一輩中的佼佼者,平日裡來問學的人多如過江之鯽,不知不覺間便拿出了教導苛責的語氣。
“你是覺著,我讓夏嬤嬤來教導你規矩,還是我的錯。”
“不然呢?”沈觀衣不明白他憑什麼理直氣壯。
李鶴珣猛地轉頭看向她,見她滿眼疑惑不似作偽,方才以為的挑釁之言被他拋擲腦後,他委婉提醒,“夏嬤嬤是宮中的老人,秀女入宮後的規矩幾乎都是她一手操持,能請她教導一二,是你的福氣。”
沈觀衣冷嗤,“這福氣,你還是給別人吧,她若再敢來,我便叫她知道厲害。”
李鶴珣面色如霜,不想再與她逞口舌之快。
沈觀衣臉色也好不到哪裡去。
不理便不理,誰稀罕。
她才不會因為李鶴珣年紀小就不與他一般計較!分明就是他的錯。
沉默無聲,過了許久。
李鶴珣忍不住蹙眉,她為何突然不說話了?
餘光瞥見她冷沉的面色,腦中突兀的閃過歸言先前的告誡。
所以,她或許不是故意落臉,而是不喜有人教她規矩?
雨幕沉沉中,少女衣著單薄,唇瓣略微泛白,長髮因先前淋了雨,髮梢還略微有些溼潤,瞧上去倒有幾分可憐。
李鶴珣面色稍緩,這才發覺若是以身處之,他應當也會因此生怒。
或許,是他操之過急了。
不多時,探春與歸言紛紛小跑著回來,沈觀衣接過探春手裡的油紙傘,‘噌’的一下開啟,雨水四散,浸入李鶴珣的衣衫,轉瞬便只剩一抹水漬。
“哼。”
她舉著傘霸道的從李鶴珣身邊走過,踏入雨裡,傘沿恨不得戳進他的腦子裡,若不是李鶴珣及時往後躲開,臉上免不得要留下痕跡。
探春佝僂著背,亦步亦趨的跟著自家小姐身後。
歸言大氣不敢出一下,從懷裡掏出絹帕,替李鶴珣擦去脖頸上的雨水。
李鶴珣被氣的雙眼發暈,接過歸言的傘緊緊攥住,額上青筋跳動,聲音艱難從喉口擠出,“沈觀衣!”
他覺著方才替她說話的自己,簡直像被髒東西魘住一般,不可理喻!
驕縱任性,膽大妄為,無法無天,過河拆橋!
琴到她手上還不到半個時辰,她便又變了一副模樣!她莫不是以為只有她有脾性,別人都是軟柿子,任由她拿捏不成!
“歸言!”
李鶴珣二十年來,從未如此生氣過。
“屬下在。”
“去將琴拿回來!”他看她著不著急,還敢不敢如此耍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