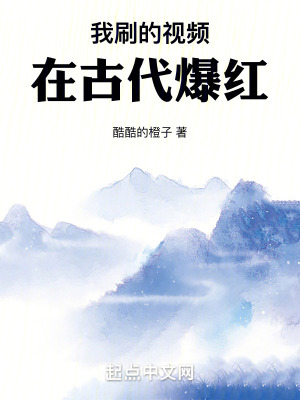懸姝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街上煙雨朦朧,雲煙樓廂房中卻暖意怏然,身披薄紗,窈窕曼妙的女子虛虛的伏在男子懷裡,食指挽著他略微卷曲的長髮,嬌聲嬌氣的道:“公子讓奴家進來服侍,怎的半天都只一個人喝酒啊。”
寧長慍一手拿著酒壺一手捏著酒杯,衣襟散亂,遠遠看去,他似乎才像是被調戲的那一個。
“我讓你進來服侍,是讓你談個曲兒聽,你以為呢?”
女子笑容一滯,嬌嗔的拍在他胸膛上,“公子這是打趣奴家呢,哪家公子來雲煙樓只聽曲兒啊。”
寧長慍掀開眼皮望著窗外,百無聊賴的答道:“不聽曲兒還能作甚?”
他平日裡無事,便在花樓聽曲兒飲酒度日,好些時候沒回京了,眼下竟覺得上京最有名的雲煙樓,也大不如前。
“還能……”她微微起身,朱唇靠近寧長慍耳邊,小聲低語幾句。
溫熱的呼吸從耳畔掃過,可這等引誘的戲碼,常年混跡在青樓中的人怎會不知。
寧長慍仰頭飲下杯中清酒,並不作答,甚至有些不耐。
突然,闌珊下的煙雨之中闖入一個身著青衣長裙的小姑娘,油紙傘上畫著紫蓮,傘沿幾乎遮住了她的容色,而在她三步之後,正亦步亦趨的跟著一個同樣著青衣的男子。
一高一矮,僅憑二人身姿,便覺著容貌也定當不俗,甚為般配。
前頭的小姑娘似乎鬧了脾氣,步伐越走越快。
可任由她多快,跟在她身後的男子都不動如山的始終保持著三步之遙,不遠不近,如閒庭信步,不驕不躁。
真有意思,想來定是哪家小兩口鬧了彆扭,出門時應當還恩愛有加,否則為何連衣衫顏色都穿的一樣。
寧長慍嘴角上揚,看的略有滋味。
突然,小姑娘猛地回頭,紙傘揚起,露出那雙含怒的眸子,哪怕煙雨朦朧,依舊明媚驚豔。
寧長慍笑容微滯,隨意握在手中的杯子猛地被他攥緊。
緊接著,跟在小姑娘身後的男子似是察覺到他的視線,赫然抬頭,溫潤清泠到極致的眉眼,上京只有一位。
李鶴珣對上他的目光錯愕一瞬,轉而頷首離開。
此時伏在他懷裡的女子不知何時已然將薄紗褪下,但寧長慍未看一眼。
李鶴尋……
他為何會跟在沈觀衣身後?
“公子……”
女子嬌媚嚶嚀,寧長慍面色陰沉得可怕,眸底錯綜複雜的情緒不停翻湧。
他猛地推開身上的女子,衣袍翻飛,帶起暗香陣陣,他大力推開緊閉的房門,腳步未停的朝樓下走去。
阿讓怔愣,“世子,世子你去哪兒啊?”
長靴被雨水沖刷,暗色更沉,寧長慍站在雲煙樓牌匾之下,望著空無一人的街道,嘴唇緊抿,眼底的火光若隱若現。
阿讓好不容易追上來,還沒等喘口氣,便聽寧長慍沉色低問:“李鶴珣今日和沈觀衣在一處?”
阿讓心中一緊,對上寧長慍怒氣蓬勃的神色,“世子……”
“他們何時走的這般近的?為何不說!”
潮溼的氣息蔓延開來,阿讓揉了揉鼻子,這下不敢再推辭,將那日晚上沈觀衣的話一五一十的告訴了寧長慍。
“姑娘覺著李大人很好,並未有退婚的想法,此時沈府應當在為姑娘準備嫁妝。”
“姑娘還說……”
寧長慍猛地回頭,眼尾被憤怒染紅,“她還說什麼?”
“姑娘還說,是世子先不要她的,所以她嫁給別人,也是理所應當的事。”
“好個理所應當!”寧長慍胸中積攢著一團陰雲,咽不下去,又發洩不出。
恍然間,他又想起方才雨中一幕,他是瘋了才覺著那二人般配!
一個不近女色整日以書為伴,一個小心思多如牛毛驕縱無理,恨不得全天下的人都捧著她才好。
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兩人,就因為那勞什子賜婚!
是他這些年太縱著沈觀衣,才讓她忘了,她是被誰從陰溝里拉出來的!
一根需要攀附才能存活的藤蔓,就該做好她藤蔓的本分,而不是被人放到一顆更大的樹上,便迫不及待的粘上去,頭也不回。
寧長慍如同被踩到痛腳的貓兒,慵懶褪去,利爪如鋒,他轉身走回雲煙樓,聲音夾著冰渣,“回來,將她的事一字不落的說給本世子聽!”
阿讓大氣不敢喘一下,“是。”
-
今日出府,沈觀衣並未坐馬車。
以她的腳程走不出很遠,所以此番回府,不過半個時辰便到了。
沈觀衣知曉李鶴珣跟在身後,她腳步不停,正欲進府之時,歸言硬著頭皮走上來,“二小姐,且慢。”
走了一路,他遲遲沒有行事便是想著公子應當是在氣頭上,待他消氣這事也就不了了之。
可如今二小姐都要進府了,他家公子呢?
沉默的站在府外的榕樹下,衣襬潮溼,執傘而立,看那樣子並不曾打消念頭。
歸言從前就聽府中小廝抱怨過,說是主子與姑娘置氣,最終受難的都是他們這些下人。
當初他不以為意,覺著公子與旁人不同,姑娘脫光了站他跟前都不能讓他多看一眼,更別說與人姑娘置氣了。
果然,話還是說早了。
世間主子都一樣,一樣!
在沈觀衣遙遙看來的眼神中,歸言硬著頭皮伸出手道:“麻煩姑娘抱了一路的琴,接下來就給我吧,公子還等著呢。”
沈觀衣眨眨眼,似是在消化他話中的意思。
一瞬之後,她猛地回頭看向樹下清泠俊逸,仿若隨時要羽化登仙的男子。
他什麼意思?
李鶴珣不躲不避的對上沈觀衣含怒的雙眸,神色淡然無波,對她的怒不以為意。
如此便惱了?
懷裡的琴被沈觀衣塞進探春懷裡,“看好,若被人奪了去,我拿你是問!”
“是!”探春站在沈府簷下,乾脆扔了傘,雙手緊緊抱著琴,警惕的瞧著歸言。
沈觀衣行至李鶴珣身旁,抬頭看他,不明白他這是玩的哪一齣。
她知曉李鶴珣善琴,前世也瞧過他亭中撫琴,但以他的眼界,萬萬看不上鳳樓月。
所以為何要與她搶?
李鶴珣壓下眼尾的嘲弄,“搶?若我記得不錯,這琴應當是我的彩頭。”
“說起來,若不是二小姐方才抱著琴,怎會手中無力連傘都拿不穩。”
雨聲颯颯,重重砸在油紙傘上,沈觀衣這才想明白,他在計較方才的事。
小氣,脾性大,斤斤計較,沒有一點容人之度。
除了這身皮囊,沒有一點相同。
從前沈觀衣覺著李鶴珣活得不太像個人,除了在她身邊,平日裡宛如一灘死水,就連殺人見血都無法激起他半點波瀾。
她畏懼他,卻也信仰他。
眼下這個倒是有了人氣兒,但是非不分。
他找嬤嬤來膈應她的事,都不曾與他計較,如今他倒還計較起來了。
沈觀衣望向他,他的眼睛生的很好看,瞳仁黝黑,鳳眸狹長,長睫濃密微微遮住半個眼眸,清明堅毅。
不似前世的他,眼裡帶著化不開的濃墨,但每每看向她時,卻又猶如烏沉天幕中突然出現的月光,點綴成世間唯一的亮。
心中翻騰的怒火突然消散下去。
他與寧長慍一樣,因為她,最終也沒落個什麼好。
一把琴罷了,前世她彈的還不夠嗎?
李鶴珣若想要,給他便是。
“李大人說的不錯,那琴本該是你的,讓歸言抱回去吧。”
李鶴珣怔住,似是沒想到沈觀衣那般在意的東西,輕易便給了他。
不吵不鬧,安靜的彷彿一件無關緊要的小事。
李鶴珣凝視傘下的姑娘,她垂目不語,所有悲鬱彷彿化為實質,砸在他心上。
方才他分明親眼瞧見沈觀衣有多在意這把琴,只是因她頑劣了些,想以此懲戒,沒曾想過她真會讓給他。
李鶴珣心下愁然,如同從前讀書般遇到難題,不知該如何化解。
見她要走,他沉吟半晌,還是心軟道:“琴你拿回去吧。”
沈觀衣步伐一頓,神情怔愣。
那是孃親唯一的琴。
少時她因噩夢睡不好,月光皎潔,孃親每夜都會起身坐在窗邊撫琴,琴聲悠揚,總能替她趕走夢中的魑魅魍魎。
可後來,唐氏帶著人不顧她的哭喊將她抱走,逼著孃親將琴砸了,說是擾人清夢。
琴絃盡斷,滿身是痕。
此後,沒有月下琴音,她便再也不敢做噩夢了。
那把琴,她可以給李鶴珣,卻不能容忍他推搡來去!
沈觀衣冷著臉回頭,正要罵出聲來,卻突然對上他澄澈清明的眸子。
那些話好像突然如鯁在喉,罵不出來了。眼前這個李鶴珣不會事事以她為先,什麼都讓著她,他也不知曉這把琴對她的意義。
他明朗如月,是燕國的未來,是李家的驕傲,更是有望進內閣,成為青史留名的賢臣般的存在。
她先前所以為的相敬如賓,或許起始便是她的一廂情願。
這個人,莫名讓她覺著,像一尊塵緣未了的佛,他本該娶一個身世地位卓絕,性情賢惠端莊的妻子,然後夫妻和睦,子孫滿堂,走上他本該走的那條路。
他應當也是這般想的,所以才會讓嬤嬤來教她規矩,所以才會計較她的失禮,斥責她的性情。
沈觀衣不喜歡憑空臆想,所以她要問個明白:“李鶴珣,若沒有陛下的這道旨意,你會上沈府提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