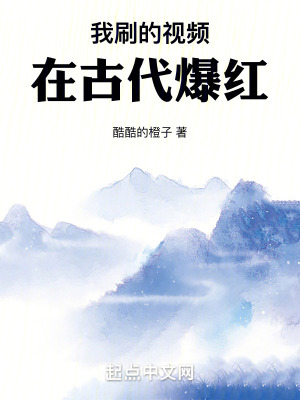懸姝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沈觀衣不動聲色地瞧著沈觀月,那一瞬,她眼底迸發出的激動如有實質。
她在高興什麼?
沈觀衣漫不經心地將剪子抵在沈觀月的喉口處,沈觀月頓時雙目圓瞪,脫口而出的話哽在喉口,嗆得她咳嗽個不停。
門外,唐氏擔憂的聲音再度傳來,“月兒?你怎麼了?”
沈觀月不敢回答,若說先前她還篤定沈觀衣便是再不可一世也不敢真地動手,可眼下識時務者為俊傑,她要做俊傑。
“二妹妹,我不會讓娘進來的,你別衝動。”
說罷,沈觀月伸出兩根手指,想要將橫在脖頸前的剪子推開。
沈觀衣歪頭瞧她,嘴角揚起,“讓她進來。”
門外唐氏著急吩咐的聲音透過縫隙傳來,沈觀月指腹剛剛碰到剪子,聞言猛地看向沈觀衣。
“噓——”
纖細柔白的手指虛虛地抵在沈觀月唇前,她過於緊張,嚥了口唾沫,額角的薄汗凝結成珠,自腮邊滾落。
沈觀衣瞧了一眼,下意識抬手去接,晶瑩的汗珠落在指腹上,她頗為嫌棄地嘖了一聲,隨手從沈觀月的下頜擦過。
嫣紅的指尖相互揉搓著,沈觀衣平靜從容道:“別聲張,不然殺了你哦。”
前世她從未自己動手殺過人,但踩著屍山火海上位之時,血腥氣兒也聞了不少。
如今她不過是學著旁人,在動手前威脅一二罷了。
拿來唬一唬沈觀月,總是綽綽有餘的。
沈觀月忙不迭地點頭,聲音都顫得變了調,“娘,我沒事!”
門外驟然安靜了一瞬,片刻後,唐氏與冬暖自門外進來,或許是關心則亂,唐氏並未注意到站在沈觀月身後的少女,只一個勁地詢問方才她為何不應聲。
倒是冬暖,在察覺到沈觀衣的存在後,厲聲質問,“二小姐為何會在這兒?”
唐氏愣了一瞬,這才注意到沈觀月始終僵著身子不發一語,臉色慘白,而她胸前的衣衫早已紅成一團。
她頓時大驚失色,咬牙切齒地看向沈觀衣,“你對月兒做了什麼?”
沈觀衣沒有理會她們二人的話,因嫌麻煩,索性今日便說個明白,不容置疑地道:“我不喜歡有人在我面前大呼小叫。”
“不喜歡別人隨意進出我的屋子。”
“更不喜歡有人在背後嚼舌根、使絆子。”
唐氏險些覺著自己的耳朵出了問題,怒火上頭,她今日便要教訓這個不知死活的丫頭片子。
她一把拉開沈觀月,手臂高抬,作勢要給沈觀衣一巴掌,可巴掌還未揮下,掌心停在空中,與沈觀月同樣的位置便多了一個血洞。
沈觀衣下手算不得狠,她沒想要這二人的命。
只是這傷口看著駭人,唐氏遲遲迴不過神來,身子一軟,倒在地上,嚇壞了冬暖與沈觀月。
但沈觀月眼下身上也有傷,她捂著傷口,面目猙獰,瞧著沈觀衣的眼神陣陣發狠,“我娘要是有什麼事,我一定要你不得好死!”
沈觀衣眼睫輕閃,總覺著這話有些耳熟。
零散的記憶忽然從腦中清晰,她想起那年冬日,大雪千里,撒鹽飛絮,厚重的雪地裡,長靴一踩便是一個印兒。
屋簷瓦房上頭白茫茫一片,孃親聽從她們的吩咐洗百件衣裳,才能給她們娘倆飯吃。
可天太冷了,從井裡打上來的水不到片刻便結了一層冰。
那雙撫琴的手就是在那個冬日佈滿了紅瘡,再未好過。
直到日落,衣裳還剩大半不止,孃親被下人們拖進柴房,黑漆漆的房中連只蠟燭都不曾有,須臾,房門緊閉,房中傳出孃親痛苦的哀嚎。
她撲到門外瘋狂地磕頭求饒,一起一落,整張臉幾乎都埋進了雪裡,漸漸的,雪中覆了一層血絲,她冷得發顫,但孃親的哀嚎聲卻並未停止。
絕望之際,她看見迴廊盡頭幾個下人提著燈火,簇擁著還未滿十歲的沈觀月走來。
她的姐姐,穿著乾淨暖和的大氅,毛茸茸的衣襟幾乎裹住了沈觀月半張小臉,像一隻乾淨漂亮的兔子,她紅著眼跌跌撞撞地衝上去,卻被冬暖攔在沈觀月的三步之外。
她一邊掙扎,一邊發狠地道:“我孃親要是有什麼事,我一定要你們不得好死!”
迴廊上暖意盎然,燈火通明,沈觀月嘲弄的看著她,和看池子裡撲騰來去的魚兒沒有區別。
那時沈觀月說了什麼來著。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能做到什麼地步。”
沈觀衣如今將這句話原封不動地還給了她,但沈觀月似乎早已忘了自己說過什麼。
鮮血順著尖端墜入地面,濺出一滴靡麗灼人的血花,沈觀衣握著剪子行至冬暖身邊,“我方才說的話,可記住了?”
冬暖面無表情,死死地按住袖籠中發顫的手。
她活了四十多年,後宅的什麼陰私手段沒有見過,手上沾染的血也算不得少,可方才二小姐看她的眼神卻讓她心裡發怵。
她處死過不少下人,正是因為如此,才分外明白那種眼神,不是一個十六歲的小姑娘能有的。
若是當真將她惹惱了,或許……
冬暖連忙垂頭,“奴婢與夫人都記住了。”
沈觀衣瞧了一眼已然暈過去的唐氏,應了一聲,抬手將剪子對準了冬暖。
在冬暖面不改色的神情中,冰涼的鋒刃貼在她的衣袍上,來回磨蹭,直至剪子的色澤恢復如初,沈觀衣才收回手轉身離開。
冬暖頓時鬆懈下來,大口地喘著氣,背心發涼。
回過神來後,冬暖便馬不停蹄地安排著,“快,請大夫,還有老爺,快去將老爺請回來!就說夫人和小姐出事了……”
“冬暖姑姑,別告訴爹爹……”
冬暖怔住,不敢置信地看向沈觀月,“為何?難不成咱們就任由二小姐欺負嗎?”
沈觀月自然也恨,但她怕啊,怕被沈觀衣知曉她們告狀。
如今沈觀衣身上有婚約,除非神不知鬼不覺的想個法子除掉她,或是解了她身上的婚約,否則沈觀衣不死,她一定會報復回來的!
冬暖儼然也想到了這一點,愁得擰眉,“那怎麼辦……”
-
天色漸晚,沈觀衣回屋時,探春早就將屋子收拾好了,被褥重新燻了香,首飾也都一一用帕子擦過。
暗香浮沉,沈觀衣褪去衣衫,赤足踏入浴桶中,整個人沒入雲霧氤氳的水中後,雙手自水中瀝出,搭在桶邊,下巴慢悠悠地抵在手臂上,闔眼養神。
“小姐,水溫可合適?”
沈觀衣輕輕應了一聲。
探春趨步行至屏風後,一眼便瞧見了沈觀衣搭在浴桶邊上的白皙手背紅腫帶血,指印劃過的地方皮肉翻滾,煞是扎眼。
她臉色一變,“小姐,您的手。”
“嗯?”沈觀衣嚶嚀一聲,緩慢地掀起眼皮,下巴不曾從手臂上挪開,她歪著頭瞧了一眼近在咫尺的手背,“哦,你說這個呀。”
她想起沈觀月與唐氏的模樣,心情極好地笑道:“沈觀月那丫頭掐的。”
探春:……
“您還笑!”她沒好氣從櫃中翻找出一瓶藥膏,心疼的蹲在浴桶邊,小心翼翼地執起沈觀衣的手,對著傷口吹了吹,嘟囔著,“自您回府後便沒有一日是安生的,這一府的豺狼虎豹,奴婢都怕哪一日您被她們吃的骨頭都不剩。”
沈觀衣抿著唇,目光從探春身上慢慢挪到了自己的手背上,盯了半晌,原先不怎麼覺著痛的地兒,此時竟有了些疼痛的感覺。
藥膏白膩如泥,抹在傷口上清清涼涼的,沈觀衣疼得‘嘶’了一聲。
探春立馬心疼地道:“不疼不疼,奴婢輕些。”
“嗯。”沈觀衣委屈地巴巴地瞧著,“是不是這藥不太好啊,我為什麼這麼痛。”
“這是世子當初送來的藥,可好用了,從前您嗑著碰著了,都是擦的這藥膏,不出兩日便好了。”
沈觀衣不太記得了,半信半疑地道:“當真?”
“嗯!”探春為沈觀衣仔細塗好藥膏後,起身去櫃中將東西放好,“不過這兩日傷口不能沾水,小姐需得注意些。”
探春繞過屏風走回來,見沈觀衣抬起那隻受傷的手,杏眸忽閃,眼巴巴地望著她。
探春:?
桶中冒著氤氳的熱氣,沈觀衣貼在邊沿,長髮落入水中,不著寸縷,露在外邊的肌膚溼漉漉的。
從桶中伸出來的藕臂白得晃人,手指微垂,水珠順著嫣紅的指尖不住地往下掉落,半晌後,她扁著嘴,慢悠悠地吐出幾個字,“再吹吹,舒服。”
與此同時,阿讓跌跌撞撞地回到侯府。
聽下人稟報,世子正與侯爺用膳呢,他猶豫一二,仍舊咬咬牙去到了正堂。
寧長慍聽到稟報後,不過片刻便走了出來。
阿讓將今日在沈府的所見所聞一字不落地告訴了寧長慍,末了還替沈觀衣抱不平,“那沈府還真是個狼窩,姑娘回去才幾日,便被她們逼成了這樣。”
“不是說她用剪子將人捅傷了?”
阿讓理直氣壯的點頭,寧長慍慢悠悠的道:“那你氣什麼,受傷的又不是她。”
“世子……”阿讓動了動唇,“姑娘平日雖嬌氣了些,但也不是這等衝動的人,她定是被逼急了才會如此,您可不能不管啊。”
寧長慍:“我什麼時候說不管了?”
“你附耳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