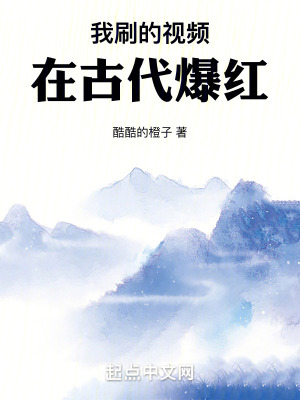懸姝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天幕烏沉,月掛樹梢,沈府中突然傳出陣陣哀嚎。
唐氏只著了一件中衣,伏在沈書戎懷中啜泣,雙眼紅腫,我見猶憐。
沈書戎坐在榻邊,壓下眉宇之間的不耐,哄了半晌,最終還是忍不住道:“你是說月兒和你身上的傷都是沈觀衣拿剪子戳的?”
“為何,她瘋了不成?”簡直是天方夜譚。
唐氏拭去眼角的淚,自然是挑對自己有利的說。
冬暖與月兒都勸她忍下,利弊說得頭頭是道,可那人是柳商的女兒,她無論如何都不能嚥下這口氣!
她不信老爺不會替她做主。
當年老爺那般寵愛柳商,最終不也任由她磋磨,那對母女早就在老爺這兒失了寵愛,眼下她與月兒差點死在沈觀衣手上,老爺一定會替她做主的!
唐氏堅信自己在沈書戎心中的夫妻之情,但沈書戎依然有疑慮。
沈觀衣圖什麼?
難不成真是攀附上李家,便目中無人到如此地步?
但不對。
沈書戎蹙眉道:“她是囂張跋扈了些,可她一個小姑娘,哪來的膽子對主母與嫡姐出手,更何況她不日便要嫁去李家,此時將人得罪了於她而言有什麼好處?那般的大家族,沒有孃家傍身,她能落個什麼好?”
他的話句句在理,就連唐氏在他的道理中也辯駁不出個一二三來。
可事實如此,唐氏咬碎了一口銀牙,“她就是個瘋子,怎能以常人常理的眼光看待。”
若是先前沒有正堂那一遭,沈書戎此時定然覺著是唐氏心思惡毒,理由拙劣。
可回想起之前沈觀衣的種種,煩躁與怒火交織,沈書戎也想借此給那逆女一個下馬威,於是怒喝道:“沒教養的東西!當初就該把她送去見商兒,省的如今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
唐氏心中一喜,柔弱地伏在他肩頭,眼底漫著一抹甜絲兒。
“來人啊!”
窗欞人影攢動,下人握著火把奔向來去,管家在門外焦急道:“老爺,夫人,大事不好了!”
-
“你是說,沈府昨夜鬧了鼠患?”
歸言頷首,將打聽來的訊息講得有聲有色,罷了還左右瞧瞧,小聲道:“據說沈夫人與沈小姐都被那老鼠咬了,還如出一轍的咬在肩膀上,公子你說,這老鼠莫不是成了精?但為什麼專挑肩膀下口呢?”
他低頭拍了拍自己精壯的肩頭,疑惑道:“也沒幾兩肉啊。”
桌案沉香浮動,筆墨紙硯規整有序,李鶴珣握筆的手指一頓,剛勁有力的字跡上立即氤氳開一團墨漬,方才寫好的冊子多了黑點,便不能用了。
他眉頭輕擰,索性放下手中筆,問道:“沈府可還有人受傷?”
“沒有。”
“去查查怎麼回事。”
半個時辰後,歸言帶著訊息匆匆回來,剛踏入屋內,便發現公子跟前的事務堆積如山,比他走時好像更多了。
微風徐來,他身後的窗欞半掩,隱約能瞧見窗外的山水竹林,明淨悠遠,仿若高人隱居之所。
歸言步履漸緩,自踏入屋內時便已然行走無聲。
廣明院向來禁止喧鬧,院中的一花一草皆是夫人按照公子的喜好佈置的,靜雅二字被夫人使得登峰造極,上京各家內院兒,他敢篤定沒有一處能比得過廣明院清淨溫雅。
“公子,查到了。”
李鶴珣應了一聲,筆鋒不曾中斷。
歸言繼續道:“鼠患是有人故意為之,但背後之人屬下暫時還未查到。”
“不過有一件事兒,屬下特意打聽了,府中的下人說,昨日沈大小姐派人去了二小姐的院中糟蹋她屋內的東西,而且二小姐自回府後便無人伺候,住的也是十分偏僻的小院兒。”
李鶴珣筆下一頓,驀然想起賞花宴那日,沈觀月當著長公主的面兒都敢那般明嘲暗諷,想來她回府後,定當也過得艱難。
那日在街上,她甚至連一張面紗的銀子都拿不出來……
過去種種畫面如走馬觀花一般從李鶴珣腦中閃過,沈觀月那日雖言語犀利,可她也不逞多讓,二人雖沒有口角之爭,但那實實在在的兩巴掌卻打得毫不猶豫。
半斤八兩,她不是讓自己受委屈的性子。
“公子,二小姐是庶女,她的生母曾經又是……屬下覺著,她在府中的日子應當並不好過。”
李家子嗣不多,雖是大家族,可府中如今除了他以外,也就一個庶子,還早早地下放去了別處。
後宅的隱私腌臢,他自小便沒見過,但他沒見過卻不表示不存在。
朝中官員大多家裡都有些不可言說的手段,他沒興趣打聽別人的家事,哪怕偶爾聽著了,也不會予以談論。
但沈觀衣日後是李家的人,哪怕她生在沈府,可這些後宅的手段她日後用不上,也不需要,如今便更不能平白無故地被人用這些手段欺了。
李鶴珣從容起身,朝著臥房走去,“更衣,備馬車。”
-
這頭,沈觀衣是醒來時才知曉昨夜府中發生了何事。
且阿讓為了讓她知曉鼠患是寧長慍命人做的,就是為了護著她動手一事,特地將早已想好對外的說辭告訴了探春,交代給她。
眼下,眾人只知曉沈府惱了耗子,唐氏與沈觀月被咬,再多的便被掩藏得死死的,一概不知。
探春繪聲繪色地剛說到激動之處,門外響起一聲震怒,“逆女,給我滾出來!”
“老爺?”
探春與沈觀衣面面相覷,就憑著那聲怒吼,也知曉來者不善。
探春心中惶恐,“老爺為何發這麼大的火?是不是夫人與大小姐……”
碗裡的白粥還剩下一半,沈觀衣慢條斯理地放下,用帕子擦了嘴,慢悠悠地道:“是他見不著我們好,走吧,出去看看。”
門外,沈書戎氣勢洶洶地帶著府中侍從走來,其中一人手上還端著一根戒棍。
沈觀衣剛起身不久,骨頭軟得提不起力氣,衣裳還是入睡時換上的薄裙,她懶洋洋地靠著門框,腦袋抵在門縫上,無辜又天真,“爹爹,發生何事了?”
上一次沈書戎便領教了她那張胡說八道的嘴,如今懶得與她多說,“你不敬主母,性子囂張跋扈,為人子女有悖倫常,今日我以沈家家規罰你,可有異議?”
“我——”
“來人,把戒棍拿來。”沈書戎打斷沈觀衣的話,不想聽。
戒棍足有半人高,沈書戎握在手中,冷眼瞧著倚在門邊依然面不改色的沈觀衣,呵斥道:“跪下!”
沈觀衣從方才起便一直在數沈書戎身後的人,整整八個,瞧模樣還都有幾分力氣。
她不會武,眼下也沒什麼刀劍,沈書戎若非要請家法,那她也沒別的法子,與其被他拂了面子受沈家家規,還不如帶著沈書戎一塊兒去死。
手指靠近隨意挽起的髮髻,沈觀衣慢悠悠地摘下玉簪,三千青絲如瀑披散,對上沈書戎幽冷的目光,她輕嗤一聲,抬步走去。
是戳瞎他一雙招子,還是從喉口貫穿……
罷了,他身後那些人瞧著便不好對付,還是對準心口穩妥一些。
她閒庭散步般地靠近沈書戎,慵懶閒適的姿態儼然不將任何人放在眼裡,沈書戎氣急,抬起戒棍便要將她那一身硬骨頭敲下去。
沈觀衣捏著髮簪的手猛地一緊,起勢抬手——
“老爺,李大人來了!”
戒棍驀然懸在半空,簪子在瞬間收回袖籠。
沈書戎蹙眉回頭,“你說誰?”
來人擦了一把頭上的汗珠,“李家公子,咱家未來姑爺。”
沈書戎臉上的神情瞬息萬變,他將戒棍遞給一旁的下人,回頭眼神複雜地瞧著沈觀衣。
披頭散髮,衣衫不整,與那日去正堂問安時相差無幾。
若非李鶴珣來得巧,今日他便要讓沈觀衣知曉,上京不是她那座破落莊子,沈家也不是她能為所欲為的地方。
沈觀衣不躲不避地與他對望,道貌岸然、諂諛取容,與前世並無區別。
她嘖了一聲,緩慢地挽起長髮,將玉簪原封不動地插入髮間,頗為惋惜。
若非李鶴珣來得巧,沈書戎現在就是一具死屍了。
“老爺,李大人還等著呢。”
沈書戎咬緊牙根,半晌後拂袖離去,“你給我待在這兒好好反省!來人,看著二小姐,不准她踏出院門一步。”
“是。”
家侍留下來了兩人,一左一右的守在院落門前,沈觀衣瞧了一眼,黑著臉轉身回屋,看向探春,“先前我讓你清點的家當,都清點好了?”
這沈府愈加惹人厭煩了。
探春點頭,“咱們還剩下一百多兩銀子。”
沈觀衣頓時蹙眉,一百多兩銀子勉強能支撐她與探春幾個月的衣食住行,但之後呢?
難道要她去做繡娘或是浣衣婦?
先前信誓旦旦要離開沈府四處遊歷的心逐漸消融。
吃苦受累她是不願的。
自她十歲至今,便從未短缺過銀兩,用的穿的都是極好的東西,若是為了離開沈府而去外面‘乞討’,倒不如她再拉著李鶴珣沉淪一次,做那誰都不敢妄言的人上人。
要不還是,不放過他好了。
沈觀衣撐著下巴,嫣紅的指尖摩挲著杯沿,眉宇中是難掩的猶豫焦躁。
李鶴珣不喜歡她,她不願上趕著去貼他的冷臉,便是為了權勢銀錢她也不想。
況且李鶴珣從前著實待她很好,她便是還恩也是應該的。
所以李鶴珣想要娶她,她便嫁給他,李鶴珣對這樁婚事有所抗拒,她便退婚。
可是……
這一世的李鶴珣似乎比那個整日陰沉著臉,令人捉摸不透的攝政王還要好拿捏一些。
她前世都能把那個魔頭玩弄於股掌之中,這顆小白楊,應當也不是難事?
好煩。
他便不能像前世那般喜歡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