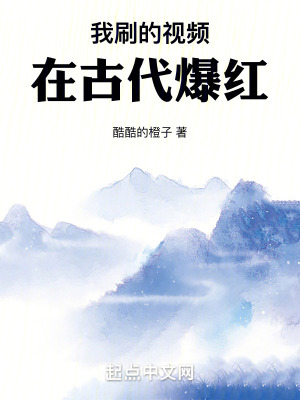懸姝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前院兒正堂。
沈書戎與李鶴珣對坐而視,木盤上的白釉青瓷茶盞晶瑩剔透,淡青色的茶水落入杯盞中,更顯透亮。
他堆著笑容寒暄,實則卻心思百轉,“不知李大人今日所來何事?”
李鶴珣從歸言手中接過一本冊子,遞給沈書戎,“沈尚書先瞧瞧。”
冊子很薄,也就是李鶴珣桌案上的滄海一粟。如今上京算不得太平,燕國各地也處於多事之秋,聖上既不作為,這些擔子便需要有人來扛。
清流世家,又是太子黨派的李家,便成了眾望所歸。
沈書戎面不改色地開啟冊子,才瞧了一眼便瞳仁驟縮,‘啪’的一聲合上,急道:“李大人,這是汙衊!本官怎會做那等齷齪的事。”
“沈大人的意思是你並未欺壓民女,也不曾將人丟到城外的院兒中自生自滅?”
“自然沒有!”沈書戎斬釘截鐵,握著冊子的手氣得發顫,“到底是誰在汙衊本官。”
“是不是汙衊沈大人說了不算,本官說了也不算。”李鶴珣又拿過一本冊子,淡淡道:“這是那民女的訟詞,她說大人先前對她百般好,還說要將她帶回府中抬為貴妾。”
沈書戎面色漆黑,放在桌下的手緊握成拳。
李鶴珣似是沒看見,繼續道:“但她不但沒等到大人兌現承諾,還被一頂轎子抬去了城外的院子,整日被人看著不能離開,且還有自稱是大人寵妾的女子找上門,不但翻遍了她的屋子,還砸爛了她的東西,讓她顏面無存。”
沈書戎咬著牙,恨極怒極。
半晌後,李鶴珣抿了口茶,漫不經心地掃過一旁還未來得及收好的戒棍,輕聲道:“據說那地方曾經還鬧過鼠患,倒是和沈大人如今的處境頗為相似。”
氣到一半的沈書戎電光石火之間突然明白了什麼。
為官二十載,他此時自然聽出李鶴珣話中的意有所指。
攥緊的手緩緩鬆開,沈書戎輕輕的撫平衣袍上的皺褶,笑道:“是,本官府上昨日也鬧了鼠患,衣兒住得遠不曾被嚇到,為了避免日後再發生這般離奇的事,本官覺著還是該讓她離主院近些的好,若出事也能有個照應。”
“但那孩子與李大人一樣,喜歡清淨,這不,今日還為了這事和我鬧彆扭呢。”
提起沈觀衣,沈書戎面上滿是寵溺無奈,他搖頭失笑,“那孩子隨了她孃親的脾性,主意大的很,性子又倔,日後恐怕還要李大人多擔待。”
李鶴珣深有所感,微微頷首。
沈書戎以為事情已經了卻,徹底放下心防與李鶴珣談天論地。平日在朝中李鶴珣是出了名的油鹽不進,除了太子,也不見他與別的大人有公事以外的來往。
今日趁著這個機會,沈書戎使盡了渾身力氣想要與其打好關係。
他沒想過沈觀衣那樣的女子,竟能將李鶴珣迷得暈頭轉向,激動與興奮不言而喻。
半個時辰之後,笑聲漸散,賓至如歸,沈書戎起身相送,嘴角的笑容揚得遲遲落不下來。
就在李鶴珣即將踏出院門之時,他驟然想起什麼,回身望向沈書戎,青衣飛揚,腰間繡成的白鶴栩栩如生,“沈大人,順天府已經受理此女的訟狀,還望沈大人好自為之,莫要為朝野上下蒙羞。”
挺拔的身影逐漸消失在月亮門後,沈書戎僵硬的嘴角驟然壓下,猶如一盆冷水從頭澆到腳,彷彿他剛才的喜悅就是一場笑話!
李鶴珣什麼意思?不打算幫他將這事壓下?
沈書戎氣結。
李鶴珣此人,還真是……油鹽不進,鐵板一個!虧他以為沈觀衣將他勾得變了性子,原來竟是他高估了沈觀衣。
沈府門前,歸言跟著李鶴珣鑽進馬車,不動聲色地瞧了一眼自家從容矜貴的公子。
方才他可看的真真兒的,公子最後那句話說完後,沈尚書臉上的神色變化萬千,精彩至極。
先前公子在眾多冊子中翻找出這樁小案子可算不得容易,便是他也以為公子是來替二小姐做主的。
但到頭來,主也要做,案子也不能丟。只能說沈尚書遇到他家公子這般眼裡不容沙子的姑爺,回頭指不定罵得多難聽呢。
“回府吧。”
“公子,您不見二小姐一面嗎?”人都來了,就這樣走,多虧啊。
公子平日公務繁忙,二小姐又不主動來尋公子,這樣下去,何時才能增進夫妻情誼?
見他不語,歸言又道:“屬下覺著,您今日幫了二小姐,總歸是要讓她知曉的,說不定二小姐感激之餘,便不想退婚了呢?”
李鶴珣心中冷意連連,此時並不想見那個總是令人著惱的女子,“聖旨賜婚,不是她與我能做主的,更不會因為一件事而左右結果。”
這話,歸言一個字都不信。但見公子堅持,又想起府中還未處理好的事務,頓時閉了嘴,消了心思。
他家公子又不是那些只知道風花雪月的紈絝子弟,大理寺的事務需要他平日審理,朝中事務也總是被各位大人拉著談論,算一算,著實沒有多少心思能放在二小姐身上。
馬蹄揚起,帶有李家族徽的馬車平穩地駛離沈府門前。
與此同時,唐氏聽說今日府中發生之事後,翩然走至正堂,壓著心中喜意,故作忐忑道:“老爺,李家該不會是來……咱家二姐兒的婚事可不能丟啊。”
見沈書戎面色陰沉,她只覺著自己十之八九猜中了。
剛剛升起的一絲雀躍,便被沈書戎冷沉的聲音打斷,“你說得沒錯,與李家的婚事不能丟,所以此事就此作罷,你與月兒的傷,便如外面傳言所說,是老鼠咬的。”
而那外室他會想法子帶回來,免得當真被她告的顏面無存。
唐氏面色一僵,險些維持不住臉上的神情,只聽沈書戎繼續道:“今日李鶴珣向我透露李家有意提前成婚,最好就在半月後的七月初一,所以沈觀衣的嫁妝,你得趕緊準備起來,免得到時候丟了面兒。”
“嫁……妝?”
她不但討不回公道,還要給沈觀衣準備嫁妝?
她聲音中的不甘沈書戎怎會聽不出來,轉頭不耐道:“收起你那些心思,沈觀衣的嫁妝你就按照你這些年給月兒的準備的規格來。”
“憑什麼?”唐氏再也維持不住臉上的神情,驚聲道:“月兒是嫡女,她一個曲娘所出的庶女,嫁妝怎麼能與月兒相同!”
婦人便是婦人,整日眼中只知道盯著那一畝三分地。
沈書戎懶得與她多說,“這事按我說的辦,到時若因為嫁妝的事兒讓沈家抬不起頭來,你這正妻的位置換個人來坐也未嘗不可。”
男人走後唐氏怔愣了許久,待她回過神時,淚珠早糊滿了眼眶,悲拗鋪天蓋地地襲來,渾身的力氣如同被抽乾一般墜在椅子上。
“夫人……”冬暖心中不忍。
唐氏遙遙抬頭,眼眶泛紅,“冬暖,他說他要換個妻子,他要換個妻子啊……”
“我這些年忍著他納了一個又一個小妾,替他打理家宅,對府中庶出視如己出,讓他安心做他的大官,無後顧之憂,我做的還不夠嗎?他明知我在乎這個位置,時隔六年,卻偏偏還以此來剜我的心!”
當年柳商初入府中,受盡寵愛,她最得寵時,沈書戎甚至動過要立她為妻的打算,這般年少輕狂不合規矩之事,他差點便為柳商做了。
她日日以淚洗面,皆因孃家只是小門小戶,父親不過區區七品閒官,那時沈書戎官途順暢,她心中本就不安,怕因無法在家世上給予幫助被休棄,而柳商恰好在那時出現,恨怨二字都不夠道出她當初的無助。
後來她好不容易弄死了柳商,可她的女兒卻還要回來禍害這個家!
冬暖瞧著面目猙獰的夫人,知曉她心中難受委屈,但後宅女子,孃家勢微夫家不疼,事事便只能忍著。
沈觀衣本就不似尋常女子循規蹈矩,她離經叛道,又是個囂張跋扈的主兒,而今無論是李家還是老爺的態度都在明晃晃地告訴她們,沈觀衣動不得。
“夫人,這後宅的苦您最是明白,眼下二小姐雖佔著上風,可李家門風嚴謹,咱們何不順了老爺的心意,讓二小姐風風光光地嫁去李家?”
“夫人且等著看吧,日子還長著呢,總有她栽跟頭的時候。”
-
沈府近來很忙,常有面生之人進出府內,連端茶小廝都忙得腳不沾地,而沈觀衣那日只被關了一個時辰,守在院門的家僕便走了。
之後連著三日大雨,她在屋內悶了幾日,終於守得雲開,晴空萬里。
只是令她興致闌珊的是,那日的雜耍班子不見了。
她百無聊賴地走在攤販密集的街上,上京大多地界兒前世她都走了個遍,著實沒什麼得趣的地兒,也就尋藝坊能令她流連幾分。
沈觀衣抬頭瞧了一眼,天光大亮,才剛過午時,於是拿著僅剩的一百多兩銀子,帶著探春聽曲兒去了。
探春新奇地瞧著,此樓以紅黃兩色為主調,有秦樓楚館的靡豔,亦有茶坊的清雅,一共三層,除一層大堂外,樓上皆是廂房,越往上要的銀子便越多。
沈觀衣如今沒有銀子,自是去不了廂房。
她尋了個正對戲臺的位置,帶著探春坐下,臺上正咿呀唱著上京時下最愛聽的曲子,悲涼悽楚的調子引人入勝,沈觀衣撐著下巴,聽得認真。
探春是第一次進藝坊,現下正好奇的緊,仰著頭瞧來瞧去,從紅綢看到掛在牆上的羽扇,突然,雙目突兀地對上了一人的視線。
二樓的望柱旁,二人負手而立,衣衫一紅一白,皆貴氣逼人,似在談論什麼。
其中著紅衣的那人對上探春震驚的目光,聲音驟然頓住,餘光在瞧見探春身邊坐著的姑娘後,眼底暗光乍現,嘴角緩慢地彎起一道冷懍的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