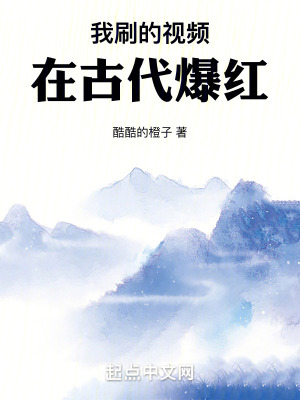懸姝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臺上唱的悲慟,悠悠翠幕,愁緒萬千。
沈觀衣聽的認真,卻忽覺袖籠被身旁之人攥住,她側頭看去,只見探春面上難掩高興,“小姐,世子,世子……”
她順著探春的目光抬頭望去,二層走廊上三三兩兩的人中,就屬寧長慍最招人,那身衣裳紅豔卓絕,玉冠束髮,自冠頂兩側順下的細長吊穗與長髮糾纏,此時他正捏著酒杯與身側之人說著什麼,似是壓根沒發覺她在看他。
當真沒發覺嗎?
沈觀衣回過頭,並不想去鑽研他的心思,隨手捏起小二送來的點心,悠哉地將目光又放回到臺上去。
探春微怔,“小姐,世子在那邊,咱們不過去嗎?”
“過去做什麼,咱們聽咱們的曲兒,別去擾他。”
探春似懂非懂,但見小姐不動,她也回過頭正襟危坐,不再往那處多看一眼。
餘光一直注意著這頭的寧長慍眼尾一冷,握著酒杯的指尖略顯用力,微微泛白。
“阿慍,這處也忒無趣了些,姑娘也沒雲煙樓的好看,咱要不換個地兒吧。”
站在寧長慍身邊的男子弓著腰,雙手懶散地搭在勾欄上,三指掐著杯口,搖搖晃晃,稍不留神便會掉下去。
他側頭看向寧長慍,“怎麼說,換不換?”
寧長慍回過神,轉身走進包廂,“雲煙樓?如今已經大不如前了。”
“趙玦,你若不想聽曲兒,大可以先走。”
廂房木門敞開,寧長慍席地坐於蒲團上,見趙玦遲遲不曾回應,掀起眼皮一瞧,那廝不知道看見了什麼,眼神直勾勾地望著下面。
能讓他多看一眼的,除了箭術高超之人便是漂亮的女子了。
尋藝坊的藝中,可沒有射禮一說,寧長慍將酒杯嗑在桌上,喚道:“趙公子又瞧上哪家姑娘了?”
趙玦嘖了一聲,旋身回到廂房,將門關上後,屈膝坐在寧長慍對面,外間婉轉的曲聲絲絲縷縷的傳來,他挑眉賣了個關子,“你猜我方才看見了誰?”
不等寧長慍回話,他便自己忍不住一股腦地交代了,“沈家二小姐。”
提起沈觀衣,趙玦腦中便不由自主地浮現那日賞花宴上的驚鴻一瞥,嘖嘖稱奇,“先前你南下沒回來,不知道那沈二小姐長得那叫一個絕,說是天姿國色也不為過。”
“哦?當真如此好看?”寧長慍漫不經心地把玩著垂在胸前的細穗。
被人懷疑眼光是趙玦萬萬不能忍的,“你若不信去外面瞧瞧,那沈二小姐如今就坐在下面呢。”
他晃著腦袋,如品酒般回味,“當真是上京獨一無二的好顏色啊。”
寧長慍默不作聲地抿了一口酒,趙玦睜開眼,頗為遺憾地嘖了一聲,“就是名花有主,動不得,動不得啊。”
“還有你趙公子動不得的人?”
趙玦怪異地瞧了寧長慍一眼,“沈二小姐與李家那位定親之事早已傳遍上京,哪怕你先前不在京城,如今都回來好些時日了,竟會不知?”
“一個小小的少卿罷了,你怕了?”
對上寧長慍淡然不屑的目光,趙玦有些無語。
少卿不可怕,可怕的是李家,如今上京幾乎一半的權勢掌握在李家手中,連太子都要巴結討好的人,他們兩個二世祖憑什麼和李鶴珣鬥。
自年少時,李鶴珣便與他們不同,從不與他們在一起玩鬧便罷了,家中長輩還總是耳提面命地將他們與李鶴珣做比較。
誰家公子少時沒有嫉妒過李鶴珣,但那又如何,人家十七歲高中三元,如今更是朝中官員,哪像他們,連個功名都考不上,皆等著自家安排,將來撈個閒官噹噹,再憑著這些年在上京的根基往上爬。
李鶴珣那人,與他們從來都不是一處人,也不是他們能得罪的人。
趙玦回過神,驟然發現寧長慍身前的酒壺已然空了兩個,他蹙眉道:“你今兒個怎麼了?”
寧長慍不語,一杯接著一杯,只覺心中如同塞了一團棉花般,堵得慌。
他抬手拭去嘴角的酒漬,目光粼粼地看向趙玦,“你說我去毀了這樁婚事如何?”
“你瘋了?”
趙玦只當他吃醉了酒,懶得搭理,拍拍衣衫上莫須有的灰塵起身。
這處當真無趣,若不是今日不好進宮,他哪能與寧長慍來這處虛度光陰,“我走了,你自己慢慢喝吧。”
臨到踏出門外時,趙玦又回身勸慰道:“我勸你別做傻事啊,人家的婚事,你摻和進去有什麼好處。”
人家的婚事……
修長分明的手指虛掩著額角,寧長慍頭痛欲裂,只覺腦中紛紛擾擾,隨時都會炸開一般。
門外琴音嫋嫋,伴隨著木門合上的吱呀聲,耳邊若有似無地響起一道俏生生的輕呼,“長慍哥哥!”
他恍然間抬頭看去,如春日乍現,她穿著粉白襦裙,如一隻剛剛破繭而出的蝴蝶,朝著他飛撲而來。
那時,好像是熙平四十年。
他與趙玦一行人從雲煙樓出來,瞧著天色尚早,便想著去莊子上看看他養的小姑娘。
兩個月不曾來的地方乾淨如初,十三歲的沈觀衣也如往日一般在瞧見他的瞬間,眼中盛滿了光,提著裙角飛奔而來。
只是她臉上明媚的笑意在距離他一步之遙時戛然而止,杏眸中漸漸盈滿了水光,明明委屈卻偏要故作若無其事地試圖將淚珠揉回去。
不滿地嘟囔,“你是不是又去喝花酒了?”
小姑娘鼻子靈,聞著便聞著了,他不曾刻意避開她。
她咬著唇,羞得雙頰通紅,卻仍舊質問出聲,“我長大後一定比她們好看,你就不能多看看我嗎?”
他尤覺好笑,“我看她們可不是因為她們好看。”
沈觀衣似乎不明白,扁著嘴,覺著他在騙人,“可阿讓說了,好看的姑娘總是能讓你多瞧一眼的。”
說著,她便提著裙角轉了一圈,頭上的珍珠步搖晃悠悠的,煞是可愛,“你看,這是你前些日子送來的新衣裳,我穿著是不是也不比她們差。”
他沒說話,沈觀衣便抿了下唇,沒骨頭似的倚在他臂彎處,小姑娘不高,堪堪碰著他肩膀,委屈巴巴的揪他衣袖上的雲紋繡線,“長慍哥哥……”
“嗯?”
“我日後會變得和我娘一樣漂亮的,你等等我好不好?”
他只當戲言,不曾放在心上,調侃道:“你才多大,就學著旁人傾訴衷腸了?平日裡少看些話本子。”
“我十三了。”她猛地抬起頭,不甘示弱地挺起胸脯,“探春說,京城的女子十三便可以相看人家了。”
“我沒有爹孃替我相看,那我便自己看。”
他被沈觀衣理直氣壯的小模樣逗得樂不可支,“所以你看上我了?”
“長慍哥哥!”沈觀衣又羞又惱,急得跺腳。
柳絮紛飛,院中的枇杷樹結了果,那是沈觀衣第一次向他表露心跡。
他說不上高興與否,只是覺著當年無意中的善舉,救下的小姑娘眨眼間便長大了,有了女兒家的心思。
就像是一朵悄然盛開的牡丹,攜著火光,不顧一切地釋放著她心中的思慕之情。
他也不知從何時開始,從推拒到縱容,甚至為了讓她患得患失,常常做出一些令她生氣的事。
可事後,只要他哄一鬨,沈觀衣便又用那雙依賴眷戀的目光看著他。
他早早地便知曉,他這些年對沈觀衣的照顧是旁人如何都比不過的。
沈觀衣就像是他圈養在身邊,只屬於他一人的東西。
而這件東西,在他離京的時候,被人偷走了。
寧長慍眼尾泛紅,長袖猛地掃過桌案,東西灑落一地,清脆的響聲片刻後才緩緩停下。
那些人為什麼要搶走他的東西!
她是他的,只能是他的!
寧長慍撐著木桌起身,眸光大盛,嫉妒嗜心,如灼灼燃燒的火焰,支撐著他跌跌撞撞的朝著門外走去。
-
一曲唱罷,沈觀衣敲了敲桌子,喚醒一旁睡得正香的探春,“走了。”
探春猛地驚醒,下意識去摸嘴角,在瞧見沈觀衣正盯著她時,訕笑道:“小姐,奴婢粗鄙,著實欣賞不了這些曲兒。”
“我知道,沒怪你,走吧。”
沈觀衣起身,裙襬自椅上滑落,探春抹抹嘴,連忙跟上。
“小姐,方才都唱了些什麼啊?奴婢沒聽著,您和奴婢說說唄。”
探春臉上掛著討好的笑,沈觀衣斜睨了一眼,嫌棄地回過頭。
前世那個擋在她身前,將欲要害她之人折磨得不成人樣的探春姑姑,眼下還真是瞧不出半點威勢。
“說了你也聽不明白。”
探春不依不饒地扒著沈觀衣,“小姐,您就和奴婢說說嘛。”
沈觀衣沒好氣的看向她,“你——”
“這位姑娘。”
小二突然打斷二人說話,小跑著上前,攔住探春,訕笑道:“老闆有請,不知姑娘能否賞些薄面?”
“我?”探春與沈觀衣對視一眼,不敢置信地指著自己。
在小二再三保證沒有請錯人後,沈觀衣才掩唇笑道:“快去吧,說不定是老闆只是想問問你坊中曲子到底是哪點聽著讓人想睡覺。”
“小姐!”探春羞惱,但仍舊在小二殷勤的目光中跟著走了。
沈觀衣含笑回頭,四處瞧著藝坊的佈置,一層的廂房不多,每道門前都掛著刻有名字的木牌,尋藝坊平日晚間生意不錯,白日倒是不見人多。
她慢吞吞地從刻著春日彩三字的門前走過,腳步未停,門前掛著的鈴鐺晶瑩透亮,應當是琉璃做的,沈觀衣多瞧了一眼。
突然,春日彩的房門被人從內開啟,她雙眸瞪圓,手腕被人緊緊扣住,紅影一閃而過,木門重新緊閉,周遭恢復如常,只有門上的鈴鐺搖晃出清脆的聲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