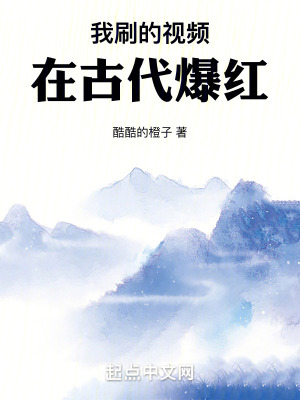懸姝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惱怒驚訝只有一瞬,沈觀衣在瞧見那抹豔紅之時,便知曉他是誰了。
後背抵在牆上,髮絲輕顫,沈觀衣的目光從捏著她肩膀的手上移開,抬頭對上他赤紅的雙眸。
黝黑的碎髮從額角撫過他漂亮的鳳眸,酒氣徐徐,沈觀衣抬手替他將髮絲勾回耳畔,眨眼輕笑,“長慍哥哥,好巧啊。”
他嗓音低啞,眸中濃墨滾滾,“我不找你,你是不是準備今日就這般過去了?”
沈觀衣唇瓣微張,神情莫名,這般無辜疑惑的樣子,倒是顯得他在刻意刁難了。
但方才她分明瞧見了他,就算沒瞧見,她身邊的小丫鬟難道不會告訴她嗎?
可她沒來!
寧長慍只覺從聖上賜婚那日到現在,積攢的火氣如有實質,要將他灼燒殆盡,“沈觀衣,你當本世子是菩薩心腸?白白養了你這麼多年,到頭來你說走就走?”
他的掌心不由得用了力氣,似是要將這衣衫之下的骨頭捏成粉碎。
沈觀衣疼得蹙眉,下意識便要伸手去撓他。
寧長慍是吃了不少酒,但還沒弱到能被一個小姑娘撓了的地步。
皓腕被扣住,沈觀衣動彈不得,疼得眼尾都滲出了水珠,心中氣結,但她瞭解寧長慍的性子,硬碰硬,只會讓他氣焰更勝,現下她還在他手裡,得罪了他遭罪的是自己。
沈觀衣壓下心中火氣,水眸盈盈地望著他,扁著嘴,氣若游絲的嗓音中帶著一抹不易察覺的嬌,“長慍哥哥,我肩膀好疼……”
“娓娓聽你地話,你先鬆開手好不好?”她急得快哭了。
但寧長慍與她相識六年,她的小心思瞞不過他,一個連剜去皮肉都能咬牙硬挺過來的姑娘,怎會因為這點疼便哼唧著要哭。
她嬌氣,無非是因為知曉只要她哭一哭便能解決許多事。
示弱二字,她向來懂得其要領。
寧長慍冷笑一聲,緩緩鬆開手,目光灼灼地盯著她,“聽我的話?我若是讓你回莊子上呢。”
果不其然,方才還柔弱的他一手便能掐死的小羊羔,頓時露出了獠牙,惡狠狠地瞪著他。
淚眼矇矓什麼的,不過是錯覺罷了。
那就是一隻喂不熟的白眼狼。
沈觀衣揉著疼痛的肩膀,冷眼如刀,恨不得將寧長慍戳出幾個洞來,“我為何要回去!”
他被氣笑了,雖然知曉這丫頭嘴裡沒句實話,但方才還信誓旦旦地說著聽他的話,下一瞬便忘到了九霄雲外,他便如此好糊弄?
“不回去你要做什麼,難不成當真嫁到李家去?”
沈觀衣理所當然地點頭,“有何不可?聖上賜婚,我總不能抗旨不遵。”
涼風徐徐,攜著乾燥的氣息從敞開的窗欞蔓延進來,二人沉默許久,還是沈觀衣先耐下性子服了軟。
她長嘆一聲,“長慍哥哥,哪怕我不嫁入李家,也不會再回莊子上了。”
她與之相處二十多年的長慍哥哥,他喜歡什麼,性子如何,她都一清二楚。
當初她既能讓寧長慍對她愛恨難捨,如今便能斷了他的念想。
寧長慍盯著她許久,末了冷不丁地半眯著眸子,“沈觀衣,你到底想做什麼?”
她將先前對阿讓的那套說辭原封不動地說給了寧長慍,可寧長慍壓根不信,“少拿那些話來敷衍我。”
沈觀衣驀地一頓,走至蒲團旁坐下,“既你想知道,那我便與你說實話。”
寧長慍眼底蔓延出一絲冷嘲。
“我喜歡他。”
片刻的寂靜後,是寧長慍的嗤笑。
喜歡他?
他眸子裡的光明明滅滅,最終沉寂在黝黑的瞳仁裡,“沈觀衣,你有膽就再說一遍。”
“你知我先前在莊子上為何睡得那般早嗎?”
“聖旨下來,我高興得連著兩日沒有睡好。”
在寧長慍死寂一般的眸子裡,沈觀衣笑眼彎彎,女兒心思一覽無餘,“我喜歡他啊,所以才這般高興。”
“長慍哥哥,我一直都將你當作親兄長,你會替我高興的,對吧?”
親兄長?當初是誰拉著他的袖子不放,只求讓他多看看她。
是誰讓他等她長大!
“沈觀衣,你沒有心嗎?”
沈觀衣赫然怔住,那雙鳳眸似乎在瞬間消了氣焰,黯淡無光,他頹喪得宛如前世離京的那個夜晚。
過去種種,前世與今生似乎在瞬間交織成初見寧長慍那日。
那時與今日不同。
風雨交加,雷聲陣陣,她被幾個奴僕欺壓了許久,好不容易從莊子裡逃出去,卻被石子絆住了腳,滾在泥潭裡遲遲爬不起來。
遙遙而來的馬車停在離她三步遠的位置,她不知哪來的勇氣起身跪在馬車跟前,給車裡的主子磕頭,泥水腥臭,濺了滿臉,她顧不上擦,只一個勁地懇求道:“大人,求你救救我,求求你……”
氈簾被一雙白皙的手掀開,眉眼精緻的少年坐在馬車中,錦衣華服,矜貴傲然。
他高高在上地看著她,那雙漂亮的鳳眸明亮耀眼,半晌後,才勾唇笑道:“阿讓,去瞧瞧。”
說罷,他慢吞吞地走下馬車,握著一柄梅花油紙傘,傘柄鑲了銀線,是她從未見過的好看。
少年踩著長靴行至她身前,泥水浸溼了他的衣襬,沈觀衣尤覺心疼。
這麼好看的衣裳,怎就沾了泥呢。
大雨滂沱,狂風大作,她早已摔成泥人,髒得不成樣子。
寧長慍執傘停在她身前,傘沿傾斜,遮去砸在她身上有些疼的雨珠,挑眉道:“你怎的這麼髒?”
她肩膀瑟縮,羞愧地垂下頭,撐在地上的手被汙水蔓延遮擋,她抓著堅硬的石子,死死壓住想要逃走的心。
“罷了。”
沈觀衣瞳仁緊縮,心口一緊,以為他欲要反悔。
她不髒的,莊子上的人都說她是狐媚子,說她長了一張勾人的臉。
沈觀衣慌亂地抬手想要抹乾淨臉上的淤泥,滿是紅瘡的手伸到半空,便瞧見一方乾淨玉白的絹帕如同昏暗天光中唯一的亮色,驟然出現在眼前。
她驀然怔住,耳邊是寧長慍輕緩的聲音,“走吧,本世子帶你去洗洗。”
她那時知曉寧長慍只是將她當成一個小孩兒,或是一件消遣的趣事兒,並不曾放在心上。
是她一次又一次地擠進他的眼中,引來他愈加深沉的目光。
若景寧侯府沒有害過她孃親該多好。
她不會拽他入泥潭,不會讓那雙耀眼奪目的眸子因為她而黯淡無光。
沈觀衣回過神,悄然抬手,如往日一般去攥寧長慍的袖袍,“長慍哥哥……”
嫣紅的指尖剛碰到衣衫便被寧長慍大力揮開,他嘴角上揚,笑意不達眼底,言辭鑿鑿的想要戳穿她的謊言。
“你住的莊子距離上京五十里,不算太遠,可上京這麼多年過去,幾乎無人知曉沈家還有一個庶女被養在莊子上。”
“你說你喜歡他,那處連沈家都不願去,他到底是何時出了京,你又是何時見到他的?”
“難不成憑你回京的這些時日,便對他愛慕難捨?那你的喜歡也太過輕浮。”
“六年,你在我跟前撒謊,不覺得自己愚蠢?”
沈觀衣收回手,知曉他這人不好應付,如此,她只能俏生生地問他,“非要見過才算喜歡嗎?”
寧長慍似是知道她要說什麼,在他慍怒驚慌的眸子中,沈觀衣依舊不怕死地繼續道:“那為何我見了你這麼多年,卻不曾喜歡?”
不曾喜歡。
酒意上頭,寧長慍氣得雙眼發暈,忍不住扶著桌案才勉強站穩,兩指按壓著額頭上跳動的青筋。
她是真的敢!
“從前是誰讓我等她,是誰眼巴巴地求著我,說要入侯府做夫人的!”
她從前說這些話的時候,早已知曉景寧侯與她孃親的恩怨,所以……她是故意的啊。
她想嫁給寧長慍讓侯府此後不得安寧,只是沒曾想有了李鶴珣這個變故。
沈觀衣天真得近乎殘忍,“年少不更事,長慍哥哥不也常常訓我,說那些女兒心思當不得真。”
寧長慍一直知曉沈觀衣就像是一個刺蝟,平日裡乖巧地露出自己的肚皮,雖然嬌氣了些,卻更惹人愛憐,想讓人將這世間一切都捧到她面前,還怕她嫌棄不夠好。
可一旦惹惱了她,那渾身的刺便如同不要命般地扎向旁人,不將身上戳幾個窟窿便不肯罷休。
寧長慍唇瓣輕啟,嗓音攜著濃郁的疲倦,“你非要嫁他?”
沈觀衣不語。
“若我不讓你嫁呢?”
他眼底逐漸蔓延出一絲懇求,不等他開口,沈觀衣便輕聲打斷道:“長慍哥哥的恩情,娓娓銘記於心,待我嫁去李家,若有能幫襯得上的地方,一定不會推辭。”
那些到了嘴邊的衷腸被他咬碎了牙,混著血沫嚥了下去。
刻在骨子裡的驕傲不允許他低三下四地去求一個女子,還是一個將他棄如敝屣的女子。
他狠狠閉上眼,半晌後才艱澀地從唇縫裡擠出幾個字來,“隨你。”
衣袍在空中劃過一道轉瞬即逝的緋色,與房中格格不入的酒氣眨眼便被屋內原有的薰香淹沒。
寧長慍走時看她的那一眼裡沒有半點情誼,這六年的照顧與縱容似乎在瞬間被他盡數收回。
可惜嗎?或許吧。
但這就是她要的結果,所以也談不上後悔。
惆悵悲拗不過片刻,沈觀衣便慢吞吞地起身,帶著探春回了府。
“小姐,那尋藝坊的老闆好生奇怪,說要見奴婢,可奴婢等了他半晌也不見人。”
她自然見不到人,畢竟人與她在一處。
沈觀衣懶洋洋地回應著,主僕二人閒聊半晌,直到馬車停在沈府門前,二人才噤了聲。
今日天色尚早,沈觀衣剛踏進府中,便聽見下人絮叨著什麼禮單冊子,嫁妝物件兒。
她略微詫異,示意探春去打探一二。
不消片刻,探春便急促地回來稟報,“小姐,是夫人在準備您的嫁妝,據說李家將婚期提前到了半月後,府中上下正忙著籌備呢。”
正堂中,下人往來不絕,大大小小的箱子正被冬暖帶著清點。
唐氏坐在椅子上,一手拿著嫁妝單子,一手打著算盤,整個正堂瞧上去異常忙碌。
假山石後,沈觀衣站著看了一會兒,不明白婚期為何會突然提前。
“二小姐,您回來了。”
冬暖偶然抬眸,正好瞧見山石後的一點裙角,稍稍往旁走了一步,便看清了來人是誰,頓時眉開眼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