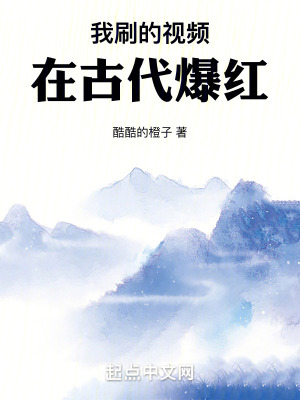懸姝提示您:看後求收藏(書包網www.shubaoinc.com),接著再看更方便。
“二小姐,這婚期是李家那邊要求的,奴婢也不知他們為何這般著急,按理說您今年也才十六,即便是十七八嫁過去也是不晚的。”
“老爺和夫人都同意了,這不,還剩半月,下月初一您便要嫁去李家,嫁妝什麼的咱們都只好加快準備。”
“您放心,夫人待您與月姐兒一樣,看看這滿屋子的東西,都是夫人親自盯著的。”
月朗風清,雀兒自枝椏上掠過,樹影斑駁間,少女坐於窗欞前,琴音懶散,雜亂無章,可細細聽去卻又心曠神怡,說不出是哪首曲子,但撫琴之人琴藝高超,近於無我。
突然,啪地一聲,琴絃被人猛地按住,隱隱發顫。
沈觀衣自從冬暖那裡知曉提前婚期是李家的意思後,已經在矮塌前坐了一個時辰了。
探春佈置好晚膳,高興喚道:“小姐,今日夫人不知怎得了,竟讓廚房給咱們送了這麼多好吃的,小姐您快來瞧瞧啊。”
事出反常必有妖。
前世壓根就沒這一遭,沈觀衣從琴上撫過,眼底的光明明滅滅。
想起李鶴珣每次見她時的氣惱與沉鬱,她蹙起眉頭,總不能是李鶴珣讓她嫁過去。
可若不是李鶴珣,那便就只剩下李家。
李鶴珣不願違抗聖意,她依了他,自己去求公主,可李鶴珣連李家都搞不定嗎?竟讓他們將婚期提前了。
到時候她當真嫁過去,李鶴珣還指不定將她冷落到什麼地步呢。
那人可不像沈府這一家子好打發。
沈觀衣愁得發了脾氣,盯著那一桌唐氏送來的晚膳,冷聲道:“扔出去!”
公主那邊如今還不曾回話,原先並不著急的時間如今只剩下半月,若公主遲遲不曾答應,難不成她當真要嫁去李家,受李鶴珣的冷眼不成!
她嫁他的前提是他願意娶,而不是被逼無奈,最終連相敬如賓都做不到。
-
翌日,風和日暄,一輛不起眼的馬車自上京街道駛過,堪堪停在東風茶坊門前。
馬車內,隱隱傳來一道不耐的聲音,“放著衙門不去,日日待在這茶坊議事,衙門的茶不夠他們喝的?”
探春連忙心虛地拉住沈觀衣的衣袖,阻止她的大放厥詞,“小姐,您小點聲。”
“聖上整日沉迷煉丹,臣子又只知道往茶坊裡鑽,燕國怎麼還不完!”
“小姐,您消消氣,消消氣。”探春連忙抬高了聲音,試圖壓下沈觀衣的怒火。
自離開莊子的前一天起,小姐就像是變了個人一般,總是做一些令她震驚之事,如今更是口不擇言。
探春心裡苦,怕這大逆不道的話被誰聽去,就憑著她們二人這身份,壓根活不到明日。
沈觀衣氣的胸脯一上一下,恨不能衝進去將所有人大罵一通。
前世她當攝政王妃的時候,又不是沒做過這等事情,誰敢多說她一句!
“小姐,李大人按時上朝,為國為民是好事啊,日後您嫁去李家,有這麼一個夫君,免不了要得多少貴女的羨慕呢。”
“呵,誰稀罕。”
她天不亮便去李家遞拜帖見李鶴珣,結果被告知人上朝去了。
馬車慢悠悠地去了宮外,等到朝臣下朝,卻仍舊不見李鶴珣身影,宮門侍衛說他應當上衙去了。
於是她又去了大理寺,結果倒好,人不在,與大臣們來此處喝茶了。
眼下已近午時,她如同被人當狗一般溜了一上午,眼下怒火攻心,哪裡顧得上那麼多。
探春連連安撫,“是是是,您不稀罕,是李大人不識抬舉,整日亂跑,害得小姐受累。”
“奴婢這就去將李大人帶下來。”
沈觀衣臉色好了些許,紅唇緊抿,半晌才從喉口擠出一道輕輕的應聲。
探春不敢耽擱,連忙起身彎腰,掀開氈簾下了馬車。可轉頭,便見不遠處迎來一輛更為精緻大氣的馬車。
東風茶坊開在巷口,門前狹窄,向來不許馬車停留。
如今她們的馬車堵在門邊,從巷子盡頭又醒來一輛,眼瞧著便要撞上,那輛馬車猛然停住,車伕將馬鞭一折,指著探春,囂張地怒喝,“大膽,敢擋我家主子的去路。”
探春嚇得肩膀微縮,連連道:“我們這就走,這就走。”
上京遍地是權貴,探春不想惹事,但沈觀衣本就不曾消下去的火氣瞬時又冒了出來。
她猛地掀開窗邊的帷幕,美眸流盼,怒意升騰,卻將這張小臉襯得更加明豔,“讓他們換道。”
霸道的言辭引來車伕的怒目,“你是哪家的小姐,竟敢——”
“吵什麼。”馬車內傳出的聲音低沉喑啞,略顯不耐,打斷了車伕的話,“直接殺了就是。”
將殺人說得如此輕描淡寫,探春面帶惶恐的看向沈觀衣,“小姐。”
那道聲音,沈觀衣覺著有些耳熟,但她記憶不深,想來要麼是這人前世死的早,要麼便是身份低微,所以才沒讓她記住。
不等她多想,車伕已經將馬鞭一甩,帶著破空之勢,如一柄利刃襲來,欲要連人帶馬車,通通葬身於那長鞭之下。
真是好不講道理!
馬車轟然倒下,沈觀衣因縮在角落躲過一劫,此時正趴在廢墟之中,嗆得不停咳嗽,“咳咳……探春。”
探春連忙跑過去將小姐扶了起來,“小姐,您沒事吧?”
怎可能沒事,那些碎木頭砸得她疼死了,沈觀衣就著探春的手臂起身,咬牙切齒地瞪著不遠處欲要使來第二鞭的車伕。
她猛地抬手,一掌拍在沒了馬車,只剩韁繩的孤零零的馬屁股上,怕力氣不夠,兩指狠狠一擰。
馬兒啼叫,痛得揚起馬蹄朝車伕飛奔而去。
這一聲將雙手環胸靠在二樓漆柱旁閉目養神的歸言吵醒了。
連帶著爭論不休的官員們都停滯了一瞬,有人蹙眉道:“下面發生了何事,今日怎的這般吵?”
“這茶坊咱們不是包下來了嗎?怎麼還會有閒雜人等過來,掌櫃的呢,掌櫃的!”
被打斷了思緒,李鶴珣也略微不悅,目光幽幽地看向歸言。
歸言站在窗邊伸長了腦袋往下看,只一眼便大驚失色地回了頭,在眾人不耐的目光中,吞吐道:“公、公子,是二小姐。”
“二小姐出事了!”
歸言口中的出事,大抵就是馬兒一通亂撞,差點從車伕身上踐踏過去不說,還撞翻了馬車。
沈觀衣行至車伕身前,見他捂著胸口倒在地上,除了身上有些灰塵外,並未有什麼事,頓時氣不打一處來,一腳踩在他的小腹上,狠狠一攆,隨後雙腳踩上去,跳下來,踩上去……
“啊——”
探春大驚失色,連滾帶爬地過來拉住沈觀衣,“小姐,小姐您做什麼啊。”
“自然是收拾他!”
車伕明面上瞧著沒什麼傷口,可那馬兒可是對著他撞過來,要不是有幾分功夫在身,早就成了肉泥,眼下五臟六腑都如同錯了位,痛苦不堪還被人踩在腳底下,他連忙轉頭痛呼,“主子,主子救我。”
馬車翻了,先前坐在內裡的主人自然露了面。
那人瞧上去不過十七八歲,骨瘦如柴,眉眼精緻,與當今聖上有幾分相似,藍色大氅因方才之事略微鬆散,他提起滑落的衣襟,雙眸陰冷,如毒蛇朝外吐著信子,令人不寒而慄。
沈觀衣想起來了,普天之下能有這雙眼睛的,只有那位陰騭殘忍的二皇子孟央。
那是個殺人不眨眼的主兒,比起前世的李鶴珣來,也不逞多讓。
這不,一聲不吭便從旁人腰間拔出長劍,朝著她走來。
孟央身量不高,又十分消瘦,那身華服穿著他身上倒像是偷穿了大人衣裳的孩童,格格不入。
沈觀衣二話不說,利落地拔下簪子,警惕地看著他,不帶半分畏懼。
若他敢對她動手,她怎麼著也要剝他一層皮肉!
但孟央連眼神都沒給她一個,行至車伕身邊,手起刀落,一劍封喉,那人瞬間沒了氣息。
不過一個簡單的動作,孟央便喘氣不停,冷嗤道:“廢物!”
說罷,他便抬頭看向沈觀衣,眼裡遍佈陰冷,像是在打量一個死人,“便是你擋了本皇子的路?”
那柄還帶著活人血的劍被他艱難舉起,沈觀衣身量柔軟,且比他康健。
在他顫顫巍巍地雙手舉起劍要殺了她時,她長腿迅速一抬,裙角翻出一個漂亮的璇兒,一腳踢在孟央的手腕上,他手中的劍落在地上發出聲響,整個人搖搖欲墜,險些摔倒。
沈觀衣不想與孟央正面對上,於是在他即將摔倒之際,甚是好心地扶了他一把。
探春在一旁目瞪口呆,大氣都不敢出一下。
沈觀衣握著孟央的手腕不放,他清瘦得似乎只剩下骨頭,那極細的手腕彷彿一折便會斷,連她都能輕易握住。
對上他要吃人的目光,沈觀衣無辜道:“殿下,小心些。”
孟央咳嗽喘息著,對她這種與侮辱無異的行為惱羞成怒,手腕在她掌心扭動掙扎,試圖將她揮開,“放開!”
那張精緻到雌雄莫辨的臉因劇烈的咳嗽而染上紅暈,他力氣不大,連一個女子的手都掙扎不開,一怒之下他便想用另一隻手去掐沈觀衣的脖子。
探春驚呼,“小姐!”
“二小姐!”
茶坊門前驟然多了諸多官袍未褪的大人,瞧著這逼仄巷中的慘烈,紛紛目瞪口呆。
唯有李鶴珣眉眼一凝,冷冷地瞧著不遠處的兩人。
以他們的方向看去,只能瞧見一道婀娜的背影,女子髮絲紊亂,襦裙沾了一層灰,纖細的脖頸正被孟央掐在手中。
李鶴珣眉目陰沉,風雨欲來,夾著寒意的聲音驟然響起,“殿下,可否將你的手從臣妻的脖子上拿開。”